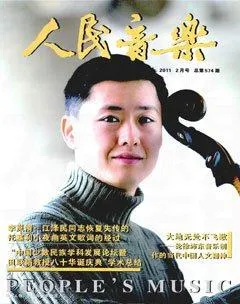阿倫.福特[中的“音樂分析學”
時 間:2010年6月5日
地 點:美國康涅狄格州哈姆登市福特別墅
訪談者:姜蕾(以下簡稱姜)
被訪談者:阿倫·福特 (以下簡稱F)
【前言】阿倫·福特(Allen Forte)是美國耶魯大學終身榮譽教授,美國音樂理論學會創建者,音集集合理論創始人,曾為美國《音樂理論》雜志主編。他一生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建樹輝煌,在海內外享有盛譽。到目前為止已發表重要理論著作8部,音樂理論文章100余篇,并參與過眾多音樂詞典、詞條的編纂。2009年10月,中國首屆音樂分析學會議在上海音樂學院召開,阿倫·福特教授作為特邀嘉賓首次正式訪問中國,在會議上做了多場專題講座。在此次會議上,圍繞當代音樂分析理論及福特音集理論等問題的探討,可謂百花齊放、精彩紛呈,但同時又覺得意猶未盡。譬如有關學科的命名,學科的屬性、意義及任務,相關理論術語的辨析,以及福特理論等問題引發了與會者激烈的討論及會后持續多方面的深入思考。作為一位親手創立美國音樂理論協會的元老,一位有著深厚學術功力的音樂理論家,一位有著四十余載豐富教學經歷的音樂教育家,福特教授就此次會議及其他相關問題的認識和思考相信會帶給中國音樂理論界以寶貴的啟發。我有幸作為福特先生此次訪華的全程陪同,同時也借助我目前正在耶魯大學訪學的契機,特采訪和整理了福特先生此次中國之行的感想,及他對相關學術問題的看法,以與國內同行分享。
第一部分:中國學術之行感談
姜:2009年10月你應上海音樂學院的邀請特訪中國,與中國學者們開展一次學術交流互動,不知你對中國之行感覺如何?對中國音樂理論界有什么直接的感受?
F:2009年10月,我應上海音樂學院的邀請以傳統和現代歐洲音樂的結構特征為主題,為學生和學者們開展了一系列講座。我是很期待有這樣的一次機會,與中國的學生學者們在會上或會后進行交流、互動。在此次會議中,好些中國音樂學者,特別是一些年輕人的提問讓我印象深刻,他(她)們不僅英語表達流暢,對當代音樂分析理論的知識儲備也頗顯功底,這其中就包括我和其他一些西方理論家的學術成就,真讓人感到驚喜。很顯然,中國音樂理論研究水平的提高,正在使其學術環境日臻成熟。
姜:在這次上海音樂分析會議上,對于“什么是音樂分析學”成為與會學者討論的一個中心論題。首先是“音樂分析學”的學科命名的問題,此次分析會議的會標采用“Music Analystics”一詞,你覺得這個詞準確嗎?西方音樂分析理論構架之初,有沒有關于學科命名問題的爭論和困惑?最終又如何解決?
F:在上海的這次會議上,提出“Music Analytic”這樣一個術語,這個詞是本次研討會所首創的,相當引人注目。就我的觀點而言,“Music Analytic”完全可以在將來的亞洲或國際會議上作為重要特色被采用。
當美國音樂理論學會(SMT)1977年建立時,其命名是由創建者按照當時的具體情況研究決定的,因為這個命名將它的組織工作與它的姊妹學科“美國音樂學協會”(AMS)的組織工作清晰地劃分開來。后者主要致力于音樂歷史的研究,而前者不僅關注音樂理論的當下活動,同時也展望音樂“理論學”(Theoretics)——我這里運用了“Theoretics”這個新詞,有與中國的“Analytics”相呼應之意——領域的創新貢獻,尤其是由那些年輕成員所做的創新。在此,我想提一下在美國音樂學協會的芝加哥年會會議上,當音樂理論學會的創始人第一次宣布“音樂理論學會”成立時,招致了相當一部分的音樂學協會會員的不滿,他們認為新的“音樂理論學會”應該隸屬于AMS,并建議在命名中體現出這種隸屬關系,雖然沒有明說,但他們希望命名中包含這種“附屬”之類的稱謂。如今,音樂理論協會已經存在33年了。
姜:美國音樂理論協會(SMT)于1977年建立后,英國的音樂分析學會(SMA)在喬納森·頓斯比(Jonathan Dunsby)的倡導下也于1992年成立。記得理論家阿諾德·惠特爾(Arnold Whittall)曾提到過,英國《音樂分析》期刊的命名為了避免與美國《音樂理論》期刊的混淆,有意回避了“理論”一詞,而采用了“分析”。你覺得“SMT”中所概括的“music theory”和“SMA”中所概括的“music analysis”在內容、目標和研究方法上是完全一致呢?還是各具不同特征?它們之間是怎樣的一種關系?
F:美國《音樂理論》和英國《音樂分析》之間聯系緊密。美國音樂理論協會旗下的期刊《音樂理論光譜》與《音樂理論在線》和英國音樂分析協會旗下的期刊《音樂分析》都有著一個共同目標,就是為學者、學生們就已有的,或正出現的音樂作品發表其新觀點提供了一個國際性的討論舞臺。但它們有不同,其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國的音樂理論面向未來,更關注當前的新事物,在研究內容上更具體,更貼近音樂本體。而《音樂分析》更抽象些,涵蓋的范圍寬泛,較多關注過去的,傳統的研究。
姜:在西方,“music analysis”現如今是否已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成熟學科?
F:音樂分析被認為是一門獨立的音樂學術領域,這種觀點在那些主要的出版刊物中是顯而易見,如英國的雜志《音樂分析》(Music Analysis),與之相對應的還有法國刊物《音樂分析》(Analyse Musicale)比利時的“Analyse Musicale”,再有就是美國的《音樂理論雜志》(Jorunal of Music Theory),以及其他一些與美國教育機構相關的期刊等。以上提到的這些核心期刊都隸屬于相應的音樂分析學會,比如,英國音樂分析學會(SMA),法國音樂分析學會(SOCI?魪T?魪 FRAN?覶AISE D’ANALYSE MUSICALE),比利時音樂分析協會(La Société Belge d'Analyse Musicale),德國音樂理論協會(GMTH),以及美國的音樂理論協會等。
姜:就中國的音樂分析理論發展而言,有部分學者認為,存在著一種從最初的“曲式分析”向”音樂分析“、“音樂學分析”,再向“音樂分析學”的進化路程。在西方的音樂分析體系中是否存在類似的發展路徑?你對這一現象的看法?
F:在我看來,那種觀點是一種誤解和誤導,也是一種沒有必要的復雜化。當然,盡管音樂的分析偶然也涉及到其他分支學科,如音樂批評與音樂美學。這點尤其是在報紙媒體(的音樂文章中)比較突出,舉一個例子,《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音樂版編輯就曾是我在耶魯的音樂理論專業的學生,他的文章涉及方方面面。
姜:可否這樣理解,音樂理論研究必會涉及到音樂歷史的相關內容,而在做音樂歷史研究時,涉及音樂理論的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
F:我不這么認為。兩者的關系是“偶爾”關聯,而不是“必須”關聯。
姜:美國音樂學家Ian Bent在2000版《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的“音樂分析”這一條目中指出,分析的出發點是音樂現象的“本身”,而不是諸如傳記紀實、政治事件、社會條件,以及圍繞這些音樂現實的“外在因素”。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F:我完全同意這個觀點。音樂分析的中心任務是音樂的“結構”,應該讓我們的學生把注意力集中在這點上,而不是去關注作曲家的個人故事、社會政治條件等問題,否則分析者將會偏離他(她)們的主要研究軌道。順便說一句,有關生平故事之類的事業主要是業余人士的工作,他們一般沒有太多的音樂經歷,由此也容易漫游在那些諸如政治、社會條件之類的遙遠話題。在我的論著《無調性音樂結構》以及其他的專題論文中,我所關注的是創作母體(Matrix),針對作曲家的作品草稿、草圖進行技術研究,并對實際樂譜進行修正,而避談作曲家個人生平方面的內容。古斯塔夫·諾特博姆(Gustav Nottebohm)對貝多芬的第11號作品《bB大調三重奏》的分析論文“拓展”很廣,從歷史角度看很有價值,但從我的角度看,那還僅僅是一種表面性的“分析”。
姜:你發表于《音樂季刊》的“theory”(1982)一文中,曾就New Grove中的“音樂分析”(“Analysis”[Ian Bent])、“理論”(“Theory”[Claude V.Palisca])等詞條發表評論。就“New Grove”中相關音樂理論的詞條而言,哪些詞條是音樂理論專業學生所必讀的?如今2001年的New Grove 也早已面世,對比1980版,就“Analysis”和“Theory”來看,你覺得有無不足之處?
F:“Analysis”和“Theory”是New Grove中的兩條力作。作者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結構令人欽佩,詞條的寫作條理清晰、信息量豐富、權威性高。當然也并不是無可指責,比如,“Theory”在19世紀之后部分的論述顯得單薄,尤其是20世紀的理論概括并不全面,一些重要的人物被遺漏或簡略,像豪爾(Hauer)、邁爾(Meyer)、塔涅耶夫(S.L.Taneyev)等。另外,該詞條僅9頁的參考文獻確實略顯羞澀。“Analysis”的寫作也有美中不足,比如在涉及音集理論時,沒能基本區分“有序集合”和“無序集合”,前者主要應用于序列和十二音音樂分析中,后者則適用于更廣泛意義上的無調性音樂。在談到18世紀后半葉的音樂理論發展時,作者的注意力聚焦在曲式發展的歷史梳理中,而忽視了同時期另一重要的理論發展,如“層分結構理論”和“大規模調關系理論”,這些理論可以說是申克“音級”和勛伯格“音區概念”形成的前身。在18世紀上半葉的寫作中,作者把科赫(Koch)看成為1750—1840年中最中心的人物,而忽略了18世紀前葉另兩位重要的人物拉莫?穴Rameau?雪和海尼興?穴Heiniechen?雪。雖然拉莫的興趣不在于音樂分析,然而他的“基礎低音”對往后幾代人的分析理論的發展意義深遠,而海尼興的“基礎音”概念已觸及分析的方法問題等等。
我沒有仔細比較過相關詞條在2001版New Grove中的變化。除以上談到的兩個詞條外,其中涉及音樂理論內容的詞條如傳統領域的“和聲”、“對位”、“節奏”、“申克理論與分析”;現代領域的“無調性”、“十二音創作”;單個理論家的如“海尼興”、“伯恩哈德·贊恩”?穴Ziehn?雪等,以及輔助領域的“美學”與“音響學”等等,都是有志從事這個學科研究人士所不能忽略的。
姜:“Form”與“structure”在西方是兩個具有獨立域界的術語嗎?它們之間是怎樣的一種關系?
F: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沒有很確切的答案。不過就總體而言,這兩個詞應該有各自獨立的領域。曲式比較籠統,更多是涉及傳統的相關描述。而結構更具體些,它為受過訓練的、有才華的學生提供了一個更具豐富分析視角的廣闊空間。講到這點,我想再說明一下,有關作曲家生平、社會政治背景的敘述,從我的觀點而言,是次要的。比如說,從勃拉姆斯的卑微生平經歷中,是很難找到與他卓越而創新性的音樂方面的相關信息的。
姜:你覺得當前音樂理論學科發展存在哪些挑戰和問題,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和問題?
F:最大的挑戰是,音樂理論事業發展的整體方向與質量問題,年輕學者們的努力將決定這個學科發展的未來。所以我給正在迅速成長的青年音樂理論家們的忠告是,鍛造自身敏銳的問題判斷力,而不是一味地迎合學術市場的規定,而那些有志于并能勝任于這份事業的佼佼者們,將為該領域的未來發展帶來福祉。在我看來,這點比起當前的音樂理論教育、非傳統音樂作品或技法的分析研究更來得重要。
第二部分:個人學術思想回顧
姜:你的理論著作《無調性音樂結構》已由我國音樂家羅忠镕先生翻譯成中文,對中國現當代音樂作曲技術理論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你能再介紹一下你寫作此書的初衷,以及你個人認為此書對音樂理論界的主要貢獻及價值所在?
F:我當初寫《無調性音樂結構》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想對20世紀早期所出現的和表]過的現代音樂做一個詳細的理論梳理。在那些日子里,新音樂經常面臨消極而極端的抵抗。比如,勛伯格作品的公]經常引發騷動,一次,他的《空中花園》在維也納首]時,居然有一個無禮的家伙用槍威脅他的學生。“無調性”是20世紀第一個25年中音樂創作中所出現的顯著特征,盡管勛伯格不同意“Atonality”這個詞,他認為這個詞意味著沒有了調性。但正如這個詞可能存在的不確定性一樣,對于這個時期的那些復雜音樂的結構特征,同樣沒有讓人很好地理解,這也正是我寫作此書的初衷。至于我的這本書的價值,我想應該留給后人去評價。
姜:是否可以說,你的無調性理論是對申克調性分析理論的一種及時的延伸和拓展?
F:可以這么認為,但申克理論的價值是持續發展、延伸的。可能今天的年輕一代對申克分析法持不同的看法,但它并沒有過時。
姜:有人認為,你的集合分析理論對分析勛伯格、威伯恩等“第二維也納樂派”的無調性音樂作品很有說服力,但在分析當代許多無調性音樂作品時,除了把它作為一種新的和弦標記手法外,似乎很難進行下去,您有什么建議?
F:無調性音樂產生的背景是基于勛伯格及兩位學生的創作實踐,由此,相關的分析研究首先圍繞他們展開是自然的,但無調性理論本身并不局限于這三位作曲家,它同樣適用于其他無調性音樂作品,或只包含部分無調性的作品,甚至是有調性作品。比如我和我的學生也分析穆索爾斯基、普羅科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艾夫斯、巴比特、斯托克豪森、梅西安等人的作品。
姜:你的這本書是寫于上世紀70年代的,主要集中對音樂音高結構層面的分析。而80年代后的音樂作品,更多地以注重音色、新音響的發掘為創作的新尺度,你覺得你的理論著作是否能繼續適用于指導當代的分析與創作實踐?它的延伸性價值該如何繼續體現?
F:很難的問題。我想,我們學習音樂,首先需要考慮的是作品怎樣形成的問題,它的結構成型,他的創新性體現在哪?芽及如何體現的問題。藝術音樂不同于流行音樂,流行音樂今天流行,明天就可能不在了。藝術音樂不一樣,我們今天仍然在]奏莫扎特的奏鳴曲,貝多芬的交響曲,其價值是永恒持續的。(我的)無調性音高分析理論是一個一般普遍性的理論,它可以被運用在不同的藝術音樂中,至于它的適用價值能發揮到怎樣的程度,不是由我決定,我想此理論是可以應用到分析更廣泛的音樂作品的,但那個工作將不是由我來完成,而是需要寄托于年輕的一代。不過,有一點是對的,音集集合理論可能對某些當代作曲家的作品——比如里蓋蒂的作品,我沒有任何這方面的分析經驗——有效性可能不是那么明顯。
姜:你能談談,當初是怎樣想到用數學的方式來處理你的音樂理論問題?數學為你成功的音集理論體系的建立提供了怎樣的幫助?芽音級集合與數學的關系?
F:這問題很好。對,我對數學很感興趣,一直以來我的數學很好,后來,我曾在麻省理工大學(MIT)教書2年,接觸那些理工科的學生,學到很多東西……。我覺得,在說明問題時,數字總是比文字更可靠。而且,數字是一種國際性語言,大多數的人都能懂數字,包括中國人,所以數學能為國際間的交流提供一種便利的渠道,由此用數學解釋音樂理論同樣能發揮這種優勢。你還記得我訪問中國時,一位年輕的中國學生與我討論音集理論的問題,他的英文口語不錯,但當我們坐下來談論音樂技術性細節問題時,語言的解釋似乎不夠用,不過當我們借用數學的知識來探討他的分析圖表時,則能使彼此的溝通走得更遠些。
姜:你覺得怎樣的“音樂分析”才叫好的分析?
F:我覺得,一切具有原創性價值的分析都是好的“音樂分析”。要敢于提出自己個人見解,哪怕是持相反的觀點……。
姜:目前,你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美國民歌和爵士樂方面的研究,前幾年已出版了《傾聽美國古典通俗歌曲》、《美國黃金時代的民謠》等著作。2005年發行了音樂唱片《昨天和今天的歌曲》,你負責歌曲伴奏部分的寫作和]奏。為什么現在回到這個研究課題?下一本著作的題目將會是什么?
F:對。我對美國通俗音樂,尤其是爵士樂一直很感興趣,曾經和很多爵士樂手一起]出,現在,仍然保持著對爵士樂表]和分析的濃厚興趣。爵士樂在美國,隨著一代又一代年輕表]家背景和能力的變化,呈現出一個持續變化發展的舞臺。這里,我談談我自己那個年代的爵士樂手的經歷,那時,我和其他幾個優秀的音樂家在一些遠非理想的場所]出(一個低音提琴、一個薩克斯管,沒有小提琴)。有一次,我參加一個爵士組合,其場所的營業時間是從午夜12點到凌晨6點,門口站著警察,“職業女士”坐飲個別桌位,鄰近是早已預備好的夜宿賓館……哈哈。
我現在正在寫《科爾·波特的音樂生活》。科爾·波特是著名的美國流行歌曲作曲家,我對他關注有很長時間了,在我的《美國黃金時代的民謠》一書中已涉及分析了他的6首作品。此外,還有幾篇待發表的文章如《美國爵士樂發展的萎縮》、《通俗歌曲的語法結構》等。
第三部分:教學經驗分享
姜:你曾是耶魯音樂系的資深教授,有四十多年的教學經歷,能與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教學經驗嗎?
F:我喜歡小群體的教學模式,通常是10—15個學生。我覺得這樣,才能更好地關注每一個學生的想法,并能及時地和他(她)們進行溝通。我不喜歡講座的形式,因為人太多,也就不知道聽眾的具體想法。這里插一個笑話,我們這里曾有一個教授,喜歡開講座,每次在講座前都會說,“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請隨時把手舉起來”,可是他每次講課從來不看學生,所以他總是察覺不到有學生舉手……。這個教授的例子我們不應該有。另外,我上課時講的不多,喜歡創造氛圍讓學生多講,我來回答問題。再有,我總是喜歡在鋼琴上回答學生的問題,隨時用不同的音樂范例來加以解釋,這種方式學生很喜歡,也能讓他(她)們較快地理解。
姜:你當時都開設哪些音樂理論課程?學生的分析報告及考試要求是怎樣的?
F:本科生開設的課程大致是傳統的基礎理論課,比如基礎和聲,對位,綜合作曲基礎理論等。
姜:沒有獨立的曲式課?
F:沒有,曲式課往往包含在和聲課程里面,或是綜合的作曲基礎理論課程中。研究生的理論課程有高級和聲、對位,申克分析法,音集理論,興德米特和聲理論等等。學期考試是每個學生要做公開的分析案例陳述,分析的范圍可根據個人的興趣而定,以及規定篇幅的論文。
姜:你覺得年輕一代音樂理論教師應該具備哪些素質?
F:對現在和未來一代年輕音樂理論家的期望,我想強調的一點是,應該具備在鍵盤上親身實踐的能力。比如流暢的移調(這是聲樂伴奏的基礎),在和聲與節奏的空隙間提供多種方式的裝飾和填充能力,創造一個有助于形成整體結構框架的音樂背景。比如,可以組建一個鋼琴與低音提琴、一件銅管樂器(活栓長號是我的最愛)的小組合,這種鍛煉很有必要。
姜:最后請您對中國音樂理論工作者們提一些寶貴意見。
F:哈哈……,請轉達我對中國音樂家們的致意,但提“意見”我真是不敢當啊。
姜:非常感謝您能接受我的這次訪問。祝愿您身體健康,希望早日拜讀您的新著!
姜蕾 華東師范大學音樂系教師,上海音樂學院博士生
(責任編輯 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