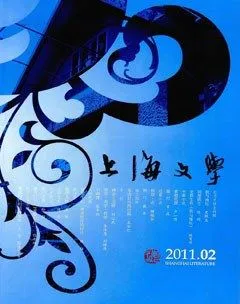繁盛時代的精神衰變
主持人:何言宏
對話者:王堯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清華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學昕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何言宏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持人的話1993年,也是在《上海文學》的“批評家俱樂部”欄目,王曉明教授等的對話《曠野上的廢墟》曾經提出人文精神危機的問題,引發過一場波及全國的大討論,對此,我們應該都記憶猶新。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還是在這里,基本上還是就我們的文學實踐來討論精神問題,無疑具有特別的意義,也讓我們感慨萬端。時隔多年,我們很自然地要問,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這么多年漫長和豐富的社會歷史實踐與文學文化實踐,“曠野上的廢墟”是否已不再?與當年的“曠野”相比,我們目前所置身與面對的,已經是一個號稱“崛起”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中,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文學,又各是一幅怎樣的精神景象?我想,這個問題一旦去作認真的思考,悲從中來,應該是我們很多人的感受。這么多年,說實話,與我們的理想和我們的希望相比,無論是我們的民族與社會,還是我們的文學,精神成就都很有限。
精神現實與文學的承擔
張清華:過去很多年中,我們似乎很樂于談“文學的危機”,但再過上若干年回頭看,那只是“盛世危言”而已,文學似乎并沒有什么衰敗的跡象,相反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的文學與中國的經濟一樣取得了長足的、令人不可思議的發展。而這一次,我以為確實是來到了某種“精神的拐點”。我們回頭看,世紀之交以來文學的走勢確乎呈現為一個“下坡路”的趨勢,作家們在世紀初所擁有的那種批判力量正在變得一天比一天稀薄。簡單地說,在世紀之初至少還出現了《檀香刑》、《花腔》、《愛人同志》等小說,即便人們對這些作品有這樣那樣的不滿意,但它們直指近代和當代中國社會歷史以及政治與文化的尖銳的批判精神,不能不說還是豐沛的。在這十年的中期,盡管有喜劇性和夸誕化的趨勢,但畢竟也還有《受活》、《兄弟》、《生死疲勞》等作品,有《人面桃花》、《山河入夢》、《刺猬歌》、《秦腔》、《笨花》等非常有藝術旨趣的小說,而在最近的兩三年中,小說界似乎正呈現一種“廣闊的沉寂”,好作品、有分量的小說明顯稀少了。日益繁盛的是一些基本沒有人文立場和精神價值的小說,一些融入了“諜戰”或“懸疑”元素的、投合某種商業和市場目的的小說甚至獲得了主流的文學獎項,這對于很難耐得住誘惑的中國作家來說,更是一種考驗。總體而言,我個人認為,隨著作家文化身份的微妙轉換,人文精神的日漸式微,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精英作家在精神活力與藝術創造力上,正呈現出的日漸枯竭的跡象。而下一代的作家中具有大氣象的又少之又少,這就使我們的文學真的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一個令人擔心擔憂的時刻。
何言宏:所以我說,這是一個“繁盛”的時代,經濟“繁盛”,文學也“繁盛”。這些年來,我們的經濟成就舉世矚目,經濟的繁盛使得我們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遍呼“崛起”。到了今天,晚清以降的“強國夢”似已成真,貧弱多年的中國終于出現了強大的跡象,表現在精神上,當然也相應地產生了豪邁、自信與不無強烈的民族認同意識,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無視另外的現實,那就是我們在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的同時,也存在著很多令人擔憂甚至是很可怕的現象。比如前不久,《人民日報》還發表過《人沒了,發展還有什么意義》這樣的時評,痛苦反省諸如礦難、火災、血拆、石化爆炸和工業污染之類的以人的生命為代價的發展。其實這也警告我們,一路狂奔的發展已經導致了很多嚴重的災難與問題,在我們的精神深處,如果連對人的生命都不再珍視、不再疼惜,再多的財富、再大的發展又有什么意義?所以我又認為,在我們的經濟成就與精神成就之間,存在著一個相當巨大的落差。我們可能就像一個“暴發戶”,腰纏萬貫,精神上卻很蒼白、貧窮,甚至很粗鄙與野蠻。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社會的層面上,我們仍然處在一個精神危機的時代,這就是我們的精神現實。想想看,如果一個社會傷天害理的事情大面積地屢屢發生,頻頻出現諸如毒奶粉、地溝油和制賣假藥等直接危害生命的藥品安全與食品安全問題,那這個社會和這個民族的精神到底衰變到哪樣的地步,真是可以想見的了。我想這起碼說明,對于很多人來說,在利益與物欲的誘惑與驅動下,精神的制約往往已失效,在他們的精神深處,無限膨脹或充斥著的,往往只是利益與欲望。“掘金時代”的上空飄揚的是“欲望的旗幟”,精神卻處于灰敗與危機之中。面臨如此嚴峻的精神現實,我一直以為,文學是應該而且也能夠有所作為、有所承擔的。
張學昕:因此說到底,我們還是希望文學能夠有匡正世風、改變民性的作用,這也很自然地使我想起“五四”甚至是更早的晚清以來我們對文學曾經寄予的厚望,那就是改造國民性的問題。這些年來,改造國民性這個啟蒙主義的文學主張受到一些人的質疑和“解構”,有的人還算有其自己的思想理路和學術文化背景,盡管在我看來這也很有問題,有的人加入這樣的合唱,激烈地否定國民性批判的話語,卻無比輕薄,思想和學理上都不值一覷的。在我看來,作為一種精神文化性格,國民性既會體現出一個民族難以移易的精神傳統,具有其較強的穩定性,但同時也是變化和歷史性地形成著的。一個民族在某一段歷史時期,往往會有其獨特的蒙昧。“五四”知識分子所揭示與批判的,是我們國民的昧于封建,到了“文革”,卻昧于政治,昧于當時的意識形態了,因此就有了1980年代的啟蒙主義文學。1990年代,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我們的國民可能更多的是昧于金錢,言宏所說的種種問題,其實大多都是“錢迷心竅”所造成的,為了金錢、為了財富、為了單向度的經濟發展,甚至連生命這樣的精神底線都屢屢突破!可以說,拜金主義,成了我們的國民最為核心的精神現實,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的文學義不容辭地應該有所承擔。因此在這樣的意義上,我認為我們的文學還應該著力于啟蒙,著力于具有新的精神指向和國民性批判內涵的精神啟蒙。
何言宏:所以說,文學的精神承擔的意義愈益突出。實事求是地說,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還是力圖有承擔的。清華剛才歷數了小說界的情況,我們不能否認像韓少功、賈平凹、莫言、閻連科、鐵凝、蘇童、畢飛宇、李洱和艾偉等不同代群的作家各自所做出的精神探索。在詩歌界,像王家新、翟永明、周倫佑和雷平陽、楊鍵、朵漁、鄭小瓊等詩人的作品,對于歷史與現實的精神關注和精神介入都很令人尊敬。還有在散文界,像夏榆的寫作也應該注意的。我經常向人推薦朵漁的《今夜,寫詩是輕浮的》這首“地震詩”和雷平陽的《殺狗的過程》,我認為它們的精神力量非常巨大,超越了很多平庸的作品。這里我用上了“平庸”這樣的字眼,是想指出在這些年來,相對于嚴峻的精神現實,在總量巨大的文學GDP中,我們生產了太多在精神上平庸的作品。清華剛才批評了一種現象,就是目前日益繁盛的一些基本沒有什么人文立場和精神價值的小說,特別是一些融入了“諜戰”或“懸疑”元素的、投合某種商業和市場目的的小說甚至獲得了主流的文學獎項。我以為除了各種主流性的文學獎項,還有像一些選刊、一些文學評論和文學研討活動,以及市場的青睞,一旦突出和嘉獎的是那些在精神上平庸的寫作,就會造成大量的平庸淹沒甚至驅逐那些真正具有精神力量和精神價值的作品,也會造成嚴重的誤導,我想清華所說的“滑坡”以及“精神拐點”的形成,和這種誤導不無關系。
當下文學的精神問題
何言宏:在包括宗教、哲學、音樂和美術等在內種種不同形式的精神實踐中,就其所能包含的精神內涵的豐富性、生動性與深廣度來說,文學有其獨特的意義。我以為在某種意義上,文學代表了一個民族在某一個時代所能達到的最高和最具綜合性的精神水準。所以說,進一步深入和具體地清理和考察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的精神格局,并且在這樣的基礎上評估它的精神成就與精神局限,便顯得重要而迫切。我個人的感覺是,這些年來的中國文學從精神的層面來看,比較混亂,亂象蓬生,喧囂無比,清理起來殊為困難。剛才我說普遍性的精神平庸淹沒和驅逐了那些真正具有精神力量和精神價值的作品,就是這種亂象的一個方面。但我也覺得,在這些亂象背后,也并不是無跡可循的,我們不如初步地診斷和清理一下新世紀文學的精神問題,揭示它的種種病相。
王堯:討論文學的精神問題,很容易空洞和情緒化。我們關于文學精神的歷史參照是什么?我們對文學精神面貌的基本估價如何?我們判斷的依據、理論假設在哪里?顯然,這些都是很模糊的。所以,這些年來,關于許多文學問題的討論都很難有交集。清華兄說過去的三十年文學有長足的發展,也指出世紀之交以來有“滑坡”的態勢,新世紀的十年應當是在過去的三十年之中的。所以,這個世紀和上個世紀的問題其實是糾纏在一起的。也就是說,精神問題有一個來龍去脈的過程,盡管它無疑有許多值得關注的“點”或者“拐點”,有“裂變”也有“關聯”。如果說,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討論”是考察這個問題的關節點,那么,我們需要討論這個“點”的前與后,文學的精神面貌究竟如何。1980年代,我們都認為是輝煌的,這個階段的文學作為精神遺產的價值還需要認識。當時的文學,所發生的歷史背景之一,是我們曾經有過精神被奴役的歷史,或者說經過長期的“心理暴力”的干擾,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是對精神的解放。文學同時又置身在重新開始的現代化歷程中,這是精神的開放過程。一是解放,一是開放。當時,我們所意識到的問題,是中/西、傳統/現代的沖突,文學的主題被概括為文明與愚昧的沖突。其時,我們已經面臨了精神處境的問題,到了1990年代初,有很強的挫折感。當現代化運動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以后,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運作以后,“人文精神”的問題變得突出了,整個文化的形態、結構、價值體系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一個新的語境中,各種沖突匯集在一起,我們逐漸失去了應對的能力(不僅僅是批判)。主流意識形態控制語言的方式有所變化,1980年代以后,文學如何處理這部分的問題已經有些經驗,但如何對待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則是個問題。這個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知識分子包括作家在內的經驗,并非完全對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加以拒絕,我們可以看到文學在這方面的妥協。我們不能改變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我們又要堅持精英的立場,那么構成我們堅持的精神資源是什么,我們的精神是否具有獨立性,我們又如何以文學的方式介入讀者的精神生活?我覺得現在也不能籠統地說“人文精神”式微了,而是這個社會的人文結構發生了變化。在這個變化中,文學的精神品質成了問題。
張清華:問題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了,文學有病,只是病在哪里?大家會有各自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見。在我觀之,隨著作家文化身份與寫作心態中人文性的日益喪失,他們對于歷史、現實以及當代經驗的認知方式、認知深度與結果都隨之出現了問題。不止是與歷史之間的“和解”,瓦解了他們探究、批判與追問的勇氣與眼光,有的作家干脆就是重新為歷史進行打扮和粉飾,或者毫無思考性質地使用“革命”或當代政治的資源,而讀者對此則毫無分辨能力。一些宣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作品(如《狼圖騰》一類)能夠大行其道,一些改頭換面噱頭化或怪異化的“歷史小說”(前兩年是《亮劍》一類,最近則改成了花樣百出的“諜戰”或“懸疑”題材)更是風靡一時,這都是值得我們反思和警惕的。這些作品要么迎合了政治的某種利益誘惑,要么應和了某種偏狹的民族主義思潮,它們從另一個方面表明了文學領域中人文主義思想的式微,投機政治與民族主義思潮的日益膨脹,而這可不是什么好征兆。從目前看,這些作品已經大有超過人文性的“純文學”創作的勢頭——從現實的利益獲得與關注度上則大約早已超過了前者。我以為這是值得警醒的,這已不只是文學界的危機,而是精神界的危機,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被異化的表現。我們的作家如果喪失警覺和免疫力,我以為是非常令人悲哀的。
何言宏:王堯兄提醒我們,應該從歷史變遷和社會文化結構等錯綜復雜的方面來考察文學的精神品質,你和清華也都揭示了這些年文學精神衰變的基本軌跡,清華還對諸如“懸疑”和“諜戰”這樣的小說大行其道深惡痛絕。據最近的一次報道,目前我國僅長篇小說的年產量就已經達到了三千余部,其中有多少讓我們“深惡痛絕”的寫作,真是只有天知道。其實,除了“懸疑”,還有諸如“玄幻小說”、“盜墓小說”、“口水詩”和那些以“青春”之名實際上對一代人的青春害多利少的所謂“青春寫作”,它們泡沫化的膨脹與“發展”,都顯示出當下文學中的精神病相。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的所謂“繁盛”,就是病態的了,套用一句前面的話——精神有了病,文學的發展還有什么意義?這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
張學昕:清華和言宏所說的現象和憂慮,的確很令人擔憂和可怕。不過,這可能只是一個很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方面,盡管這一面看上去很強大。但是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的精神坐標或代表性標志,終究是那些能夠穿透生活表象的、能夠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經典性文本。我不相信那些流行的、時尚的甚至風靡一時的東西會有多大的生命力,而真正有人文性的文字才能抵達人內心的最深處。這一點,我對我們時代的作家的寫作并不悲觀,還是滿懷信心,充滿期待的!
張清華:還有一點必須要指出,即“現實主義”思潮的泛濫趨勢。“現實主義”本身當然沒有罪過,但這些年“現實主義”風行的結果是,文學的“現實性”增強了,而文學的“精神性”含量則衰減了。先鋒文學運動留給我們的遺產——哲學探尋的興趣、精神追問的熱忱、批判的尖銳性,以及形式上的難度——都被這場俗而又俗的現實主義運動給丟棄殆盡了。在我看來,與其說是文學“回到了現實”,還不如說是“喪失了它的精神家園”。如今一些原本勢頭很好的青年作家,也漸漸失去了思想與藝術上的銳氣,因為他們深為周身的這種氣氛所圍困。我曾經遇到過一位青年作家,他非常郁悶于如今批評家和編輯的趣味,認為這些人過于相信自己對于文學的判斷,并且誤導了這些年許多有才華的青年人,我聽后深為羞愧。我在想,我們為什么如此樂于降低文學的精神與藝術難度,樂于夸耀文學中通俗而瑣碎的趨向?固然文學不能總是堅持哲學或思想的高度,不能夸大形式的意義,但如今文學的淺白和無力,其高度和難度的喪失,對歷史和現實的妥協,對于市場與流俗的迎合和獻媚,多數是在“現實主義”的名義下獲得了合法外衣。當然,籠統地將所有問題都歸罪于“現實主義”的泛濫也是不對的,其中的各種因素也要細加分析,比如“底層寫作”的問題,它涉及到敏感而復雜的文學倫理,不能簡單化地看待。不過我個人認為,它已經超出了“現實主義”作為一個藝術問題的范疇,它所引起的社會反應本身應該更值得我們重視。還有,如果從歷史來看,“現實主義”帶給中國當代文學的困境與負面影響似乎更大些,整個1950、1960和1970年代文學的困境都與此有關。這困境當然不是源于“現實主義”本身,而是源于我們認識論哲學方面的一種“先天缺陷”——因為一旦提到“現實主義”,我們好像不是在說一種文學的表現方法,而是在說“唯一正確”的道路和原則,將之當成一種“文學的最高標準”來理解,這是在過去很多年中“現實主義”之所以成為“文學的災難”的一個原因。而如今,我們對于這些問題仍然未予深入反思。從這個角度講,把“現實主義的泛濫”和“文學精神性的喪失”聯系起來看,也許是不無道理的。
王堯:我對有意鼓吹的現實主義,和清華兄一樣持反對的態度。我覺得這些年來有一些批評家的論述往回退了,退到了周揚他們這一代理論家批評家當年已經否定的那些資源中去了。這是需要警惕的。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之爭,在1980年代已經解決,如果再從對峙的立場來各執一端已無必要。現實主義不是必然導致文學精神性的喪失,如同現代主義也不必然導致文學精神性的增加一樣。我愿意跨越主義,把問題歸結到我們以什么樣的哲學和方式對待現實。
何言宏:我很同意王堯兄的說法,關鍵還得看我們以怎樣的精神姿態對待我們的歷史、現實和我們的文學。我甚至以為,文學精神品質的低劣,可能正與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并未得到真正的貫徹很有關系。前面我說過,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的繁盛和國力的強大,也隨著媒介和出版業的繁榮,我們的文學也出現了相當“繁盛”的景象,作家隊伍在壯大,文學活動在增多,文學評獎的獎金額度及其所帶來的附加利益也越來越“刺激”,與1980年代相比,文學GDP翻了不知多少倍。但與其相對的,卻是文學的精神品質在不斷衰變。很多假現實主義之名的寫作,其實并未真正地直面我們的歷史與現實。試問一下,新世紀以來不止萬部的長篇小說和總量巨大的文學GDP,有哪一部和哪一篇作品真正觸及了我們這個民族最為敏感的神經和最為深巨的精神隱痛?上一次對話中,我曾說到我們的文學存在著一個精神耗散與精神減損的機制,在我看來,文學體制新的一體化實踐、來自體制與市場的種種誘惑,還有作家群體的內部分層與社會結構之間的共謀與同構等等,都是這一機制的諸多方面,文學精神力量的衰退,我想與這些都有關系。王堯說要跨越主義,我以為我們的文學還應該“跨越”這些復雜的機制,包括“跨越”對自身利益的算計,真正抵達其應有的精神高度與深度。
尋找我們的精神出路
何言宏:當下中國的精神現實迫切需要文學的精神救治與引領,而我們的文學卻又呈現出種種復雜的精神問題,難當重任。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民族總是需要精神出路,精神重生的渴望異常強烈,所以說,探尋和思考這樣的可能盡管很困難,卻非常必要。具體地說,問題其實就是,在為我們這個民族尋求精神出路的事業中,文學應有怎樣的作為?我們非常清楚,這樣重要和困難的問題,不可能一下子就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只能提出初步的思考。我個人以為,探尋和思考這樣的問題,有一個我們必須面對的前提,那就是要認識到我們目前所面臨的精神困境的實質。我一直認為,現時代的精神困境與精神危機實際上發生于我們這個民族現代性的歷史進程中。自晚清以來,在帝國崩潰以后,從辛亥革命開始,一直到目前“經濟掛帥”的改革,我們這個民族曾經實踐過一系列在本質上屬于現代性的拯救方案。每一個方案的實施與更迭,在民族的精神深處,都會發生相當巨大的精神震蕩,都會經歷由起初的激情與幻想,到最終的失望與幻滅這樣痛苦的精神歷程。更重要的還在于,每一個新的方案都是對前一個方案的“斷裂”或“反動”,其所引發的震蕩無疑將更大。所以說近百年來,我們這個民族并沒有建立起一個較為有效的“現代性的精神根基”,一直處于“無根性的精神危機”中。如此漫長和如此嚴峻的精神危機,迫切需要尋求可靠的精神出路,這也成了很多思想家和文學家們相當急迫的精神使命。
張清華:尋找精神的道路正未有窮期。1990年代中國學界爆發的“人文精神討論”其實是一次精神尋找的自覺,它表明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對于自身文化身份的責任感與堅守信念的自我提醒。而今十多年過去,隨著中國社會與經濟的變化,這種文化自覺與身份體認變得更加迫切,但也更加艱難。1990年代,盡管知識分子承受了一定的壓力,但從社會的價值認同看,對于精神價值、文學的精神性向度仍然都懷著敬意,所以當上海的批評家們提出“人文精神”這一命題的時候,所獲得的是強烈的回應與認同,即便不同意的人,也不是反對人文精神本身,而是對于通向人文價值實現的道路有不同的認知。如今,如果再有人提出類似的命題,恐怕所得到的就不僅僅是認同,而可能是譏笑和嘲諷;另一方面,社會語境與文化文學語境也發生了劇變,單向度地談論“精神”命題肯定是有陷阱的,我們對此也要有清醒認識。不過,不管時代發生什么變化,知識分子、作家、文化從業者的共同責任是不會變的,那就是仍然要有“務虛”的沖動,要有對于文化與民族精神的憂患、反思與警示。如果我們的文學失去了這樣的精神,那就淪為了市場與消費文化的工具。
張學昕: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務虛”激情還是很可愛、很值得尊敬的,當時的人們確實也沒有覺得有什么可笑,都在很認真地爭論不休。我想由于精神語境的進一步惡化,類似的“務虛”即使顯得“可笑”,還是應該有足夠的勇氣去積極探尋的,大而話之,這是為民族,小而言之,也是為自己。有沒有勇氣去尋求我們的精神出路,在這個時代,首先就成了一個考驗與問題,這是遠遠不同于1990年代的地方。在此意義上,我們無疑要繼承過去時代的知識分子勇于“務虛”的精神傳統。現在的問題是,知識分子的內在精神坐標已經發生了嚴重的位移,幾近于陷落,因此,問題也就變成了知識分子如何才能拯救自身了。期待知識分子“鐵肩擔道義”變得越來越困難,很多知識分子的作為所暴露出來的精神水平,連一般的常人都不如了,還能對他們指望什么?其實,這在不少作家的身上表現得也很突出,比如隨著很多作家的“中產化”,出現了清華一再指出的作家身份的變化所導致的精神立場、價值取向方面的曖昧,批判精神日益衰弱,這很讓人擔憂。
王堯:言宏提到的這個話題,很可能變成一個“現實主義”的問題了。我的基本想法是重建文學與精神生活的聯系。文學是精神生活的鏡像,這是一個沒有分歧的“共識”。但文學與精神生活的關系逐漸演變為一種失敗的關系。我們今天的不安和焦慮,很大程度上來自文學從精神生活的退出,或者是對精神生活的影響越來越減弱。當文學對這個時代的精神生活無足輕重時,文學才真正的是邊緣化了。現在,我們已經有了這種邊緣化的危險。我們一直認為文學的位置邊緣化了,文學的價值沒有邊緣化,但是如果文學失去對精神生活的重要影響,其價值又如何不會邊緣化?
張清華:談到尋求精神出路的問題,我也許更加留戀和懷念“先鋒文學運動”。我以為在新文學誕生以來的百年歷史與滄桑劇變中,“先鋒文學運動”是最值得懷念的時期之一,它對于文學形式的迷戀,所隱含的其實是對于哲學深度與精神難度的追求;它對于人性黑暗與無意識世界的挖掘與展現,所隱含的是對于世界和人生的悲劇性認識。當然,它也對應了一代青年作家的精神反叛——這是至為幸運的一點,對于這代作家來說,他們的叛逆沖動與“青春寫作”直接奔向了“先鋒文學”,而不是像他們的后代許多“80后”那樣,是把“青春寫作”直接投向了市場與媚俗的商業寫作。這是最使我感到痛心和憂慮的。我也不否認“80后”中有好的寫手、有才華的青年,甚至也有個別堅持“純文學”寫作的人,但總體上,他們被這個逐名趨利的物化時代挾持了,獲益其多又受困其間,將文學變成了“撒嬌”與賣錢的方式。無論如何,這不是精神的上升,而是湮滅。尋找精神的出路,要從培育和尋找精神的承擔者開始,對于我們這一代來說,這是責無旁貸的使命。我當然不是說要讓文學“重回先鋒文學”,這也許是不可能的,但先鋒文學所創造的叛逆與批判精神,對藝術與精神難度的崇尚,應該得到傳承。
何言宏:清華和學昕所說的,其實是想強調,我們應該從知識分子的精神史和既往的文學史中尋求精神經驗和精神動力方面的雙重支持。說到知識分子的精神史和既往的文學史,遠的不說,就說王堯在前面所提到的1980年代。那個年代包括文學知識分子在內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實踐所不斷取得的精神突破,他們的精神勇敢和精神的爆發力量,確實是我們值得珍視的精神遺產。清華從精神的角度懷念先鋒小說,與那時相比,現在的知識分子精神確實很灰敗、衰變和矮化了許多。所以,我很同意清華的主張,尋求我們的精神出路,關鍵是要從培育和尋找精神的承擔者開始。在此方面,不僅大部分“80后”很讓我們失望,就連我們自身也問題重重。現在看來,如何擺脫市場和體制的雙重誘惑與雙重壓力,誕生出勇于和能夠承擔起尋路重任的精神主體——在我的理解中,這還是魯迅先生所寄望的“精神界之戰士”——目前成了關鍵的問題。說到“精神界之戰士”,忽然想到當年錢理群先生對摩羅所作的如此夸獎,但是今天的摩羅,這位當年的“精神界之戰士”又如何了呢?從1949年偉大領袖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到摩羅大聲呼喊的“中國站起來”,“人民”二字的被舍去,個中意味,很值得深思。摩羅只是個案,但他體現和代表的絕不僅僅是他個人,這使我更意識到“精神界之戰士”難得,真正和堅定的“精神界之戰士”更加難得。王堯說要重建文學與精神生活的聯系,這個提法非常好。現在的情況確實是,文學似乎和我們這個民族以及我們自身的精神生活已經沒有什么關系了,文學對我們已經喪失了它所應有的精神影響。不能否認,不少作家在他們的創作中,也在進行一定的精神努力,但是說實話,這些努力很難滿足我們的精神需求。由于和精神界與思想界的脫離,很多作家自以為深刻和有力的精神與思想,我們讀來全都是常識,其實是很平庸的。兩三年前,我在討論“70后”的代表性作家魏微小說的問題時曾經提出,我們的文學應該在對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生活和我們作為人的自身進行深切批判的基礎上,重新建立更加明確也更加有效和有力的精神立場,現在看來,這一立場的建立,不僅還應該通過重建文學與我們精神生活的聯系,也應該通過重建文學與我們思想生活的聯系來進行。不過,話再說回來,無論是精神主體的培育與重塑,還是重建文學與精神生活、思想生活的聯系,抑或是批判性精神立場的確立,都應指向和建立于一種更加穩固的“精神根基”。也許,我們的精神出路,正在于去不斷地尋找和建立這樣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