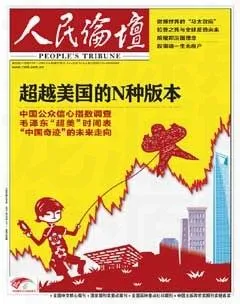紅色文化空殼化憂思
紅色文化向人們承諾的美好現實,未能在真實的社會歷史層面上全面實現,這就形成了紅色文化的表達危機,也形成了中國當下文化生產的表達危機——既然現實不能提供一個令人滿意的圖景,紅色文化所贊美的種種境況,也就自然成為一種空殼的允諾
2011年4月8日,我陪同《百年情書》的導演金舸一行在南開大學范孫樓章閣廳與同學們進行交流。大家對這部在南開首映的電影充滿了興趣,討論的話題慢慢轉向林覺民那封情書背后隱藏的凄苦人生故事。出乎我的想象,同學們明顯對金舸執導這樣一部“革命題材”的作品表達出“同情”的意味,仿佛導演是在命題作文,是為了拍攝一部電影而不得不走紅色路線。結果,導演金舸對那段歷史的闡釋未能激發起大家的認同。似乎只要是“紅色”,就一定是因為“聽令遵命”而生產出來的文化產品,其間生命的壯烈犧牲與血肉橫飛也變成了同學們熱情想象的視覺盛宴手段。
空殼化的紅色文化是對主流價值的顛覆與漠視
顯然,《百年情書》交流會的故事隱約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中國社會文化領域已經面臨紅色文化的空殼化現象。所謂紅色文化的空殼化,指的是傳統社會主義文化價值在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經濟改革歷程之后,已經被一種世俗主義、甚至是市儈主義的價值范式所沖擊,并且被暗中抽空了具體內涵,成為脆弱5B1/idRooIBifrTuvT1c2w==的、鏤空的儲物盒。人們對于革命時代的激情,喪失了認同的欲望,卻保留了獵奇的幻想。以毀滅為視覺印象的革命年代,如何呈現其間回腸蕩氣的偉大精神,如何讓今天的人們了解紅色文化所包含的崇高美,已經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
因此,僅僅為了迎合各種活動需要而進行的紅色宣傳,除了顯示一種訓導主義的霸道和教條之外,難以有所建樹。前不久,四川宜賓市興文縣舉行紅段子創作大賽,官員稱為了不傳播黃段子、灰段子,用發紅段子的形式揚社會新風,借助通俗易懂的短信來謳歌家鄉的新變化。他們甚至設立較高的獎金來鼓勵干部們發送紅段子。這個事件立刻引起了許多人的議論,人們在不認可這種“文化大躍進”式的紅段子制作方式的同時,也批評這種行為背后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觀念。
有趣的是,這個新聞事件最值得我們憂慮的地方并不僅僅是官員們文化制造活動的作秀,而是這種作秀明明已經喪失了現實意義,卻仍舊被炒作為一種“政治信念”。換句話說,不憚于以虛假的形式來創造或使用紅色文化,成為今天主流文化生產的基本邏輯。明知沒有作用,還要裝模作樣,這種空殼化的紅色文化,掩耳盜鈴之余,其實恰恰是對他們所倡導的主流價值的顛覆與漠視。
四川興文紅段子現象體現了主流文化與政治機制之間巨大的裂縫。一方面,主旋律的、紅色的文化生產體系,依照傳統社會主義的道德原則與價值取向,不斷向民眾承諾一個公平、繁榮和穩定的現實圖景——無論是春節晚會的祥和還是同一首歌的激情懷舊,無不按照“美”的原則想象性地塑造一個美輪美奐的現實人生;另一方面,中國社會政治管理體系圍繞保護自由經濟的目的轉型并確立,造就了中國社會獨有的資本政治化現象,公民對政府管理方式、社會控制能力與生活保障體系的嚴重失望,從而出現了國家穩定強大、個人卻感覺失衡渺小的吊詭心態。也就是說,紅色文化向人們承諾的美好現實,未能在真實的社會歷史層面上全面實現,這就形成了紅色文化的表達危機,也形成了中國當下文化生產的表達危機——既然現實不能提供一個令人滿意的圖景,紅色文化所贊美的種種境況,也就自然成為一種空殼的允諾。
四川興文縣的官員,懷著美好初衷提出用紅段子驅逐灰段子、黃段子的計劃,也無形中顯示出紅色文化的生產者、管理者對于我所說的那種文化表達危機的盲視與麻木。事實上,文化的表達危機來自于現實的社會危機。換言之,文化的危機,并不能僅僅用文化的方式來解決,而是要在社會存在、在現實體制的領域內解決。而這一點恰恰是許多文化生產者與管理者不能、不愿或者不敢面對的問題。
無獨有偶,在藝術文化領域,有諸多學者、藝術家同樣無法意識到這個問題。在《十月圍城》上映之后,許多學者站出來贊美這部電影如何把紅色文化與商業文化巧妙地嫁接在一起,實現了主旋律電影的商業化成功運作,并且天真地認為,觀眾爭相購票觀看這部電影,乃是說明紅色文化只要有市場運作,就能恢復其魅力。說到底,他們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承認這樣一種現實:紅色文化的表意危機,乃是一種社會性的政治危機,而不僅僅是一個美學策略的危機。在《十月圍城》中,作為紅色革命文化符號的“孫中山”不僅沒有真正出場,而且,還被暗中轉換成了一個毫無政治含義的“敘事動機”。換句話說,《十月圍城》不過是運用了香港電影常見的一種“奪寶模式”來設計影片,“革命”、“孫中山”,只不過是徹底空殼的“寶”而已,并沒有任何政治功能與內涵。
文化的危機要在社會存在、現實體制的領域內解決
由此觀之,當前紅色文化的空殼化,作為一種表意危機,呈現為兩種形態:一是被有意作為一種政治秀來使用,一是被作為一種消費符號來使用。前者常常不被認同,流于形式;后者熱熱鬧鬧,不過是把紅色歷史與故事,當做當代城市人幻想浪漫和傳奇的一種文化體驗類商品來推銷使用。不妨說,這兩種紅色文化的空殼化形式,或冷或 熱,都無視紅色政治文化中激情四溢的啟蒙主義光輝與理想主義品質,都是按照世俗主義或者說市儈主義的邏輯來對待紅色文化。在他們那里,紅色文化要么是死氣沉沉的陳詞濫調,要么是桀驁不馴的革命江湖——現實批判與理想向往的激情,已經消失殆盡了。
所以,當前對于紅色文化的重建工程,核心點應該落在“激情感染力”這個方面。為什么林覺民能夠在如此輾轉折磨之后還是毅然犧牲?是什么讓千百萬中華兒女在抗日的烽火中喋血戰場?是什么讓瞿秋白淡然面對槍口?感染力不僅僅是來自對黨團身份的強調,更不是來自血肉橫飛的視覺刺激效果。紅色文化里面最大的合理性,不是毀滅的壯觀與犧牲的激烈,而是背后隱含的對于更好的生活的追求、對于更合理的未來的向往、對于社會主義所承諾的現實的信念。
換言之,紅色文化的合理性正在于它宣揚了這樣一種理念:沒有什么比人民的幸福更加重要;沒有全人類的解放,就沒有自己的解放。紅色文化的建構,要放下訓導主義的架子,要回到革命時代和今天的人們都認可的生活理想層面上:如何建構一個更加合理、更加美好的中國?如何讓全部的公民都能夠生活得更加安全、民主和幸福?只有改變文化生產理念,真正取得人們的認同,紅色文化的生命力才會長久。
(作者為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責編/高源 美編/葉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