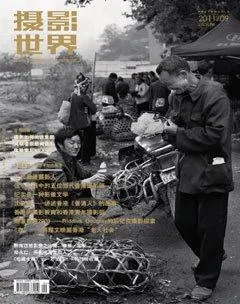風光攝影與傳統繪畫的異同
2011-12-29 00:00:00李元
攝影世界 2011年9期





在視覺媒體乃至文化、藝術里,攝影是非常獨特而且有別于任何其他媒體的。它是19世紀歐洲工業革命時代的發明,它的興起不像繪畫、雕刻乃至書法和文學等那樣,并不是隨著人類文明開始在各社會文化里同步發展的。不過在這個科學進步的時代里,目前它已經成為一項最大眾化,而且也是應用最廣泛的視覺媒體。也正因為如此,攝影到底是什么?怎么去看待它的意義與發揮也就難有定論。這使我常常感到,我們有必要接受,在很多攝影的探討上,“沒有對的或是錯的意見,只有不同的看法。”
作為一種新興的媒體,我們對于攝影的理解是逐步深入的,而它的廣泛應用也沒有和社會的經濟發展與改變脫節。從攝影發明的時候開始,它的紀實性便成為它普及應用的動力。而作為一項沒有前例可循的媒體,它一直被拿來和繪畫做比較,但是它的價值何在卻一直難有定論。在早年,像19世紀英國的羅賓遜(Henry Peach Robinson)和20世紀中國的郎靜山,都把繪畫的概念運用在攝影里,形成了所謂“畫意派”攝影風格。這個情況雖然隨著愛默生(Henry Emerson)所創導的自然主義興起,以至攝影在社會紀實上的應用而有所改變,即使在今天,還是有人以繪畫的神秘感來衡量攝影,特別是在風光攝影上,對所謂“美感”和“氣勢”的追求,還是被中國攝影界普遍接受,不過也有人認為風光攝影特別不適合跟中國文化和傳統繪畫搭配在一塊兒。
盡管說繪畫和攝影都建立在一張畫紙(或是照片)上,兩者有相似的地方,但這兩者確實是兩種不同的媒體,不能混為一談。至于前面所談到的兩種看法,在我認為都是把攝影看得過分局限,而忽視了作為視覺媒體,攝影所能發揮的內涵與價值。
創作基礎的不同
首先,在創作的基礎上,攝影和繪畫是完全不同的追求。繪畫是根據畫家的經歷和觀察,把他“胸有成竹”的構思主觀地布置在畫紙上。但是建立在“實物成像”基礎上的攝影,它的出發點在于客觀現實(甚至沒有預料情況)的存在。攝影的本質是把眼前的客觀景物或事件,通過相機轉變成攝影者主觀意識的發揮。相反來說,不論攝影者有多么深刻的理念和構思,如果沒有客觀現實的存在,他就無法著手。這就是為什么我常常覺得,在我的攝影追求上,不是我想拍什么,而是領會到老天爺讓我拍什么。當然我的這份隨意性并不為很多攝影者所接受,不過對于這個問題,我在后面會做進一步的分析。
這里,我想先談談最近我在網上看到的一篇大作。這位作者首先指出,風光攝影與中國傳統繪畫之間的差異。他特別提到,在中國的傳統繪畫里既是沒有光源概念,也缺乏透視的理念。對于這一認識,我相信熟悉傳統繪畫的人都會認同。也正因為如此,就像那位作者所說,“從西方繪畫轉到攝影是非常順暢的”。這是因為傳統的西方繪畫基本上是建立在記錄的基礎上。也正因為如此,隨著攝影的發明,它促使西方繪畫跳出了傳統的追求,從多方面來找尋突破。相對說來,從光線、留白到透視感,這位作者對于中國傳統繪畫的理解,想必也讓他認識到中國繪畫從來不是從純粹記錄出發的。可能就是這個理由,使他認為風光攝影特別不適合跟中國傳統繪畫搭配在一塊兒。但是,在構圖以及視覺效果的發揮上,兩者還是有相互借鑒的價值,不過這也并不能限制風光攝影的發揮。畢竟說來,攝影與繪畫都是視覺的語言,所能帶來的發揮完全要看各人的思維與能力。不過這位作者的一些觀點,似乎也反映出目前在急于“和國際接軌”的心理下,國內一部分攝影愛好者對攝影的看法。他們認為,攝影既是西方的發明,人們似乎只有跟著西方的傳統去探討攝影,而沒有認識到,作為一項視覺的媒體,攝影雖然有它的特性,但絕不是說我們需要對它在西方文化里所建立的傳統無條件地接受。
記錄層面的不同
其次,建立在“實物成像”基礎上的攝影,雖然可以被看作是一份記錄,但是我們有必要認識到所謂“記錄”和事實之間的差異。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談攝影》(On Photography)一書里指出,“盡管說我們心目中對它真實性的認定為攝影帶來了它的權威性和吸引力,它還是處于藝術和真相之間;雖然說攝影者最關心的是錄制事實,他們卻還是被品位和良知,這些潛意識上的壓力所左右。”更何況當攝影將三維物體在二維平面上重現出來的時候,它所表現的就只不過是攝影者對事物觀察的一個側面,而不再是事物的本身。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能夠認識到攝影者的觀點,也可以對同一個題材的攝影作品做比較。換句話說,即使在西方文化里,攝影并不局限于對實在物體純粹的記錄,它到底是什么,還是有不同的看法。
從光線、留白到透視感,攝影與傳統繪畫,甚至其他任何媒體之間的差距,在于攝影的紀實性、發現性和瞬間性。因為攝影的紀實性,從一方面來說,照片的拍攝不能像繪畫(甚至文學)那樣,可以根據自己既定的思想去發揮。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正因為它的紀實性,攝影作品就比任何其他媒體更有說服力。但是很遺憾的是,隨著數碼技術的演進,攝影紀實性受到了無窮盡的挑戰。不過我想強調的是,這個問題不在于攝影本身,而在于太多的攝影者喜歡把自己abDWJNL/KIxY+BfXyfeqLDPCc+gTiaYNOmL8Az8EWa8=既有的主觀理念放在攝影紀實性的前面。
其實說來,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不僅說主觀的“自我”在當今的社會文化里,被認為是個性的發揮,所謂創新與原創,都是在于獨立而有別于他人的追求。特別在當今所謂“觀念藝術”的領域里,創意者的追求也在于表達個人的理念。說到這里,又讓我想到一些想“和國際接軌”的“觀念攝影”推動者。其實說來,“觀念攝影”本身就是一個結合了兩項不同意義的名詞。從“觀念”來說,它只是“觀念藝術”創意者的一種手段。正因為個人主觀意識和理念的表達和發揮是他的追求,往往是在理念形成之后,他再去決定表達這份理念最理想的手段。在這個階段,如果他發現攝影是最能表達自己理念的手段,他就會用攝影表達這份理念。換句話說,對于一些“觀念攝影”的實踐者來說,他的追求與其說在“攝影”,還不如說著重于“觀念”的表達。如果兩者之間有所矛盾,他可以放棄攝影的紀實性,而強調作品所表現的觀念。這也就是說,對這一類的攝影愛好者來說,我在前面所談到的攝影隨意性就和他們的理念幾乎可以說是兩種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追求。
可是反過來說,正因為對一些風光攝影的愛好者對一些景物拍攝的興趣不在于純粹的記錄,而來自這些景物為他所激發的個人看法和觀念的表達。從廣義的來說,這不僅符合“觀念攝影”的定義,而且它的發揮是從攝影的特性出發的。只不過對于大自然的價值,在西方社會里不是這樣來認識的。要把這樣的照片推入當今西方文化里對“觀念攝影”的解釋,那就像當今中國國際地位推進一樣,需要時間,也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不過這個話就說得太遠了。對于這個問題,我在2010年一月的《攝影世界》里所寫的《從觀念攝影談寓情于景》一文里已有所探討。
對我來說,攝影的紀實性是攝影有別于其他媒體的基本差異。如果把它放棄了,攝影只不過是數碼時代的畫筆而已。但是反過來說,作為一項記錄的工具,攝影是否就局限于實在事物的再現,而攝影作品也只能從它的題材來解釋?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從攝影發展過程中得到一些認識和先例。自古以來,獨立思維和個性的發揮雖然在于創作者本人,但是最終價值的認定卻不在于創作者本人,而是在于社會對它的接受。不過即使在不同的社會與文化里,它的認定還是在于智慧、思想、深度或是社會價值。正因為攝影只是被看作一項純粹的記錄,在西方文化里,它的人文價值往往就成為衡量的標準。桑塔格認為,“惟有攝影的工業化為攝影家帶來了對于社會題材上的應用以后,攝影才被當作藝術來看待。”這是因為在西方的人本社會里,人文題材和觀賞者有直接的溝通,攝影者個人的觀點也是他對社會和人生看法的表露。相對來說,在風光攝影里,安塞爾·亞當斯(Ansel Adams)之所以被推崇,主要的是他在暗房技術的獨特創新與發揮。不過隨著數碼技術的演進,手藝老人的很多基本功都被科技所取代了。
但是在中國文化里,繪畫本身就不是從記錄出發的,特別是山水畫的價值,與其說在于寫實,不如說通過對大自然的觀察所帶來的主觀意念和思維的表現,從而引發生活的借鑒與哲學思想的引申。這份追求遍及在中國文化里的各種媒體里。即使在詩詞文學里也充滿著對于大自然的描述、借鑒和引申。從李白的“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到毛澤東的“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在中國文化里,吟詩詠景以至“以景寄情”一直被認為是生活上的情趣,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修養。這份傳統有別于發明攝影的西方社會,可是它所激發的思維卻一樣地引發對人生的認識與感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元代馬致遠所寫的《天凈沙 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可以看作是一幅紀實的照片,但是它為馬致遠所帶來的感受卻是“斷腸人在天涯”。這不僅遠超越了題材的本身,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有的反應,更不用說跨越不同文化的鴻溝了。也正因為如此,也沒有必要貶低他人在這方面的探索。
這個例子,不僅說明了文化上的差異,也可以印證我在前面所說的論點,“沒有對的或是錯的意見,只有不同的看法。”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正是風光攝影與傳統繪畫的異同。兩者雖然都能用來表現創意者主觀的意識,但是攝影的紀實性卻正是可以改變傳統繪畫里的留白和“散點透視”這些被一些人認為是“虛”的形象,從而引用攝影的各種特性,發揮風光攝影里所能表現的中國文化內涵。
不過話又要說回來了,攝影的紀實性卻也能使得一部分觀賞者堅持“見山是山”的觀點,而無法領悟“見山不是山”的引申。這雖然可以是因人而異,但要減低這份可能性,我們也可以從詩詞、哲學甚至書法得到啟發。一般來說,人們走在野外,大地上的景物都能引發各種不同因人而異的思維。舉例來說,從攝影的發現性講,走在水邊,可以觸發對《道德經》里所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的感受。如果說這份構思在當今聽來似乎顯得太遠了,我們也可以發現,從“枯藤、老樹”到“小橋、流水”,以至“古道、瘦馬”,馬致遠引著讀者從近到遠,一步步進入這片景色,這也就是說,如果說攝影的紀實性,特別是利用熟悉的前景,可以讓一位觀賞者沒有顧慮地走進畫面里,那就容易為他帶來個人的感受與反應。這也就是陶淵明所寫的,“景翳翳以相入,撫孤松而盤桓”所給人帶來的感受。而一旦人們覺得和眼前的景物能夠融會成一體,那不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嗎?我們又何必在畫面里堅持“天”與“人”實在物體的出現呢?如果說攝影的意義僅限于實在物體本身的記錄,那就未免過分小看了人的思維能力了。
總之,我認為所謂“媒體”的價值在于表達個人的思維以及他所處的文化。就像前面所說,繪畫、雕刻以至書法和文學等媒體那樣,都是隨著人類文明開始在各社會文化里有同步發展的。如何在攝影這個來自西方的媒體里找尋自己,而把中國文化里的認識和價值觀推向攝影的追求上,有賴所有華人和畫意攝影者更深入地去探討它、理解它。而并不是絞盡腦汁或是耍點花招來注入什么深刻,甚至宏偉的哲學概念。假如我們放棄這份努力,認為“大家吃漢堡包,我們就沒有必要去研究對生煎包的改進”,把精力放在現階段而且是建立在歐美價值觀上的攝影標準,那將是非常遺憾的。要是我們不探討風光攝影,追求風光攝影進一步的發展,也就沒有人會做這份努力。
盡管說攝影的紀實性證實了風光照片的畫面來自現實的環境,它能為觀賞者所帶來的認識,說明了它的拍攝一樣能夠表現出攝影者的看法,可以超越純粹的記錄。通過畫框和構圖的應用,它也可以是攝影發現性的發揮。在這片起伏的麥地上,收割機所刻畫的線條帶來了一個充滿動感的畫面,足以引發對大自然環境新的認識和感受。
攝于美國愛達荷州。
佳能FT-QL相機,FD 80?200毫米F4 鏡頭,光圈f/16,快門1/30 秒。
“天、地、風、雷、水、火、山、澤”是《易經》里的“八卦”。其中“天、地、山、澤”是大地上具體的景物,也是風光攝影拍攝的題材,而“風、雷、水、火”卻是天地交匯的媒介。火代表了熱力,它使得水蒸發成云成霧,也通過風、雷而下降成雨成雪,交匯天地,溝通萬物。而這份連接最能通過云層的變化表達。換句話說,太陽與云層的變化,足以改變大地的景觀,形成了隨時在改變的動態大地。
攝于加利福尼亞州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佳能EOS-1N相機,EF 28~135毫米F3.5-5.6 IS 鏡頭,景深對焦,局部測光。
走在樹林里,地上的蕨草和盤結的樹干不僅帶來了對比,也讓人感到走進了這樣的一個環境。至于說它能讓人感受什么,那就因人而異了。
攝于加利福尼亞州紅木國家公園。
佳能EOS 5D Mark Ⅱ相機,EF 28~135毫米F3.5-5.6 IS 鏡頭,光圈f/32,快門1.6秒。
不論是繪畫還是攝影,畫面題材的選擇以及構圖,不僅在于個人的背景,也和他所拍攝的題材連接在一起。就拿梵高來說,他在色彩上的運用也和他所選擇的地區有關。走在三峽地區,峭壁與小舟的結合很自然地令人想起國畫效果來。
攝于三峽大寧河畔。
佳能F-1相機,FD 80~200毫米F4 鏡頭,光圈f/22,快門1/60 秒。
攝影的紀實性配合上熟悉的前景,特別是通過廣角鏡頭所帶來的透視感,可以讓一名觀賞者沒有顧慮地走進畫面里去,那就容易為他帶來個人的感受與反應了。在這里,一棵倒下的枯樹幾乎讓人感到匍匐向前。
攝于納米比亞。
佳能EOS 20D相機,EF 10~22毫米F3.5-4.5 鏡頭,自動景深對焦,局部測光。
大自然環境瞬息多變,這正是攝影瞬間性發揮的機會。在這里,云層的變化為一個非常平凡的環境帶來的幾分神秘感。
攝于華盛頓州雷尼爾山國家公園。
佳能EOS 5D Mark Ⅱ相機,EF 28~135毫米F3.5-5.6 IS 鏡頭,光圈f/32,快門1/200 秒。
對我來說,表現出自然有機而且具有生命力的一種可能,就是在于建立一個具有動感的畫面。在這里樹木和它在陽光下的影子不僅具有動感,在畫面里也似乎有一份呼應。
攝于加利福尼亞州約蘇亞樹國家公園。
佳能EOS 5D Mark Ⅱ相機,EF 16~35毫米F2.8L 鏡頭,光圈f/22,快門1/50 秒。
“天地交而萬物化生”是中國文化里的宇宙觀。在野外,利用云層的變化,不僅最能表現這份交匯,也能顯示一份動感。
攝于美國蒙塔那州。
EOS 5D Mark Ⅱ相機,EF 16~35毫米F2.8L 鏡頭,光圈f/16,快門1/50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