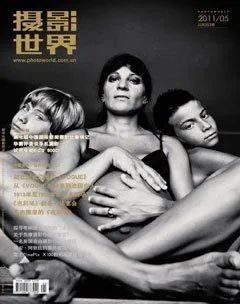雜志圈里的《名利場》
2011-12-29 00:00:00章開元
攝影世界 2011年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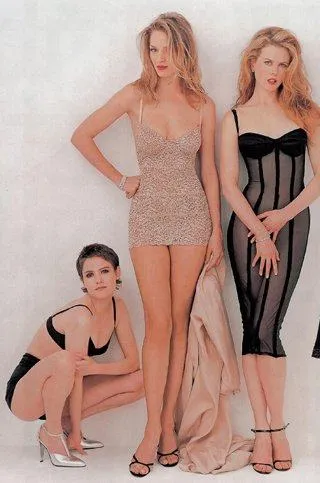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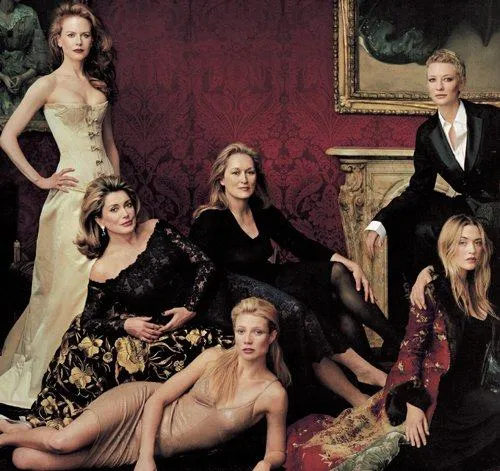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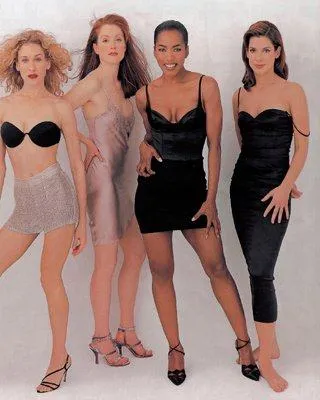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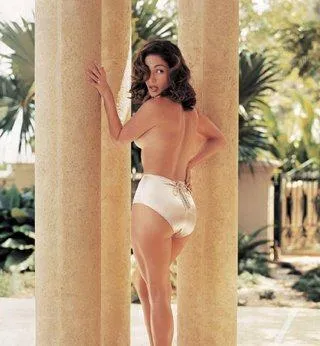


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甚至還包括可預見的未來,美國都是世界上第一雜志消費大國。美國雜志的發展歷程也就是世界的“雜志史”。在當今的網絡時代,紙質雜志逐漸式微,電子閱讀方式異軍突起,但說來說去雜志作為一種新聞出版業態,完全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或許這一天還很遙遠。美國的雜志之所以有極強的生命力,細品之下很有些像其他享譽全球的美國產品,好吃不貴麥當勞肯德基、好玩不貴當屬迪斯尼、好喝不貴有可口可樂、耐穿不貴首選牛仔褲、好看不貴又有好萊塢,等等;你說它是爛貨也好,垃圾食品也罷,總之美國人不像歐洲人那樣老想爭創名優,到頭來弄得個曲高和寡,賣得個賊貴,如今不是關門溜號,就是假貨仿冒品滿天飛。說白了美國貨就是西方國家的大眾貨,非但中產上下的人都用得起,外國人也可以跟著沾光,你想做假還不容易;因為名氣太大,利又薄,容易被人看穿,做假的劃不來。反正至今誰也沒聽說過假麥當勞或假可口可樂這類的產品。而君不見,假LV包和勞力士手表滿天飛,就是這般道理。
再回頭說美國的雜志,種類繁多,各自都能找到對頭的看客,不過也有不走運的,那怎么辦?商場如戰場,不戰自敗。掏錢辦雜志的人都是最具有商業頭腦的精英分子,但也有失算賠錢的時候。就盈利而言,搞股票證券的有前瞻性和投機性,而搞雜志的則更要復雜一些,投機性的沒有,前瞻性和敏感性加到一起都不夠,怎么也要再有點兒文化感覺。
追溯到上個世紀之初,美國盛產百萬富翁,當時的“百萬美元”富翁絕對不一般,那陣子美國普通工人一小時干下來只掙一毛錢,一千美元就能買一幅歷史近百年的頂級油畫,一棟豪宅在紐約第五大道這樣的地段蓋起來也不過就幾十萬美元。差不多也是這個時候,近代攝影術已趨完善,雖然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彩色照片,但黑白照片的質量已不成問題,只要是認真之作,無論是影調還是層次,都堪稱完美。攝影在當時已形成了不可小覷的工業規模,尤其是在早期的工業化國家,在攝影上打主意和準備以此發財的大有人在。在攝影技術并不十分成熟之前,西方人就很會運用手繪的插圖來為書籍報刊做插圖,這回有了照片,其紀實表意功能與昔日繪畫不可同日而語,就大眾的取向而言,有了照片就不看繪畫,有了電影或電視,就不看照片,這是誰也左右不了的必然。但當時看電影肯定去電影院,電視連影子還沒有,所以介乎于報紙和書籍之間的雜志大行其道,尤其是刊登大量插圖的消遣性雜志,辦一個火一個。
1913年,已經成功經營了包括《時尚》(VOGUE)在內的多種出版物的著名出版商康德·納斯特又收進兩種新雜志——《服裝》和《名利場》。憑著一個精明商人的直覺和與生俱來的商業頭腦,他準備大干一番。一開始他把兩本雜志合并了,取名叫《服裝和名利場》,迅即成為紐約最為時髦的刊物。但這個名字無論是看上去還是念出來都覺得不順嘴,況且有了“服裝”這兩個字,等于自己給自己限定活動地盤,傻呀?六個月以后,納斯特悄悄拿去了“服裝”二字。隨后是手腳齊上,主意策劃滿天飛,兩年之內居然使這本雜志成為全美廣告收入最多的月刊。納斯特深知,在如今的攝影時代,刊登好照片是雜志銷量的助長劑,照片代表著時尚和事實,而攝影名家,在那個時候是僅次于當紅電影明星的文化人,畫畫兒的比不了。他首先瞄中的是攝影大師斯泰肯。1923年,康德·納斯特重金聘請當時聲望最高的肖像攝影師愛德華·斯泰肯作為雜志的首席攝影師,而且一任就是13年。斯泰肯首創了“名人肖像”拍攝方法,以獨特的風格和品位將諸多名人的肖像,包括查理·卓別林和葛麗泰·嘉寶這樣的好萊塢明星的肖像登到了《名利場》中。在造就一批時代偶像的同時,《名利場》也為自己贏得了廣泛的關注。1928年,作為首席攝影師的愛德華·斯泰肯年收入接近3萬美元,而那時候紐約東區的一幢住宅也不過4萬美元。除了斯泰肯外,一些重量級的攝影人也被招入旗下,比如像擅長拍人物肖像的霍斯特,等等。
在斯泰肯的推動下,這些攝影家讓雜志的攝影插圖變得大膽自由,且富有創意。新雜志雖保留了《名利場》的原名,但在內容上做較大改進,宗旨以報道上流社會生活品位、宴飲聚會、藝術修養、體育幽默、明星軼事,只要能配照片的就盡量不用手繪插圖,是一本名副其實的“新面孔”雜志。
1914年,新《名利場》創刊號發表,并以月刊形式發行。當時的《名利場》雜志定位不是瞄準大眾,納斯特認為向往上流社會和向高生活水準看齊的人都有可能成為這本雜志的潛在擁躉,這是當時美國社會的風氣。在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早期,也就是1840年前后,英國的社會風氣也是向貴族及有教養的人看齊,狄更斯和勃朗特姐妹幾乎所有的文學作品里都反映了這個趨勢,這個于無形中的“名利場”起到了推動文化教育事業發展,民眾積極要求向上的主流行為。而此時的美國步人后塵已見端倪。從歷史的先例判斷,財富的大量積累必然導致文化的興旺,尤其是美國掙了些錢的新貴,對有品位的生活一無所知,《名利場》就像是一本“新生活”指南,吸引讀者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不過納斯特是個商人,或者最多是個被包裝起來的儒商,不是文人,更不是作家,辦雜志掙錢才是第一位的。他首創的“等級對應”方式,在《名利場》雜志的定位上率先實踐,順利地開始了自己的名利之旅。所謂“等級對應”,即根據讀者的收入水平或者普遍興趣確定雜志的讀者群,再確定時尚、政治、藝術、娛樂等各方面的內容,為讀者量身定制。這樣自己可以少一些浪費,讀者也可以提高閱讀效率,兩全其美。
辦雜志是徹頭徹尾的商業行為,至于一本雜志的社會效益和生存期到底有多久,納斯特并沒多想,這也為早期的《名利場》短命埋下了伏筆。讀過1913至193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出版的《名利場》的人現在已經很少,即使找到一兩個,他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總之,很難想象如果《名利場》的缺席會使今天的美國雜志界呈現怎樣的一幅景象。如今,《名利場》已經成為公認的美國最重要的雜志之一。它是造星工廠,是好萊塢的《圣經》,是華府政客的讀本,是文科研究生的重要課外讀物、也是追名逐利的蕓蕓眾生看世界的一個管洞,當然還是商業人像攝影師展示自己作品的流動影廊。
將近一個世紀以前,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由于歷史短,屬于自己的美國獨特文化尚在形成之中,所以富裕起來的美國人渴望了解世界,尤其是西歐;民間風氣崇尚成為優雅,有教養的人。他們向往歐洲特別是希臘羅馬厚重的文化傳統,富人以能到歐洲游歷為榮。不過遠涉重洋去開眼界、見世面的畢竟是少數,多數人只有通過閱讀書籍、報紙和雜志來了解世界,當然還有電影,可惜帶不回家。康德·納斯特正是把握了美國大眾的這一心理,適時推出《名利場》雜志,即便沒有達到轟動效應,但至少也讓人眼前一亮,覺得與眾不同。在整個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名利場》都是引領時尚的先鋒。它向讀者們介紹“正宗的生活藝術”,諸如爵士樂、文學、戲劇,以及這些領域的鮮為人知的幕后故事與未經證實的小道新聞;它記錄并推動了前衛藝術的發展,為有創意卻還沒有得志的攝影師提供施展才華的空間。
怎料1929年美國股市狂瀉,許多百萬富翁頃刻之間一貧如洗,曾經一度奢糜浪跡的生活突然變得遙不可及。當成千上萬的人步入失業者的行列時,《名利場》的前途不說自明,進入到舉步維艱的歲月。1936年,《名利場》宣布停刊。這個一度風光無限的雜志在經營了22年之后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取而代之是更加迎合大眾口味的《生活》畫報,這個結局連創辦人納斯特事先沒有想到,他雖然不是算卦師,但他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一個成功的雜志出版人,只是時運不濟而已。
無論如何,《名利場》作為一本綜藝和生活類雜志,以高水準的照片,特別是具有前衛風格的封面照為開路神(相比《生活》畫報的封面照,后者就非常老套,毫無創新之意),迎合準上流趣味,這個定位沒有錯,只要逢時,它還會卷土重來,事實正是如此。1980年代,美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又為《名利場》的鳳凰涅槃創造了條件。對于一個以時尚為主的雜志,后來的條件顯然比《名利場》初創時期的條件更加成熟,彩色攝影這時已經普及,比斯泰肯更有想法、更具前衛精神的攝影師輩出。不過,由于電視進家入戶,以及《生活》畫報的即將垮臺,使之插足雜志領域也更具挑戰性。1983年,美國傳媒巨頭紐豪斯收購康德·納斯特出版集團。雄心勃勃的紐豪斯決定將《名利場》復刊。雖然《名利場》曾經領銜時尚潮流,但今非昔比,要想使《名利場》重現昔日風采,除了有龐大的資金支持外,還要有能掌控全局的核心架構人物,即主編。在斥資上千萬美元,但市場反應并不理想的情況下,紐豪斯將目光投向海外,重金請來了英國的傳奇雜志人蒂娜·布朗做《名利場》的主編。這個習慣于在大床上看稿子,每個汗毛孔里都浸透著辦雜志好主意的英國女人,真的能在彩色電視機普及的時代扭轉乾坤嗎?人們拭目以待。蒂娜·布朗在牛津大學圣安妮學院學習時就開始了她的新聞生涯。她先是為一份校刊撰稿,后來又成為《新政治家》雜志的校園特約記者。25歲那年,英國老牌雜志《閑聊》邀請她出任該雜志主編。雖然這是一份有著300多年歷史的雜志,但因為形式陳舊,內容過時,已經沒有多少讀者。布朗接手后,借助英國王子查爾斯娶平民王妃黛安娜這一契機,對英國的上流社會、社交生活和時尚趣味進行廣泛深入的報道,使《閑聊》雜志搖身一變成為一份生動有趣且充滿時尚感的雜志,發行量從原來的1萬份飆升到4萬份。蒂娜本人也成為業界交口稱贊的傳奇人物。1984年,蒂娜正式擔任《名利場》主編,當時《名利場》的發行量只有25萬份,廣告量不足12頁,奄奄一息尚存。布朗從雜志管理、編輯方針、雜志內容和包裝等各方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在短短的時間內,她就解雇了一批只拿錢不出活兒的“前朝老臣”,并精心挑選組織了一個強大的人事陣容。對于雜志本身,經過仔細深入的研究調查,蒂娜·布朗給《名利場》開出了一劑靈丹妙藥:名人效應+引人入勝的報道+新聞敏感性=金錢。為了獲得高質量的文字報道,蒂娜用優厚的稿酬網羅了一大批一流作家,其中一些作家的薪酬合同甚至高達六位數。蒂娜堅信:今天的攝影已不是昨天的攝影,一流的照片必須選配一流的文字,否則的話讀者就會去選擇看電視。攝影和文字的高度契合,合二為一才是完整的稿件。攝影師通常文字水平不行,事實上也沒時間寫;而文字作者由于稿酬低又不愿意爬格子。照片是讓人看的,文字是讓人讀的,好照片加文字才能真正地留住鐵桿讀者。她打了一個比喻,說是英國的滑稽劇,其實就如同中國的相聲,侯寶林的表情再逗人,也不及他開口說話,否則的話只是個“半成品”。事實證明布朗是對的。1984年,《名利場》的一篇寫作技巧很高的深度新聞報道獲得了美國期刊界大獎“國家期刊獎”,《名利場》立即成為傳媒矚目的焦點,并迅速躋身一流雜志的行列。蒂娜·布朗的時尚雜志按新聞報道的路子辦;新聞報道的內容又夾雜時尚內容的手法;在攝影配圖的風格取向上大膽創新;甚至敢于擺弄好萊塢的大牌明星,面對讀者做出各種稀奇古怪的姿態,一般雜志只敢“尊重本人意見”拍攝,等等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確實令人耳目一新。不斷躥升的發行量表明,大眾對穿名牌時裝的好萊塢影星或政界名流,其關注度遠超過這件衣服罩在時裝模特兒那高挑而脫離現實的身材上。作為雜志的主編,她不放過任何有價值的新聞線索,尤其是有關名人的新聞。1985年6月號的《名利場》刊出里根夫婦相擁跳狐步舞的封面故事,頭條標題為《里根隨爵士起舞》。該刊一經出版立刻引起轟動,在報攤上的炙手可熱。從1984年到1992年的8年間,《名利場》先后四次獲得美國“國家期刊獎”,兩次被評為美國“最暢銷雜志”。有評論者認為,《名利場》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在于把握了80年代美國的時代精神以及和平時期,人們向往富貴安定生活的心理。
再好的戲也有收場的時候,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另外一位出色的雜志人卡特接手《名利場》雜志。同蒂娜·布朗一樣,戈萊登·卡特也是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外籍人土,《名利場》的投資人認為,對于一本外向型雜志,還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在渥太華大學求學期間,卡特曾主編一份同學創辦的刊物《加拿大評論》,并把刊物塑造成具有新共和風格的文化政治雜志。離開這份刊物的時候,該刊的發行量已經達到5萬份。1978年,卡特到紐約發展,受聘為《時代》雜志撰稿人。1985年,卡特和另一位《時代》的同人共同創辦《間諜》雜志。這本專揭名人隱私的雜志以辛辣的諷刺和旁門左道的見解做為切入點。雖然雜志在6年后因財政狀況不佳而被出售,但卡特卻通過主編這份雜志而成為美國雜志名利場中的驕子型人物。與蒂娜不同的是,卡特并不喜歡將自己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中。他接手后更愿意讓《名利場》成為人們談論的中心,而他自己卻不被人知。他的目標是要讓《名利場》不但擁有忠實的讀者群,還要具有更廣泛的影響力,成為“當前文化的主流雜志”。坐鎮《名利場》,卡特保持了雜志原有的風格,并努力使其完善,盡量做到圖片、文字到版式設計都是一流的,具有獨創性的。在這方面,《名利場》可謂一擲千金,但稿酬的具體細節雜志向不公開,據傳說,《名利場》首席文字寫手的年薪高達40萬美元;而《名利場》同期聘用的美國著名女攝影師安妮·萊博維茲的5年期合同金額更多,達幾百萬美元。雜志的照片從封面到插圖都拍得一絲不茍,美國本土名人自不必說,好萊塢大腕更是一個不落。境外拍攝不惜血本,只要策劃通過,多遠都去。優厚的稿酬和慷慨的投資自然物有所值。在1992~2003年間,《名利場》共獲得6項“國家期刊獎”。在內容上,《名利場》以報道名人私生活尤其是當紅好萊塢明星為主,特別是每期的好萊塢明星照,事先保密,一旦刊出絕對令人大呼驚奇,不是怪姿勢,就是怪表情,要么就是怪誕奇異的組合。這樣的安排,對于中國的電影明星是不可想象的,因為能約到她們拍攝本身就很不容易,再讓她們聽從攝影師的擺布,做出“難看”的表情,追求品相完美的中國演員當然不會。但雜志也不局限于好萊塢的艷事秘聞,撩情艷照,它也關注社會突發事件和熱點問題。2001年“9·11”恐怖襲擊發生后,《名利場》立刻派寫手到襲擊現場進行采訪,跟蹤事件進程,雜志寫手明顯高于一般的文字記者,其文字和聯想水平根本就不在一個等級上,記者寫出來的是消息,寫手寫出來的是文章。丘吉爾和海明威早先都是文字記者,也都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們經歷的就是從記者到寫手,再從寫手到作家的發展過程。寫手寫出的“9·11”紀實報道果然不同凡響,蓋過一般媒體,成為雜志一大賣點。這樣一本融合了時尚、政治、名人、金錢和社會新聞的雜志,不但普通人愛讀,社會名流和知識分子也愛讀。而廣告商更是看中了《名利場》的讀者群:他們平均年齡37歲,當時平均年收入5.8萬美元,70%上受過大學教育。這樣的讀者群正是廣告商心目中理想的消費者對象。卡特經營下的《名利場》不但發行量繼續增加,而且廣告投放量也增加了60%,達到了每年近1900頁,收入超過1億美元。
要將雜志做大做強,光憑一本雜志本身是不夠的。卡特充分利用雜志的社會資源,發展其在娛樂界和政界的影響力。通過每年奧斯卡頒獎典禮結束后的名流宴會,以及每年白宮記者聚餐會,現場推介《名利場》,極力打造獨此一家的“明星級”刊物。通過卡特10年的經營,《名利場》無論是在聲望、影響、地位,還是帶給出版商的利潤方面都比從前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近兩年美國平面媒體受網絡沖擊并不景氣,但《名利場》依然是紐豪斯媒體集團中最賺錢的雜志之一,也依然是傳媒、娛樂和政界追名逐利的舞臺和普通大眾欣賞名利中人華麗人生的看臺。作為附屬產品,《名利場》雜志的名人肖像照展覽也成了世界各地的畫廊及美術館經常展出的內容,吸引看客無數。一個在歐美文化圈里混的人想要出名,不在《名利場》中占上幾個頁碼,就不配算是名人,這幾乎成了一條行內潛規則。
如今辦雜志絕對是個系統工程,一好兩好還不成,必須面面俱到;從基礎到立柱再至上層結構,差一點兒都不成。如今的雜志人,不光要懂平面媒體,還要熟悉網絡技術與新傳媒傳播方式,見風使舵,遇彎截角;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玩到極致,方可在雜志的名利場中應付自如,《名利場》的昨天和今天已經證明了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