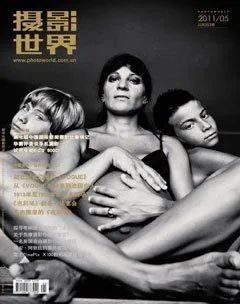“本質直觀”
俄國形式主義藝術理論認為,藝術不是外在世界的直接模仿,而是通過藝術語言和技巧,使那些平常我們熟視無睹的對象變得陌生,從而延長我們感知對象的時間,激發我們認識對象的欲望。
如果我們從這一立場考察程玉楊的攝影,那么我們就會發現,程玉楊在多大程度上也使我們司空見慣的世界變得陌生和不可思議。為了達到這一視覺效果,程玉楊采取了兩種在我看來極其有效的方法,一是在攝影技巧上,程玉楊不僅把負像作為正式的攝影作品來對待,而且還采取了技術難度較大的連續上下左右的單拍和組合,以擴展攝取對象的范圍和觀看的視覺空間。這種手法的優點是,它不同于廣角拍攝會使對象彎曲變形;二是在每幅負片的連接中,用一白線把它們進行既連接又阻隔的組合。這一方式既彌補了每一單幅負片在連接中的錯位,與此同時也因這些不影響整體的錯覺感受的錯位、重疊、晃動和曝光的差異而加強了作品的整體感、形式感,以及與對象的距離感和陌生感。
程玉楊利用攝影中的負像及其組合創作作品,在視覺上無疑顛覆了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不過必須看到的是,程玉楊只是把此作為手段,目的是讓我們在一個陌生的視覺世界中,重新觀看、審視和反思我們早已熟知而變得麻木不仁的世界。
程玉楊喜歡拍攝兩種題材,一種是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的皇宮建筑,它們象征著統治階級的權力和富有,如《故宮一角》、《頤和園系列》、《九龍壁》、《天安門系列》、《圓明園》等;另一種是拍攝城市居民居住的胡同、鄉村農民居住的水鄉和村落。事實上,程玉楊拍攝的兩類對象,基本上代表了中國傳統社會中兩個相互依存和對立的階級。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程玉楊拍攝的這些對象仍然與我們同在,而從那些墻上寫著“拆”字的胡同,人群走動的天安門來看,程玉楊的立場應該不只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或為即將消失的民居攝像存檔,留下可供后人觀賞的歷史文獻,而是為了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建立一種內在聯系,以揭示現代社會的本質。我這樣說的理由是,如果用正片拍攝這些對象,那很顯然,其視覺效果和文化傾向與懷舊的老照片或美麗的風光片有區別,這大概就是當下視覺藝術和文化的上下文,是導致程玉楊用負像拍攝作品的原因。在我看來,程玉楊這批攝影作品的意義也在于此,即他成功地抵制了用正片拍攝這些對象的誘惑和淺薄,而采用負像及其富有藝術性的多幅組合,把我們引入一個陌生的世界,讓我們去重新反思和審視支撐這個世界和社會的深層結構,以達到直觀本質的目的。
從攝影史的角度看,程玉楊也在一定意義上改變了攝影的出發點,因為照相機模仿的是人的眼晴,目的是使照片中的物象與我們看到的世界完全一致;但很顯然,程玉楊用負像攝影顛覆了發明照相機的初衷和起點,從而為哲學家胡塞爾所說的“本質直觀”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
(本文作者系著名美術理論家、藝術批評家、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主任、美術理論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