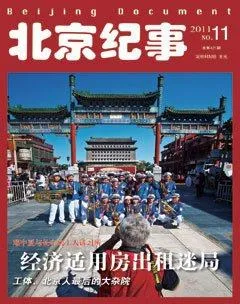天安門\\密云的空間感及追求博大純粹的“北京精神”
看了2011年7月1日《北京日報》刊登航拍的天安門為中心城區全景照和反映密云縣新貌照片,不禁對最近熱議的“北京精神”有所聯想。從照片中誰都能看到北京歷史文化的厚重和輝煌,一個是城市中無與倫比的地標,一個是充滿歷史滄桑的“邊關”,是我們要尋找的精神內涵。
天安門是什么地方?它是共和國兒女心目中的圣地,你一生可以不去別的地方,但如果沒有到過天安門肯定會感到遺憾。許多年以前,我們到外地時總愛自報家門:咱是北京人。人家往往會提起天安門,因為在新中國,圍繞著它發生的影響民眾的政治文化大事實在是太多了。50歲上下的北京人都能發自內心地哼幾句“我愛北京天安門”,誰家都會有幾張老少三代在天安門前的全家福。國慶節前夕,朝陽區文化館推出了匠心獨具的“集體的影像記憶”主題照片收集展——我愛北京天安門。從朝陽區1000多個市民家庭中征集、精選的500幅天安門留影,陳列在798藝術區的玫瑰之名藝術中心。
天安門廣場西邊的人民大會堂,每年的“兩會”討論國計民生,話題舉世關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一大政治特色,體現了幾代革命家的理想。廣場東邊的國家博物館正在舉辦辛亥革命名家墨跡展,孫中山的墨寶“天下為公”“共和”“博愛”就是一種革命精神的彰顯。幾個月前,國家博物館搞了“LV藝術時空之旅”和寶格麗的展覽,社會質疑聲不斷。有博文說:“一個只有上百年歷史的商業品牌都有著文化的含量和傳播的意義,中國數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所留下的文物,還不夠擺滿這座世界第一大博物館的展廳嗎?國家博物館自身的收藏就有近百萬件,雖然不是所有的收藏都適合展出,但目前展出的似乎也不足百分之一。”的確,國家投資25億改擴建的博物館,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精神。“北京精神”的表述語——愛國、創新、包容、厚德,在評選中受到北京人的普遍認同,就是反映了這座城市所蘊含的積極健康的文化風骨。
還說辛亥革命,首義雖然在湖北武昌,但北京自元明以來一直是我國的政治中心,清末民初北京政局直接制約和影響著全國的變化和發展。孫中山一生三次進北京,第一次是1894年,看透了滿清的腐敗,下定了武裝革命的決心。第二次是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虎坊橋湖廣會館主持成立中國國民黨。第三次是1924年底,12月31日下午4時30分,孫先生乘火車到前門火車站,北京學生、市民各界10萬人迎接。1925年3月12日在京病逝,4月2日靈柩移往西山碧云寺,北京幾十萬人自發走上街頭送行。
另外,在北京的近代史上還有一位在文化和思想上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梁啟超先生。他最先發現了我們民族的劣根性:缺愛國心,少獨立性,乏公共心,虧自治性。對民國北洋政府、國會的亂象,說出“問今日欲強中國,宜莫急于復議院,曰,未也。凡國必風氣已開,文學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說議院”的斷語。提到當時的議會政治,又不得不說說國民黨的先驅人物宋教仁,他試圖在中國實現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度。1913年,就在他滿懷信心赴京組織國民黨內閣時,被袁世凱派人刺殺于上海的滬寧車站,年僅31歲。這個起草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即憲法草案)的政治家,因為曾任農林總長,在現在的北京動物園,過去的“萬牲園”辦公。后來,這里有個“宋教仁紀念塔遺址”,他的墨寶是:“白眼觀天下,丹心報國家”。
河北人民出版社《宋教仁與民國初年的議會政治》(1998年8月第1版)一書評論:宋教仁的被暗殺,已在客觀上證實了資產階級議會政治,即共和政體權力結構宋教仁模式的虛幻性。揭開這一模式的虛幻性,透析活躍于中國政治活動中的典型角色由夢幻成真而又真成夢幻的規律性悲喜劇過程,可以發現其背后有一個嚴肅的政治主題,即20世紀的中國,沒有資產階級議會政治存在的社會基礎和政治生態環境:議會型的兩黨或多黨自由競爭制在中國根本行不通。它還從一個歷史側面有力地證明了: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是經過歷史淘汰的結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符合我國國情的一項根本的政治制度。
推翻封建王朝已經過去100年,國家走上了復興之路,很多人對過去的苦難逐漸遺忘。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是民族不屈不撓的偉大精神捍衛了這片熱土。我們只有了解過去的生存狀態,才知道今天和平美好生活的可貴。
北京的密云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提起“漁陽”“檀州”,便是打打殺殺的故事。1980年春天,高中臨畢業前半年到密云的穆家峪植樹一個月,聽了好多楊家將、穆桂英和明代戚繼光守長城的傳奇。1969年,中蘇邊境我們解放軍進行自衛反擊戰,北京在挖防空洞,我們這些小學生在議論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線,就說到距北京130公里的密云古北口。因為它與山海關、居庸關同為古代北方和東北少數民族進逼北京、南下中原的三大要道,素有“京都鎖鑰”之稱。附近有紀念楊令公的楊業祠,楊業當年舉家拼死一戰,氣壯山河。中國幾千年來戍邊將士的血液里的愛國情懷是我們所不能忘記的。30年前,密云山區到了春天要鬧饑荒,人們的記憶里就一個字“餓”,一天就一頓還是粗糧。我們學生有白饅頭,吃不完就給那些爬到榆樹上擼新葉子吃的孩子,他們都是50年代建密云水庫時的移民。旅游書這樣介紹,密云水庫宛若碧玉鑲嵌在燕山群峰環抱之中,是北京人飲用水的主要來源。為了這一池凈水,無數的農民背井離鄉,犧牲了自己的利益。
或許你沒注意,半個世紀前的感人事跡還在發生。最近,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同志為在南水北調工程中無私奉獻的河南人民深情賦詩:
南水北送真輝煌,最動情是離故鄉。
清水滋潤京城日,共贊豫宛好兒郎。
《人民日報》2011年7月13日發表報告文學《南水北調進行時》,用了兩個有點“聳人聽聞”的小標題,一條是“渴、渴、渴,很多人看不到”。說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興建的密云、官廳、懷柔、海子四大水庫,總庫容88億立方米。到了2011年年初,北京最大的水源地密云水庫的蓄水量不到總庫容的四分之一,官廳水庫更可憐,只有總庫容的4%。北京從什么時候開始缺水的?很難說清楚,反正1949年,北京人口220萬,人均水資源量達1800立方米。現在,北京已經是世界上缺水最嚴重的特大城市。目前,每年缺口10億立方米。另一條小標題是“京津冀一杯水,移民幾滴淚”。為了北京人有水喝,工程要移民34.5萬人,他們扶老攜幼,背井離鄉,失去了祖祖輩輩辛勤耕耘的土地。這是一種充滿悲情的奉獻,也是中華民族優秀精神的延續——為了大我舍了小我。
飲水思源,這水來之不易,我們這些天天離不開水的城市人,該知道珍惜這看似最廉價的資源了。愛國、愛北京,不是一句空話。愛護地球,善待生命,也是實實在在的“北京精神”。
(編輯??麻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