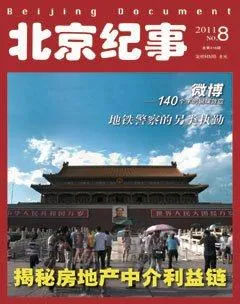載沉載浮的房產經紀人
2011-12-29 00:00:00趙博淵
北京紀事 2011年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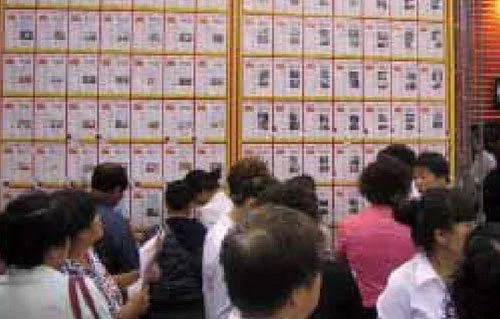

作為共和國的首都,北京的國際形象與經濟發展舉世矚目。近年來,城市建設更是日新月異,開創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
從北京的建設發展來看,成績當然是主流,與改革開放前相比,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逐漸樹立了一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形象。但是,這樣的快速發展也勢必帶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不可避免地構成一些不和諧音符,貫穿在建設的全過程中,盡管瑕不掩瑜,可它的影響力和破壞力卻是巨大的。
房地產中介的前塵往事
北京的房地產業同全國一樣,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很短,因而房地產市場自然不很規范。近幾年來,超高速發展使得管理和法規制度相對滯后。
打著跟頭上翻的房價不僅造就了一大批暴富炒家,也帶火了京城的房地產業以及一大批相關的行業,隨之又衍生出諸多急于分享盛宴的大軍沖殺進這個大市場。虛火上升必將導致泡沫經濟,泡沫經濟必將影響普通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上層瘋狂追逐暴利的財富巨頭和大部分望房興嘆的工薪百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房地產業是個大市場,要想面面俱到地解讀它是不可能的,出于興趣,筆者想試著論說下房地產中介行業,說得對不對,權作為茶余飯后的談資吧。
對房地產市場而言,中介無疑是最有利于市場發展的行業之一。然而無論北京還是全國,最為人們詬病,形象不佳、口碑最差的也當數房地產中介。
房地產中介古來有之,而且從來也不是為老百姓所褒揚與推崇的行業。舊時代老北京有句比較刻薄的俗諺:“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這話說得有些一桿子打倒一船人的嫌疑,可其中也有一定的理由,因為這五大行當中都有許多人經營著傷天害理的勾當。而所謂“牙”行就是指平地摳烙餅,一手托兩家的“說合人”。
舊時的房地產(主要是指房屋)中介不需要資金投入,只憑消息靈通及一張好嘴便可撮合房屋買賣雙方,待成交后收取中介費,從中得利。解放前最通俗的叫法,是管這些人叫“拉房纖的”“纖手”“房牙子”,改革開放初也有“房倒兒”“房蟲子”等稱呼,只是都屬不太光彩的小名。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重塑形象改成集團作戰,又從香港引入了新名稱新包裝,才改稱為房地產中介或經紀公司,纖手們也搖身一變成了經紀人。當然,他們的被認可還需要持有上崗證,是合法的具有國家資質認可的職業經營者。
清代京城一些文人喜歡以打油通俗的方式創作竹枝詞,有首竹枝詞是這么說的:
幾張契紙幾間房,才有風聲便著忙;
破二成三分歉賬,誰知事件尚荒唐。
這首小詞算是給拉房纖的白描了一下。
舊社會的纖手們大多是耳朵長、嘴6DHWgIBFv5EjWNctjEhmutIVvxNwkpY0pTS8G5wfZ6k=兒勤、腿兒勤,好打聽事、“撮合事”的消息靈通人士,雖說許多人不是專職干這種買賣的,可他們會隨處留心,不拘鬧市大街小胡同,茶館酒樓澡堂子,有點兒風聲就會窮追不舍。行內纖手間也會經常互通情報,利益均沾。特別是對一些官員升遷謫貶放外任,“宅門”婚喪嫁娶討小都要心中有個數兒,信息絕對是他們的第一生命。腿兒勤就是要落實信息,多跑道兒,多問多看多打聽,有時還得出點兒血,拉攏人脈,打通關節,掌握最準確信息。一樁買賣如果能攥住上家兒當然最好,可這種機會并不多,因此必須迅速找到下家。這時候巧舌如簧盡管很重要,能不能快速成交也就要看個人的本事了,否則心思沒少費,讓別人捷足先登那就只有生氣干瞪眼的份兒了。因為拉房纖的既沒錢又沒房,靠的是給買賣雙方撮合成功才能掙到錢。
不過對于買房人與賣房人來說,卻也大多離不開拉房纖的。房屋在舊社會也是大宗交易,買賣雙方大都素不相識,很難相互信任。特別是一些有頭有臉的人,需自恃身份,不便于面對面地相互討價還價,這些事情通過纖手們完成就方便得多。他們都是這里面的蟲兒,且事先都進行了詳細打探,只要不是刻意隱瞞或做好了“局”,交給他們進行,相對可以放心一些。買房的當然要關心欲購房產的狀況,比如房屋四至、房產來源,是否有官司糾葛、是否有鄰里爭議,家庭或家族間有沒有矛盾糾紛,房子的年代質量,包括房子是不是干凈(指有無兇殺自盡狐鬼鬧騰)等,這些就要靠拉房纖的踩探打聽和全方位的“白話兒”一番。
如果是宗大買賣,成交時的場面也很隆重,口說無憑,要當場立契付賬方算成交。所謂的“房(地)憑文書官憑印”,場合一般會選擇在飯莊或飯館內,交易雙方、中人(纖手)、保人等諸多人眾目睽睽之下寫成契約文書交割清楚,算是“齊活”成交,然后自然會有頓大餐招呼。小宗生意也免不得要經歷這樣一個場面,只是規模小些,酒飯總是少不了的。所以,拉房纖的如說:這檔子生意只是“抹抹嘴”,即表示沒掙著錢,僅蹭了頓飯而已。
由于房屋買賣過程較長,未知因素較多,一宗交易可能會由多名纖手共同完成。這類人又不是專職的,良莠不齊,弄虛作假、坑人詐騙的事情也就時有發生。舊時所說的“倒騰房”,建好后出售時也多要借助纖手們的協助。
前面竹枝詞里說到的“破二成三”也稱“成三破二”,是指纖手們收取的費用。意思是說出資買房(成)者要拿出房價的百分之三,賣房(破)者拿出房價的百分之二,作為中費,酬勞居間說合聯系的中人們,也就是拉房纖的各位,然后再由纖手們自行分配。這也可視為那個時代的“潛規則”或行規吧。
新中國成立后,拉房纖的被當作舊社會的殘渣余孽“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據統計,至解放時,北京專兼業拉房纖的約有5000多人,其中專業的大約1000余人。一份官方的材料中是這樣描繪房纖手的:他們成分復雜、良莠不齊,敵偽官吏、逃亡地主、漢奸特務、地痞流氓混雜其間。少數大房纖手控制著十幾個以至幾十個小房纖手,敲詐欺騙、威脅勒索群眾。如所謂的西霸天鐵嘴鋼牙胡美林、北霸天坐地分贓習少朋、南霸天鐵頭劉四、東霸天小諸葛白奎珍等,便是這一類大房纖手的代表人物。老北京這四位臭名昭著、橫行一方、欺男霸女的地痞惡霸“黑社會”也被歸入這個行業,可見這潭渾水有多深了。
北京市政府在解放初即對房纖手這一行進行了嚴厲打擊,1951年4月13日,北京市政府發布了(府交字第一號)關于取締房纖手的布告,規定“從布告之日起,不論廣告社、服務社、店鋪或個人,均不得再有借說合房屋為名索取纖費或其他任何費用,違者定予嚴懲”。在此期間,政府依法傳訊和逮捕了50多名房纖手,其中29人被判了刑。
北京拉房纖的自此絕跡了30多年的時光。
從屢禁不絕到風起云涌
解放初期,北京市的私房還占有絕大比重,但隨著一次次的“運動”及新中國的建設發展,私房量銳減。特別是史無前例的“文革”,私房被全部消滅。“文革”結束后,“落實私房政策”被確定為撥亂反正的一項政策,房產主的私房在有可能的情況下陸續發還。在這樣一個長過程中,國家大力推行的是建設住房福利制分配制度,致使絕大部分房屋都成了公房。但那些“拾遺補缺”的私房也依然需要進行買賣和租賃,為此北京市相繼成立了房屋交易所和房屋管理所(解放初成立的房屋交易所存在時間并不長,與改革開放后再次設立的房地產交易所不是同一機構),買賣和租賃需由這些部門進行,個人參與或說合交易租賃,并收取好處費的,面臨的將是嚴厲打擊和牢獄之災。
這樣平淡和安穩的狀況保持了20多年。解放初大力鼓勵生育的新生代長大成人,需要結婚或分房另過,而且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也大量增加,城市的住房就成了最突出的矛盾。盡管國家解放后也陸續新建了一些住房,但與需要相比,則好似杯水車薪。在上世紀80年代進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中,統計顯示北京市的住房困難戶就已經達到40多萬戶。
為利用有限資源,盡可能地解決北京老百姓的住房困難,1980年北京市成立了房屋調換總站,各城區設有分站,每年的秋季都會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一次全市性的換房大會。大會期間,人頭攢動,盛況空前,給許多群眾解決了一定的困難。但這樣的做法只限于調換調配,解決的是上班路遠、交通不便、分家另過、鄰里不和等矛盾,治標而不能治本。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首都建設的發展,上世紀90年代末,換房大會沒有了生命力并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不過這種由官方組織,讓房屋供需雙方見面洽談的方式卻被沿襲下來,發揚光大,那就是至今依然火爆,并極大地促進了市場發展和買賣交易的房地產展銷會。
拉房纖這一行業的死灰復燃是伴著改革大潮而出現,并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逐漸發展起來的。大大小小的“房倒兒”們也從開始的熱心幫忙蹭頓飯發展到收取高額回報,從在私房上打主意發展到倒賣公房使用權。
這也引起了政府的警覺和重視,1991年北京市政府針對非法出賣、購買和倒買倒賣公房使用權日益嚴重的情況,由市房地產管理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公安局三家聯合進行打擊,并根據國務院《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北京市人民政府《關于查處非法買賣公有房屋使用權的規定》,發布了限期通告,限非法買賣公房使用權的單位和個人于1991年12月31日前,到有關部門主動坦白交待違規事實,并退還非法所得。之后,北京市工商管理局會同北京市房地產管理局又聯合發出公告,要求凡在北京市行政區域內,專門從事房地產交易中介、信息、咨詢活動的企業,一律取消;其他企業的經營范圍中,有此類項目的也一律撤銷。
然而出乎這些主管部門意料的是,這次“聲勢浩大”的打擊活動并未收到預期的效果,這幾乎是自“文革”后老百姓反應最為平淡的一次活動。到了大限截止日期,三局總計接到舉報電話和來訪150起,涉及樓房387套,平房32間,主動坦白的個人31起。頗為尷尬的三局再次發出了聯合通知,將坦白登記期限延長至1992年2月29日,并決定對在限期內主動登記、提供有關情況、居住確有困難,無其他違法違紀行為的非法購買公房使用權的單位與個人,已占用的公房可以不騰退,準予按規定辦理合法承租手續。并對檢舉揭發重大案件的有功者,給予1000元?5000元的獎勵。
1992年4月,北京市的幾個區分別召開了由法院負責的審判大會,對一批倒買倒賣公房使用權者判了刑,只是法律制裁的主要是居間牟利的倒房者。審判根本沒有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公房使用權的買賣者沒有受到多大觸動,只是稍稍有所收斂,而私下拉房纖的居間經紀人更是沒有絕跡。
讓北京市這次經辦打擊活動的主管部門始料未及的是,1992年初從沿海城市刮來的房地產熱潮,迅速升溫,到下半年便幾乎遍及全國。到1993年初,大力興辦開發區、炒房炒地炒樓花的熱炒房地產成為不可遏制之勢,房地產開發公司、經紀公司、中介公司也如雨后春筍般地冒了出來。北京市取締房地產交易中介、信息、咨詢企業的限制令也成了一紙空文。到1993年下半年,國家為穩定經濟發展,采取了經濟宏觀調控措施,抽緊銀根,房地產開發建設開始降溫,而涉及到房地產領域的各種體制的公司大多數還是保留下來,房地產熱中的那些原沒有經濟實力甚至是“皮包”經營的公司紛紛轉向了房地產咨詢中介領域。
1992年的房地產快速升溫是中國經濟歷史上的一次機遇,北京打擊“房倒兒”是自1951年打擊“房纖手”后的最大一次行動。這次意外的相交與碰撞是否也有其內在的規律,恐怕誰也說不清,但新時代的“房倒兒”“房蟲子”們卻是意外地逃過了一劫。
招商引資、“筑巢引鳳”催生出了1.5萬平方公里的開發區,開發商忙了,居間說合的經紀人也就更有事可做了。無數下海的“皮包商”只是夾著一紙合同、一枚公章和一肚子的真假信息游走于南北房地產市場。盡管如此,他們中一大部分人不僅能維持生計,也有的確實發了大財。
對于剛剛起步的土地有償使用、住宅商品化的內地大市場來說,唯一可資借鑒的就是香港的房地產運行模式。土地開發吸引來大批港商,他們的經營理念、經營方式自然會留下烙印。老“房倒兒”們突然間明白了一個道理,與其整日里擔驚受怕地單兵作戰,為何不能聯合起來辦個執照,照章經營、合法納稅,既掙錢又少擔風險呢?以往不能這么做,是因為工商部門門檻很高限制極嚴,但自房地產熱后政策放松,于是一大批房地產中介公司也就應運而生。
只不過從1993年下半年開始的房地產宏觀調控徑直延續到本世紀初,大部分房地產開發公司在勒緊褲帶過日子,中介公司雖然日子好過些但也是歷盡艱難。不過于艱難中聊以欣慰的是,行業較從前規范了許多,企業制度相對得到了完善,從業人員的業務能力也有了較大的提升。
月盈月虧,潮起潮落,市場也概莫能外,近二三年房地產熱再度席卷京城,所不同的是,此次的熱是以土地價格和商品房價格飆升為顯著標志。拋開其他不說,房地產開發企業大約可以視為此次熱潮的推手和最大獲利者,其次就當數中介行業與金融行業。而房地產中介不僅能從價格高漲的商品房市場分得一杯羹,在同步上漲的二手房市場和租賃市場上也同樣獲益匪淺。這也就難怪在北京的大街以至鬧市的顯著位置上一家家的房地產中介店面不斷地開張營業,一些特別喜歡裝修“變臉”的小飯館、發廊、食品店,也紛紛改頭換面化作房產經營或連鎖經營的中介門店。
回顧北京市房地產中介的歷史,可以說是部歷經坎坷磨難的發展史,商品社會需要這個行業,它也就有了存在的價值,只不過如何存在,以何種形式存在,則要取決于上層建筑和經濟發展的要求。中介是一個健康健全的市場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別是房地產業這樣的大市場,它對買賣雙方既能起到聯系與溝通的作用,也能起到監控與指導作用。不可否認的是,房地產中介行業存在著不少的問題。封建社會中游走于產業邊緣難以被認可的“房牙子”,只用了20多年的時間便成為遍地開花且為買賣雙方所依賴的經紀人,不說是華麗轉身也可說是艱難轉向了,只不過在華麗外表下還會隱藏著許多這個行當與生俱來的缺陷及不足。不過歷史在發展,房地產業在發展,經紀人行業也在發展。通過行業外部及內部的監管整頓和完善,它一定可以為進一步滿足城市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提供更好的服務。
(編輯??麻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