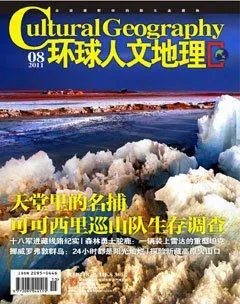陜北磚井鎮(zhèn):那些住在長城里的人
2011-12-29 00:00:00李建增
環(huán)球人文地理 2011年8期







陜北榆林地區(qū)是一個讓人驚嘆的地方,因為從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zhàn)國開始,歷代王朝幾乎都在這里修筑過長城。時至今日,地處黃土高原與塞北草原接壤地帶的榆林,共存有6個歷史時期的長城,是我國長城最多、最集中的地區(qū)。
這里最有意思的景觀是這樣形成的——由于陜北榆林靠近內(nèi)蒙古沙漠,每到春秋季節(jié)便黃風四起,沙塵漫天,長城自然也就成為了這里的人們生活居住的一堵天然“擋風墻”,于是,數(shù)百年來,當?shù)乩习傩站桶阉麄兊淖∷案G洞”,直接挖到了長城上,從而形成了一道“民居和城墻”渾為一體的景觀。
在當?shù)厝丝谥校L城被稱為邊墻,而挖在長城上的窯洞,則被叫做“邊墻窯”。榆林市定邊縣的磚井鎮(zhèn),是邊墻窯數(shù)量最多而且比較集中的地方,非常具有代表性,筆者曾經(jīng)數(shù)次帶著相機,來到磚井鎮(zhèn)拍攝那些邊墻窯,力圖用影像記錄下窯里人們的生活點滴。
磚井鎮(zhèn),軍事要塞的滄桑變遷
磚井鎮(zhèn)是明朝成化年間(1465-1487)修建的古鎮(zhèn),是陜北明長城38個營堡之一。2007年國慶節(jié),我第一次來到磚井鎮(zhèn),當?shù)乩相l(xiāng)帶我前往橫貫古城的長城腳下,拜訪了一戶還在使用邊墻窯的人家。
那其實是一家淳樸好客的陜北人,聽我說明情況之后,男主人就熱情地讓我住在了家里。他家的后面便是長城,沿著城墻有一排整齊的邊墻窯。而女主人此刻就正在窯里做飯,聽說我是專程來了解邊墻窯的,就拉起了家常:“前兩年,這一帶的邊墻窯里住的人其實很多,但是,這幾年生活條件好了,家家都蓋起了新房,大家基本上都搬出去住了,如今住在邊墻窯里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原因有兩個,一是老人們習慣了這樣的環(huán)境,二是邊墻窯冬暖夏涼,住起來的確很舒適”。
實際上,現(xiàn)在絕大多數(shù)邊墻窯都成了放置雜物的閑窯,我居住的這家人,從去年開始便把邊墻窯當作了廚房。不過,近些年來這里參觀的人比較多,窯里偶爾也會住人,前些日子窯里就住過兩個北京人。當我提出“能不能讓我也在里面住上一晚”的時候,女主人趕緊搖頭說:“不行了,閑置時間太長,放置的雜物也多,不能住了,再說現(xiàn)在條件好了,你是客人,怎么能讓你住在這閑窯里呢”。
安頓好行李之后,我?guī)е鄼C從房東家的豬圈墻登上長城。站在一處最高的城墻上望去,遠處灰茫茫一片,樹木也稀稀疏疏,沒有水也看不到山,厚厚的土城墻圍成了一圈,城墻上除了自然侵蝕的印跡外,還留有許多人工挖鑿的痕跡,比如廢棄的窯洞、放蔬菜的菜窖、豬羊圈、柴火垛以及被挖開的豁口……在土城墻里面,是平整的農(nóng)田,有農(nóng)民吆喝著牛在犁地,而孩子們則在城墻上追逐嬉戲。城墻腳下,四處堆著厚厚的沙土,有些地方的沙已經(jīng)侵襲到了城墻的半腰上。城墻上的那些城磚,也早已經(jīng)被拔得一干二凈,不過,土墻上仍然留下了一層層城磚的痕跡,仿佛在訴說著古城昔日的偉岸。而明長城從土城墻邊擦肩而過,慢慢地消失在遙遠的天際……看著這一片凄惶的景象,一首辛酸的民謠在我耳邊響起:出了邊墻豁口子,一望無際盡沙子;離別家鄉(xiāng)出邊墻,兩眼不斷淚流長……
下了城墻,我朝著城外翻地的人們走去。因為風沙大,婦女們的頭上都圍著厚厚的頭巾,一位婦女看見我在拍照,就羞澀地轉(zhuǎn)過臉去,說:“我們農(nóng)村人渾身土,滿臉灰,被太陽曬得粗皮黑肉的不好看,不像你們城里人,別照我”。“其實哪里的人都一樣,我也是農(nóng)民的后代,再說了,太陽曬了健康,皮膚厚了防風”,聽我這么說,她笑了,一邊掄起鐵鍬拍打著翻起的沙土一邊說:“旅游還是城里好,這里有什么好看的”。我說:“這里有長城和這個古鎮(zhèn),還有長城上挖的窯洞,好看,有意思”。她說:“我們家原先也住在長城的窯洞里,前幾年蓋了新房子就搬出去了,就在你去的那家的前面”,說著,她用手指了指城墻豁口外的一座房屋……拍了幾張照片之后,臨走時我問:“你們怎么在這個時節(jié)翻地,這里準備種些什么”?她說:“這里沙很大,只能種向日葵”。
當我離開揮鍬揚沙的她走到城墻豁口時,她在背后沖著我喊了一句:“你應該秋天來,那時候葵花都開了,黃燦燦的一片,那才好看吶”!
邊墻窯,民居與城墻融為一體
磚井鎮(zhèn)修筑的時間是在明朝正統(tǒng)二年(1437年),它的得名其實很簡單——因為附近有用磚砌成的水井。應該說,這并不是一個太大的鎮(zhèn),整個磚井鎮(zhèn)由黃土夯成,四周再砌上城磚,形成一個四方形的城池,城池雖然不大,但卻四四方方很是規(guī)矩。當時,這里建有樓鋪11座,城門4個,東邊的叫“靖東門”;西邊的叫“寧西門”;南邊的叫“南安門”,但是北門的名字現(xiàn)在卻沒有人知道。
許多年前,磚井鎮(zhèn)是當時重要的軍事重鎮(zhèn)。但現(xiàn)在,城墻上的城磚已經(jīng)被當?shù)剞r(nóng)民拿去建房、壘圍墻,甚至修牲口圈,4個城門也被毀成了豁口,除了城垣之外,城內(nèi)原有的建筑都隨著歷史的變遷而化作烏有,人們把城里平整后種上了莊稼。
我在磚井鎮(zhèn)的第一次晚飯很有意思,左鄰右舍都來了,大家坐在炕上,一瓶老酒、幾碟小菜,拉開了話匣子。房東叫薛庭廣,祖籍是延安吳旗人,從他爺爺開始便在這里居住,家族里三代人有近40口在邊墻窯里出生,1997年,薛庭廣家建了新房,就開始慢慢地搬出來了。老薛說:合作化(上世紀50年代)前,邊墻窯里住的人最多,到后來就少了,現(xiàn)在東關(東城門方向)基本沒人住了,只有西面有幾處還在住人。
那個夜晚,大家你一句我一杯,說了很多關于邊墻的舊事,喝了不少老白酒。老鄉(xiāng)們很熱情,說我是客人,輪著給我敬酒,說著、喝著,在酒精的作用下,我感覺自己似乎頭枕著長城睡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按照老薛指的方向行走拍攝。同東關相比,西關的地勢明顯比較寬闊,邊墻窯也比東關多。這些邊墻窯大都是三孔,多為一進兩開式——從中間這個窯洞進去,窯洞的左右兩邊各開一個過洞,由過洞進入兩邊的窯洞,三孔窯洞里,只有中間這孔有門,其余兩孔只是安裝了窗戶。由于窯洞數(shù)量多,所以用途也就很廣泛,如用作廚房、驢圈、羊圈、糞場、蔬菜窖等。有些人家還在窯洞外面的接口蓋起了平房,人住在外面的平房里,里面的窯洞因為冬暖夏涼,就成為了天然的儲藏室。
走著走著,一座敞亮的平房出現(xiàn)在我眼前,平房的外墻上貼滿了瓷磚,與房后的邊墻窯形成鮮明的對比。平房的主人叫魏永寬,65歲,是1950年住進邊墻窯的,5個兒女都出生在窯中,1994年他家蓋了這座新房,成了這里最漂亮的房子。一家人高高興興地搬進新房,邊墻窯就成了他家的廚房和閑窯。魏永寬告訴我說,“文革”時期這里還有在邊墻上挖窯的現(xiàn)象,“文革”后文物保護工作恢復了,文物工作者來到這里,對原有的邊墻窯的數(shù)目、大小等情況作了詳細的登記,并對大家講了保護長城的重要性,要求人們自覺遵守文物保護法,后來就再沒出現(xiàn)過挖窯的事。
第三天離開磚井鎮(zhèn)時,出于習慣我提出要給老薛一家拍張全家福,老薛趕忙張羅,喊回了地里干活的家人,我讓他們站在自家的邊墻窯前,給他們拍了一張合影,他的女兒在拍照前還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
大風的夜晚,在邊墻窯中睡去
后來,我在山西的老營城采風時,也見到了邊墻窯。老營城和磚井鎮(zhèn)一樣,都是一座長城經(jīng)過的古城,兩者只是在窯洞位置的選取上有著本質(zhì)區(qū)別:磚井人是把窯洞挖在長城上;老營的人則是把窯洞挖在古城的城墻上。不過,在窯洞的類型和結構上,兩者卻是一模一樣。
第二次來到磚井鎮(zhèn)的時候,我依然是住在老薛家。吃飯時,老薛的老伴仍舊在邊墻窯中給我做了一碗很香很油的面條,我發(fā)現(xiàn)那天的面里有許多肉,湯很油。老薛說我是客人,吃飯就該有油水,以前從不吃大油膩的我,把那碗油湯端起來喝了個精光。
晚上,我跟老薛兩口商量,讓我住到他家用來當廚房的邊墻窯中,起初他倆說什么都不同意,后來我借口說窯里下午做飯,炕是熱的,我怕涼,才爭得了住進窯里的機會,老薛擔心我一個人住害怕便陪在我身邊。
那天晚上的風特別大,半夜把門都吹開了,我也被驚醒了。外面黑乎乎的,風吹著門板吱吱響,似乎有什么東西在地上轉(zhuǎn)來轉(zhuǎn)去,看著身邊鼾聲大作的老薛,我考慮了半天才硬著頭皮下地把門關上,用門閂插住。心想邊墻窯里真就這么安全,難道老薛他們晚上睡覺從來不關門嗎?
那夜,老薛家的狗叫了一晚上。
- 環(huán)球人文地理的其它文章
- 遙遠的格桑花(組詩)
- 海椰子
- 接吻蟲
- 出姓
- 煤精印
- 挪威羅弗敦群島:24小時都是陽光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