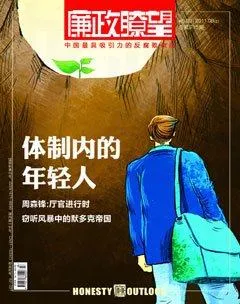我為什么要回來
2011-12-29 00:00:00衡潔
廉政瞭望 2011年8期

事業單位——金領——國企——
王裕的辦公桌很干凈。
在這個有上千人的西部大型煙草企業,王裕的辦公桌只占了小小一角。上面若干個文件夾被分門別類放得整整齊齊,電腦顯示屏調到了最佳亮度和角度,角落里還放了一株老婆給他買的仙人掌。
這個男生帶有很強的理科生思維的烙印,說話方式如同他的辦公桌一樣,喜歡按“1、2、3、4”排列,井井有條。
這里的環境他非常熟悉,可磨合得深了似乎又有些不一樣。對于體制內來說,他已是第二次進來了。1981年出生的他,先在一家事業單位工作,后來又跑到一家企業去當拿高薪的金領,現在又進了國企。
我們的聊天以王裕這樣的開頭展開:“我為什么要回來……(仰在椅子上長時間的思考)第一……”
抓鬮的決定
王裕的人生完全可以用根正苗紅來形容。父母都在體制內工作,且都是中共黨員。受父母影響,他在高中時就入了黨,當時剛滿18歲。讀的是重點大學的熱門專業,還沒畢業,父母就動用關系給他鋪好了進體制內的道路——去一家效益不錯的事業單位上班。
看著這幅徐徐展開的人生美好畫卷,王裕乖乖地去了。可3個月后,他做出了一個讓全家人大跌眼鏡的決定:他要辭職,去深圳華為公司工作。
“當時覺得,在那個單位一輩子都看到盡頭了,我想出去走一走。”王裕說。他的決定在家里引起了很大的爭論,“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我互相都無法說服對方。他們看不清未來究竟會怎樣,只是不想讓我離家去冒險”。
各方爭執不下,最后,全家人冒出一個“很娛樂”的決定:用抓鬮來看看結果。第一次,王裕抓到了“體制內”。“感覺真跟那個段子一樣:抓鬮不是讓你決定什么,而是在展開紙團的那一剎那,讓你看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王裕回憶說,“正是因為我不想去,所以硬是抓了第二次——去華為。”
“我父母一輩子都在體制內,不了解體制外的公司是個什么樣的狀況,所以一直不愿意我走。當時只有我舅舅和四姨支持我,他們說,我還是一張白紙,應該出去闖一闖。”2004年10月,王裕收拾了行囊,登上了南下的飛機,開始了歷時兩年多的尋夢之路。
我把領導給投訴了
王裕對那段體制外的經歷評價很高:“一是我認識了很多非常優秀的朋友,這是我一生的財富;二是華為軍事化的管理、大大小小數不勝數的培訓,教會了我很多技能和理念,這也是讓我終生受益的。”
2005年5月,王裕在北京出差后回家過五一節,在路上,他收到了領導的一條短信:王裕,通知你,去印度。“沒一個多余的字,卻讓我又一次興奮起來,自己終于可以到第一線工作了。”王裕說。五一節一過完,他就背著大包小包,去了印度的清奈。
到了清奈,王裕傻眼了。本以為有一個緩沖期的他,到宿舍放下行李就被拉去了工作地。“工作就像打仗一般緊張。第一次和客戶交流,他說的印度英語我有70%沒聽懂,剩下30%中,又有10%是我聽懂了但無法給他解答的技術問題。我基本當場崩潰。”王裕說。一同崩潰的還有帶他去的產品經理,交流結束后經理馬上把王裕投訴到了總部,質疑總部為什么要派這樣一個人來。“我聽說這件事后更加郁悶,覺得一點不給時間適應也太不合情理,一時情急,就發了封郵件到總部訴說情由,把我們經理也給投訴了。”王裕回憶起當時的場景,笑稱當年的自己太幼稚,“這要是放到現在,我估計就不用在這兒混了。”
但當時的華為寬容了王裕的沖動。冷靜下來的王裕,被激起了不服輸的勁頭,連著三個月,幾乎每天加班到晚上12點,終于克服了語言問題和產品知識問題,成為了獨當一面的員工。2006年4月,王裕簽下了人生的第一個大單——784萬美金。
“以前都是量的積累,現在是一個質的飛躍。”王裕說,“華為這個私企跟體制內的單位比,既單純也不單純。不單純是因為有人的地方就有斗爭,這一點華為也不可避免;單純是因為在你遇到困難的時候,公司里的朋友會告訴你竅門,伸出援助之手,而不像體制內的大多數單位,更多奉行的是各人自掃門前雪。”
2006年6月,已在印度掌握了各種資源、越來越如魚得水的王裕,接到了爸媽的電話:“兒子,回來吧。”在印度的一年間,王裕經歷了印度百年不遇的洪水,水淹到只剩一個頭,還遇到了當地的一個爆炸案,這些都讓只有一個寶貝兒子的父母不放心。他們甚至再次動用關系,給王裕聯系好了到一家大型煙草企業上班。
王裕猶豫了。“一方面,我才剛開始出成績,不想走;但另一方面,華為是個講業績的公司,我又怕無法一直保持好的勢頭,不能持續地拿單。”王裕坦誠講出了當時內心的掙扎,“華為的員工流動性很大,這讓我的內心很不穩定。我在華為的工作時間非常緊張,沒有時間充電,覺得去國企也許有閑暇時間去讀個研。慢慢地,我的選擇就有了傾向性。”
王裕權衡再三,決定回家:“當時還真沒沖著什么國企的穩定和福利回去,只是覺得工作崗位比較適合。在外漂慣了,到時不習慣再走就是。”
請你不要插嘴
2006年底,王裕進入了那家國企。剛去時最直觀的感受,就是收入上的銳減。“收入基本只有我在華為時的1/10。”王裕說,“因為體制內有相當一部分收入是按工齡算的,我是在體制內重新開始。”
正如王裕所料,國企里的工作相當輕松,這讓忙慣了的他無所適從。這種狀態持續了大半年,王裕去考了在職研究生,開始充電。
“我剛開始覺得清閑很舒服;時間長了就開始擔憂,懷疑這樣下去人是不是要廢了;再過一陣慢慢適應了;到最后,已經依賴這個體制,覺得離不了了。”王裕分析說,“一步一步,就像溫水煮青蛙。”
因為人天生的惰性,在工作強度上王裕很快被體制內的溫水同化,然而在其他方面,他還是感到了體制內外的巨大差別。
E1EWfxbgbesVnNUfIC65Eg== 在單位,王裕學會的第一件事,就是開會時如何給領導們按層級排位放座牌:“不能得罪這個,不能得罪那個,萬事安全第一。”
王裕還告訴記者,在國企非常講究流程和層級,而在華為這樣的公司則是追求結果和速度:“以前講效率,現在講嚴謹。在這里,一個合同審批需要十多個部門簽字,少一個,哪怕你再急也沒用;在華為,如果能迅速且成功地達到某一個目標,那么可以越權。在國企里如果不講流程,越級越權處理,會被視為犯了大忌。”
他給本刊記者講述了自己經歷的一件事。那天,他陪同部門領導去給一個上級領導匯報工作。匯報時,王裕感到有個地方可以再補充一下,就插了句話,結果部門領導的臉色當場就變了,嚇得他馬上閉嘴。出來后,部門領導直接對王裕說:“以后我匯報工作,請你不要插嘴。”
同時,體制內人際關系的微妙王裕也慢慢體會到了:“國企里的關系很復雜。同事中不少是關系戶,一來,本身單位就講究論資排輩,人才脫穎而出的機會就少;二來,若真的有誰脫穎而出了,也會被懷疑是‘背景硬’。”
單位的一次晉升機會更是給了王裕一個現實的打擊。當時,已在部門工作了3年的王裕,以為憑能力、憑經歷、憑學歷,都是非他莫屬。結果,領導卻提拔了另一個在單位已呆了5年的同事。“說真的,我一直就沒把他列為競爭對手,實力相差太多了。”王裕無奈地說,“從那以后,我更明白了體制內的一些規則,被席卷到其中的我們,是不得不遵守的。”
瓶頸在哪里
2011年初,王裕結婚了,愛人是一家省級單位的公務員舒心。在朋友眼中,他倆稱得上是門當戶對的組合。“在談戀愛和成家時,你會更加體會到有一個穩定單位的好處。”王裕說。
“現在我在華為的朋友,月薪都有4、5萬,這個我是遠遠比不上的。但私企總是說不清以后的風浪,但體制內的風險概率比較小。”王裕告訴本刊記者,“人有時也是要找平衡感的。我現在的單位人員穩定,周圍朋友流動少,不用加班,有更多的私人空間,薪水穩步增加,會發各種各樣的購物卡,也沒有被開除的壓力,這些都是比華為強的地方。若一直在華為,當到達一定平臺時,也許會碰到真正的瓶頸,那時也只能選擇離開。”
舒心很贊同王裕的觀點:“雖然我大學畢業就考進了公務員,沒有去體制外見識過,但當看到同學在體制外的工作那么辛苦,還是覺得體制內好。”舒心一個同事的老公在部隊轉業時沒有選擇體制內,而是選擇了下海經商,雖然現在也很成功,好車好房都有,但“幸福指數遠遠比不上和他同一批轉業、進了機關的人,他們現在也大都身居要職了”。尤其是在面臨小孩上學、就業時,體制內的人往往有一只看不見的手能將其安排到更好的地方。
“那個同事常跟我們說,后悔當初沒讓他留在體制內,尤其是對下一代來說,這樣的選擇更長遠。”舒心說。王裕也轉述了當年一名領導告誡他的話:在體制內,不要太在意前面的得失,到了后面,體制內的好處就顯現了。
2010年,王裕也成功晉升了,他對一些傳統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從抵制或反感某些規則,變為接受甚至維護這個體制:“人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綜合體。當我在體制內的最低層時,我批判它;但隨著我資歷的增長,我也晉升了,我就體會到了論資排輩的好處。怎么看待它,完全取決于你在哪邊得到的利益大。”
讓王裕高興的是,現在他們單位也實行了一些改革,在某些崗位的提拔晉升上,開始搞競聘上崗。這讓他感到,在體制內一樣能大有一番作為,“我現在的目標就是成為單位的中層”。
聊天快結束時,王裕向本刊記者透露了他的夢想:“我最初的夢想是開一家餐館。你覺得遠嗎?其實一點不遠。這個夢想至今未變,我在一點點向它接近。工作和理想是有區別的,自我價值的實現也有很多種方式。好好工作是,開餐館其實也是。總有一天,它們都會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