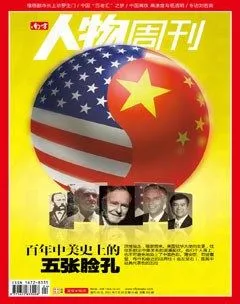土地問責的關鍵到底是什么?
如果不能破解土地財政,刮多少次問責風暴,都是無用的沙塵暴
土地問責風暴刮起,面對73名官員受到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直至撤職處分的結果,評論者大多集中于土地問責過于溫柔,只拍蒼蠅,不打老虎。這樣的評論有理,但尚嫌膚淺。
我國地方政府官員之所以熱衷土地違法,并非因為他們是天生的熱愛違法分子,而是因為地方政績、個人錢景與土地密切相關。土地問責意在抑制土地市場的尋租與透支現象,但并未涉及土地違法的根本,即土地收入與地方政績、與城市化過程、與政府錢袋牢牢捆綁在一起的制度基礎。
2010年,我國的土地收入達到前所未有的2.9萬億元人民幣,占據地方財政收入的半壁江山。與高速公路與高鐵同步,新城運動如火如荼,這場運動既可以被貼上中國城市化成果的閃亮標簽,也必然意味著更高的土地違法概率。
目前地方政府對兩種房地產建設情有獨鐘:一是城市綜合體,這種集中了住宅與商業的建筑模式為地方政府建造出一片新的商業天地,二是工業園區,一片片空曠的工業園區種植著地方政府引資、引企、發展新經濟與扶植企業上市的希望。
土地違法現象頻生,是經濟模式發展錯誤的結果。
只要地方政府繼續成為大投資家,成為經濟的主導者,擴張投資就是經濟理性人的自然選擇。為了擴大投資,地方政府會不擇手段、不顧風險向銀行貸款、將資產變現、出售土地、增加居民成本,以盡可能地獲得投資資金,土地只是其中的一項重要變現資產,但絕不是惟一的資產。
只要地方政府繼續成為大地主,出于地主的經濟理性人的精明,以高價出售土地、出售越來越多的土地獲得土地溢價,就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
地方政府之所以在土地問題上屢屢違規違法,原因就在于此,他們已經不僅僅是政府,不僅僅是守夜人,而是大投資家與大地主。在任何時候,資金與權力受到有限約束,就會不斷自我膨脹,最終的結果就是債務危機,就是貨幣與資產泡沫崩潰,就是全面的產能過剩。我們已經在日本看到了結局。
抨擊土地問責不力意義不大,如果73名官員因為土地被問責仍不足以震懾地方官員,那么就算730名官員被問責也沒有用;如果市縣級官員被問責仍然無濟于事,那么向省級官員問責同樣意義不大,相反普遍問責還會引發一場經濟與政局的動蕩。是的,國土部可以用衛星監控每一個村的土地,我們的土地審批制度全球最嚴,但那又有什么根本作用呢?以行政手段處理經濟問題,只會讓惡劣的經濟生態更加惡劣。
筆者曾不止一次聽到政府官員的真心話,他們在政績、城市化與嚴厲的土地政策之間左右為難,要前者就必然否定后者,要后者就一定會成為平庸的官員,升遷無望。
必須強調的是,任何一個不靠公平、正確的稅收制度而靠出賣資產換取生存權的政府,一定會面臨嚴厲的合法性追究。
在土地壟斷時代,土地是大宗資產,出現了土地財政下的普遍違法行為;在企業資產國有化時代,國資成為最大宗的資產,國資流失與國資套現并存;最糟糕的是,當政府把官位、爵位當成了最重要的資產,就會出現賣官鬻爵后縣官多如狗的瘋狂景象。
要解決土地違法,關鍵不是問責土地,而是把地方政府攫取土地的手拿開,讓他們通過公開的稅收生存,而稅收必須遵循法治原則,從根本上讓地方政府回到守夜人的身份上來。
在現狀下要解決土地違法難題,重要的是讓地方政府受到利益相關者的監管。目前采用的辦法,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問責,由土地擁有者對地方政府問責顯然成本更低、成效更高。
如果土地制度發生變革,資產變現后能讓原來擁有土地使用權的村民、居民獲得更多的利益,請相信,他們一定會用鷹眼看好自己的財產。政府只要有法律救濟手段就行,何必興師動眾,一次次進行悲觀的努力,在GDP與土地之間折沖樽俎,屢撞南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