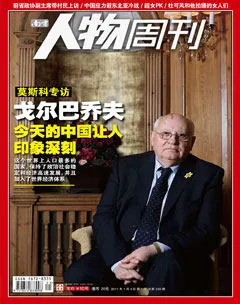杜贊奇 現代性之“惡”與民族主義的“毒”
2011-12-29 00:00:00李宗陶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1期

“在中國,共產黨一旦獲得政權就試圖運用新的文化和教育政策來實現人的翻身,但甘地卻是要在獲得權力之前實現個體的轉變,以此作為獲得政治權力的方法”
杜贊奇的笑容很給力。眉毛胡子都運動起來,擁向那雙精光四射的眼睛,向外界傳達睿智和友善。
“對歷史的探索就是一種徘徊在語言和歷史真實之間的活動”,這是杜贊奇浸淫史學40年的心得。
他與漢學的結緣可追溯到1973年。當時他在德里大學念書,中國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一班歷史系學生的濃厚興趣。“因為它展現了一條可能改變歷史的路徑,很大地啟發了我們,我們覺得這是應該研究學習的東西。”杜教授告訴記者。
赴美深造分為兩個階段。在芝加哥大學,杜贊奇遇到他最重要的導師之一孔飛力先生。“我在研究中國革命的時候,對中國的農村很感興趣。我最初的興趣也受到孔飛力教授的影響,他不是那么激進的人。他認為相對于革命階層而言,本地政治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因此《文化、權力與國家》源自我最初的興趣,并受到美國漢學界非革命一代學者的影響。”
這本書是杜贊奇的博士論文,獲得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1989年度杰出東亞歷史著作獎;一年后,又獲亞洲研究學會約瑟夫?R?列文森20世紀中國最佳圖書獎——同年,孔飛力的代表作《叫魂》獲得了“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
1977年,費正清教授自哈佛榮退,孔飛力接替費正清出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杜贊奇與導師一同從芝加哥遷往波士頓。
杜贊奇向記者談起對兩座一流學府的比較:“芝大是一個具有知識分子氣息(Intellectual)的地方,而哈佛是一個學術性(Scholarly)的地方——我甚至覺得哈佛都不是學術性的,而是一個權力之地。更確切地說,兩所大學的區別在于前者是純粹的知識權力,而后者是混雜的知識權力。哈佛總喜歡把總統、國王、大使、前大使這些人物都混雜在校園里,希望兼顧公共職能和公眾形象。而對芝大來說,最重要的是你寫過一些什么,有多深入。
尋找發展和生活之間的平衡
人物周刊:您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的最后部分用很大篇幅談論了甘地對現代性的批判。譬如說:現代化的機器設備只能刺激人更多的物質欲望,卻永不能滿足他們;工業化帶來破壞、剝削和疾病,造成城市和鄉村之間極其嚴重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而在30年前,中國一位同樣智慧的領袖憑借一句“發展就是硬道理”將中國領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新紀元。人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兩種看上去矛盾的思想呢?
杜贊奇:我們需要尋找發展和生活之間的平衡。目前中國的問題似乎是很難控制,如同普羅米修斯被解開了鎖鏈,一切都被發展所驅動,釋放出來追求利潤的力量很難被收回,這是最大的挑戰。
需要有幾個重要人物,如甘地,成為對現代性批評的象征。以芝加哥為例,芝加哥有一個人文的、反經濟發展的傳統,一直以出產眾多知識分子包括許多諾貝爾獎得主而聞名,但突然間它被視為經濟之都,這對芝加哥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沖擊,于是在米爾頓?弗里德曼研究院(Milton Friedman Institute)就此爆發了一場大爭論,后來弗里德曼就成了芝加哥的象征。我想說的是,芝加哥有很強大的知識傳統,我們必須保有這些傳統來對現代性進行對抗和平衡。
人物周刊:在您看來,發展到今天的西方現代性的特征是什么?
杜贊奇:我認為我們生活在“后西方現代性”的狀況中,這個世界正被“發展的觀念”所主導,使用著各種現代技術。我們以前認為宗教是和現代性分開的,所以沒有意識到文化角色的問題,但事實上,西方現代性很大程度上是伴隨著基督教而來的。譬如對個人價值的極度推崇——在新教看來,每個人都像上帝一樣,可以直接和上帝溝通,由此推出個人權利的主張等等。因此我覺得基督教是西方現代性的重要特性,而我們要重新思考這些關于超驗的觀念,包括中國的天人合一。
現代性帶來道德貶值
人物周刊:印度的泰戈爾、日本的岡倉天心、中國的章太炎都在“文明重構”這一主題上提出過自己的主張。您能大致談談他們在思想和作為上的異同嗎?
杜贊奇:我理解他們是想嘗試超越國家,他們是反帝先鋒,他們將西方看作推動“文明”概念的帝國主義,而這個文明則是他們試圖合法化帝國主義的說辭,影響了我們的價值觀。問題是他們除了民族主義以外沒有其他達成這個目的的手段,因為民族主義是惟一可用的方法,而一旦如此,你就在自我和他者之間劃了一條界限。泰戈爾和甘地嘗試抵制這種民族主義,但沒有用。章太炎是一個復雜的人,他同時是個排滿的民族主義者和一個佛教徒。他不是一個好例子。
我對他們也有批評。他們和大眾文化沒什么關系,他們對于亞洲的統一性只是局限于高雅文化,譬如士大夫文化,他們不看普通人的生活。那個時候有很多印度人來中國,有一些印度士兵來中國,但這些人是不為這些知識分子所看到的。這些普通人的普通關系是更復雜的。溝通普通人之間的關系在今天的亞洲仍然是很重要的;而簡單地描述偉大的歷史文明是不夠的。
人物周刊:現代人應該如何面對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和文明、道德的關系?
杜贊奇:我不想討論短期內的道德上升和墮落,而是想長期來看。作為社會良心的道德是一碼事,作為實際操作的道德是另一碼事。帝國時期的中國滿口仁義道德,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上呢?
在現代性的長期發展中有一個道德話語的貶值,因為現代性逐漸詆毀道德的價值,將人看作市場社會中的工具。市場社會把人的價值簡化為市場價值,而市場書寫了人的行為,所以現代社會中道德是沒有功用的,甚至父母都不教孩子講道講德了。因此我們要提可持續性這個問題,因為它提出了對倫理的要求。這是在我看來惟一的希望。所以今天服務員來房間打掃的時候,我跟她說:不要換毛巾!
毛澤東和甘地都是理想主義者
人物周刊:您曾說過,如果換一種環境,梁漱溟、晏陽初和陶行知都有可能成為甘地的角色,但他們最終沒能成為。所以,想請教是怎樣的環境限制了他們?這種限制的根源是什么?
杜贊奇:梁漱溟、晏陽初和陶行知沒有成為甘地式的人物有多種原因。一方面,“五四”運動使得現代性成為一個超越一切的需要;另一方面,政治和權力的產生使得他們必須首先獲得權力才能實現理想;此外日本的侵華戰爭也對此有影響。
限制的根源我認為是在這些精英的意識中,為一項事業而做的政治動員是重要的,而非緩慢的對個人的教化,對一個人內在的改變。而甘地是希望每個人都從內在發生改變。我覺得后來中國對個人內在的改變是更成功的,但那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后。共產黨一旦獲得政權就試圖運用新的文化和教育政策來實現人的翻身,但甘地卻是要在獲得權力之前實現個體的轉變,以此作為獲得政治權力的方法——這個想法在當時的中國是不被看重的。甘地認為在個人內在發生改變之前獲得權力會導致腐敗,當然他是浪漫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
人物周刊:您愿意比較一下毛澤東和甘地的異同么?
杜贊奇:毛和甘地都是很深刻的理想主義者,都相信超驗的力量,相信可以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東西。毛的超驗是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甘地的超驗是他自己來源于一些印度教傳統的、對神的理解。當然他們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對甘地來說,你必須自己先成為這個理想本身,讓超驗在你自身中發生,然后才能承擔起真正的權力,而毛則是先奪取政權,然后再發動文化大革命。相同的是,他們不止是浪漫主義者,而且都是行動者,要真的實現他們的理想。
從民族主義到國家主義
人物周刊:您如何評價奈保爾在“印度三部曲”中的立場?
杜贊奇:我看過第一本《幽黯國度》。有人說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作家,因為他能批評第三世界。如果一個歐洲人批評印度,誰都會指責他,但奈保爾是第三世界的作家,還能自我批評,西方很高興。
我不完全同意這個觀點。奈保爾對第三世界具有一種很真誠的批判態度,但他沒有責任意識。魯迅會說這是國民性,也是他自己的狀況;但奈保爾不說這樣的話,他對印度人沒有認同感。如果他能選擇,他會選擇做歐洲人做英國人,因為他們代表了最高階段的文明。有不少這樣的印度人,他們很勇敢。
有一個可能比奈保爾更偉大的印度作家Nirad C. Chaudhuri,他也用英文寫作,11年前去世。他在孟加拉地區的一個村莊里生活了五十年,做政府秘書。他閱讀了所有的歐洲和梵語經典,五十多歲第一次去英國就對英國了如指掌,他一生都在膜拜英國。他的寫作中充滿了對印度和印度人的強烈批評,但有趣的是,他可以定居在牛津。但他最終選擇回到印度,居住在德里舊城。和魯迅不同的是,他在寫作中對印度沒有同情;但他又和奈保爾不同,因為他拒絕居住在倫敦——比較這3個人很有意思。
我覺得奈保爾的批評很重要,但是如果他對印度多一些感情,就像魯迅對中國的感情那樣,那么他的批評就會更有效果。這也是為什么魯迅仍被中國人所熱愛的原因。
人物周刊:抗日戰爭時期一些中國讀書人寧愿餓死也不吃日本大米;印度獨立運動時期要求燒毀每一寸來自國外的布匹……今天的民族主義似乎更復雜些。
杜贊奇:過去20年間,民族主義的狀況已經發生了變化。一些民族國家和政府已經不那么喜歡過多的民族主義了,因為他們想要全球化。有時候他們想要控制民族主義,這當然很困難。我覺得一方面,民族主義的強盛是之前過多民族主義教育的結果;另一方面,它是對于過度全球化的一種反應,類似保險絲。
民族主義的功能變了:早期是為了民族獨立,現在越來越成為政治經濟發展中無用的東西,同時與對全球化的恐懼心理有關。它漸漸成為了一種應激性反應,而失去了建設性功能。
人物周刊:民族主義真的是增強民族凝聚力的一劑良藥嗎?
杜贊奇:我從沒覺得它是一劑良藥。民族主義對于反帝和建國是重要的,但是藥三分毒,其力量之大,可以允許人為所欲為——就像“文革”那樣,把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烏托邦結合起來,賦予人去摧毀一切的權力。
人物周刊:為什么今天民族主義總是跟“狹隘的”連在一起?
杜贊奇:我對民族主義的理解是: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競爭很有關系。當從農業社會演變成工業社會的時候,你不僅需要不同地區的人融合在一起,而且要有競爭力。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國家是讓資本主義社會變得更有競爭力的方式,但是社會主義國家要參與競賽,就像大躍進中那樣,就需要人們犧牲自己來讓國家變得富有競爭力。它的狹隘性就在這里,總是關于自己和他者的。
人物周刊:大約四五年前,學術圈已經注意到國家主義的苗頭。您能談談對從民族主義到國家主義這一意識形態演變的看法嗎?
杜贊奇:民族主義可以是一個進步性的力量,因為它具有各種對民族的視點,譬如本土性和多元文化等。國家主義可能受到限制,但東亞地區的國家主義是政府具有強權。國家主義可以看作政府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則是民間的,后者沒有一個政府組織起來的統一看法。在日本,民族主義塑造國家主義;而在中國,民族主義里有執政黨的參與。
(感謝漢雅軒畫廊主辦的“從西天到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以及陳韻對本次采訪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