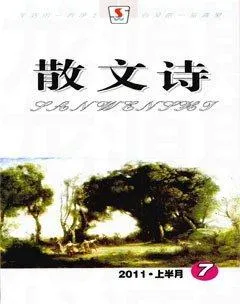散文詩與“詩片斷”
我對散文詩沒有專門的研究,但有這方面的一些實踐。大概1991年我寫出《帕斯捷爾納克》后,感到詩中那種內在的強度、亮度,那種精神噴發性腸枯味盡,于是轉向另一種形式的寫作,當時寫下了《反向》,一組詩歌片斷,很快受到了關注。上海詩人陳東東對我進行了書面采訪,他是以“散文詩”這樣一個概念。但我在回答中并不贊同這種命名,我稱它為“詩片斷”,后來一直堅持以“詩片斷”命名,迄今為止寫了10多個“詩片斷”系列。剛才聽大家談了散文詩這個概念以及它的命名的問題、名分的問題,我想這也糾纏了很多這種形式的寫作者,就像人們所說的一輛什么樣的自行車來打量它,和以前看到的自行車不一樣。我的“詩片斷”是想既打破人們對詩歌傳統的認識,又打破人們對散文詩一種既有的看法、模式,這應該有一些藝術的勇氣,和形式上的創造性,從我個人寫作經驗來講,是擺脫完整的形式和構思,從過緊的束縛中伸開自己,而在其它的地方生長出來,以片斷的形式呈現出來。一些朋友說我的某些“詩片斷”特別好,完全可以發展成一首完整的詩,但我不想發展并拒絕把它發展成一首完整的詩。因為我的這種“詩片斷”寫作不是一種所謂的加法寫作,而是一種減法寫作,我相信這種不完整中自有它的完整,一種殘缺的完整,留下更多的未完整性,留下更大的空間,讓讀者自己去完整。我個人認為這種“詩片斷”寫作自有它自身存在的理由。剛才有人談了波德萊爾、魯迅,我個人更認同兩位法國詩人瓦雷里、勒內·夏爾,勒內·夏爾與瓦雷里完全不一樣,他是一位片斷大師,他后期的詩歌創作完全是詩歌片斷形式。我們從來不會懷疑這樣一位大師級人物的這種形式的詩自有它自身存在的法理、自身存在的依據,如果用散文詩傳統的概念就無法認同這種自身存在的法理、自身存在的依據。像我的“不是你老了,而是你的鏡子變暗了”、“不是你老了,而是你獨自用餐的時間變長了”,這樣的片斷再加任何東西都是多余的,甚至會毀掉一個片斷。這也是它自身存在的法理、自身存在的依據。
另外,我還有一個想法是擺脫“美文”化,如今散文詩創作領域“美文”化、“詩意”化傾向比較嚴重,可說是鋪天蓋地,打開之后,就多得不想再讀了。剛才有人談到“詩性”這個概念,我很認同。在西方語言中,詩性與詩意是同一個詞,但在不同的語境中我想它的含義是有所區別的,像“詩意地棲居”和“詩性地棲居”給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我期待寫出的“詩片斷”更注重詩性,這是它自身存在的根本依據。這種詩性就是詩與思的兩者結合,不能太理性化、概念化。
我還要談談格言的問題。在中外的藝術中,有一種格言寫作,它與散文詩創作容易混同,我希望我寫出的“詩片斷”是反格言的,去格言化的。像我翻譯的策蘭的一句詩:“那是春天,樹木飛向它們的鳥”,這不是什么格言。但是它是詩,一讀就能讓人記住。我欣賞、期待的“詩片斷”寫作最終指向是一種存在之詩,像策蘭、勒內·夏爾的詩,是一種存在之詩。記得當年馮至先生寫了十四行詩后,朱自清先生非常高興,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談了詩與哲理,認為馮至詩歌極富哲理,但哲理性并不是馮至寫十四行詩的藝術目標,他的藝術目標就是存在之詩。此外,我還覺得這種詩片斷是一種經驗的產物。1991年我剛步入人生的中年,這也是中年寫作伴隨的一個現象,或者說是一種經驗的呈現。隨著人生閱歷、藝術閱歷的增長,詩片斷是一種能滿足我把自己的經驗投入其中的形式。我寫了一個“詩片斷”叫《冬天的詩》,當時我住在北京郊區一個小房子里,在詩中我寫了城市與鄉村、過去與現在,因為人到中年了,就出現了多個自己,過去的自己,現在的自己,相互對話,相互辯論,還有個人與現在、過去與現在等等這樣一些經驗的沉淀,把它整合成一個藝術的整體,給讀者創造一個可以自由出入的空間,能各自自由地走進去各取所需。那么,這就是一種多線條的、復調的、音樂對話形式等等,總之,它可以納入更多的經驗。《冬天的詩》被翻譯成德文,一位漢學家專門寫了一篇評論文章,談了“詩片斷”的結構問題。他特別欣賞這種多線條的結構。
寫作多年,我覺得無論是散文詩創作,還是我所說的“詩片斷”寫作,都有著廣闊的、深遠的發展前景,我們不必為它憂慮,而且不必在意它外在的形式,它就是詩。“詩片斷”受到了詩人的高度關注、讀者的喜愛,我所尊敬的耿林莽先生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寫過兩篇評論文章,分別發在《散文詩》刊、《青島日報》上。在美國我朗誦完《冬天的詩》,一位老藝術家十分興奮,我的好多“詩片斷”他都能背下來。一次我跟美國桂冠詩人羅伯特·哈斯一起在黃昏中開會,他很認真,專門找我談,他談到我其它的詩,談得非常具體,另外他談了我的兩個“詩片斷”,他的評價之高是我所沒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