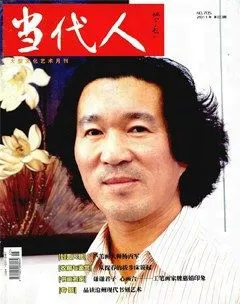謙謙君子 心畫合一
魏惠娟,石家莊市畫院畫家。現(xiàn)為中國美術(shù)家協(xié)會會員、國家一級美術(shù)師、河北省美術(shù)家協(xié)會理事、河北大學藝術(shù)學院美術(shù)系客座教授、河北省政協(xié)委員。
2001年、2003年先后入北京畫院楊瑞芬工作室、王明明工作室學習深造。作品多次參加國內(nèi)外畫展并獲獎。出版有《21世紀優(yōu)秀藝術(shù)家畫集》《魏惠娟中國畫作品集》《魏惠娟田園畫作品選》等。
結(jié)識惠娟先生,我之幸。
初次見面,她已是名滿河北畫壇的工筆女畫家。但她優(yōu)雅溫厚,謙謙然一派君子風范。于是,大畫家與我這個小編輯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
原來,惠娟先生出身寒苦農(nóng)家,卻稟賦天然。很小,她便以土地為稿紙,以樹枝代畫筆,臨寫田園。在鄉(xiāng)勞動的幾年,悉心體味生活甘苦,工余苦練寫生。這種來自生活的情感凝練、藝術(shù)養(yǎng)成,為她日后考入美術(shù)專業(yè)奠定了扎實的基礎(chǔ),也為她藝術(shù)方向的選擇打下堅實根基。
然而,美術(shù)專業(yè)畢業(yè)的惠娟,卻被分配到其他行當。此時,初為人母的她,備嘗生活艱辛——婆母患白血病,公爹又有慢性哮喘病,巨額的醫(yī)療費用,讓她們夫婦拮據(jù)的生活雪上加霜。她只得加班加點給人設(shè)計商標、設(shè)計服裝、做工藝鏡匾換取微薄的收入,以一副柔弱的肩膀擔起了照顧老人、撫育兒子的雙重擔子。
命途的磨難,其實是上蒼對一個藝術(shù)家的特殊眷顧。孝順仁厚的惠娟先生,在對親人的悉心照料中,更深刻地體悟了一個人所應(yīng)有的責任和擔當,勇氣和襟懷,也更堅定了放下行政飯碗,執(zhí)著追求藝術(shù)的道路。夜闌人靜,老人和孩子都已酣眠,惠娟先生則開始她每天的功課,心追兩宋,廣獵明清,取法傳統(tǒng),尋求屬于自己的工筆畫路徑。
天才加勤奮,是惠娟先生成功之兩翼。1993年,剛剛?cè)畾q出頭的年紀,魏惠娟為自己捧回了河北省國畫書法大賽金獎,以一幅工筆田園作品《月夜》而在畫壇贏得一席之地。此后,以工筆寫田園,成為她獨有的藝術(shù)名片。
在惠娟先生看來,田園有大美而不言,她的使命即為田園代言。所以她筆下的田園題材沒有疆界,沒有窠臼,一派天真自然。一只南瓜,一棵茄子,一畦開花的大蔥,一簇怒放的雞冠子花,一架經(jīng)霜的絲瓜,甚至一棵寂寂而開的白菜花,在她的筆下,都有著獨特的生命意義,因而也就擁有了獨具的審美情致。看那一幅幅小品,野趣天成,比如《秋情》,靜日無人,一對小鳥在麻山藥棵子下溫情私語,卻不知那些模樣憨厚樸拙的山藥豆子偷聽得正上癮,比如《田園小詩之二》,暖陽生煙,瓜田安靜到極致,老南瓜都幸福得睡著了,這時候,一只瓢蟲卻在尖細的草葉上爬行尋覓,而不遠處木籬笆上一只雀兒早悄悄盯上了“目標”,一靜一動,妙趣橫生。看那一幅幅大畫,言有盡而意無窮,畫面的主要角色可能只是一堆成熟的南瓜,一簇挨挨擠擠即將收獲的毛豆,幾只鬼頭鬼腦的小刺猬,比如《秋天的故事》《晨霧》《深秋》,但我們分明讀到的是農(nóng)家的日子,農(nóng)村的生活,是我們祖祖輩輩沉甸甸的希望,是我們的家園掛著眼淚的笑窩。“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正好可以概括惠娟先生和她魂牽夢繞的田園詩話。
讀惠娟先生的畫作,再浮躁的靈魂也會獲得一份安寧。因為畫家的筆墨色彩是安寧的,古意幽幽,閑雅淡定。那是畫家心靈的色彩,心靈的寫真,當我們進入到她獨特的繪畫語境,其實已開始與她的心靈對話。那動靜之中,那虛實之間,那流淌的氣韻,那明麗或略顯憂傷的色彩,其實是畫家一種積淀厚重百引一發(fā)的態(tài)度,一種閱盡世情之后的純真,一種舉重若輕的擔當姿態(tài)。“是生活的性靈啟迪了我的性靈”,惠娟先生總這樣對我說。事實上,只有當生活的底色映射于藝術(shù)家豐富敏銳多情的內(nèi)心世界時,生活的性靈才會躍然于畫稿!
關(guān)于惠娟先生的藝術(shù)成就,畫界早有公論,前輩評論家也多有褒獎。我作為行外人,卻每每被她的藝術(shù)情操、個人品格所感染、感動。我以為“人品即畫品”,是適宜惠娟先生的。看到她在一次又一次公益活動中的身影,看到她在工作崗位一絲不茍的“盯班”,看到她作為河北省政協(xié)委員高質(zhì)量的提案,看到她對親人、朋友潤物無聲的關(guān)懷,不由感慨系之——“畫到‘通’時格自高”。
畫田園,畫心靈,畫情懷。我祝福惠娟先生。
(責編: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