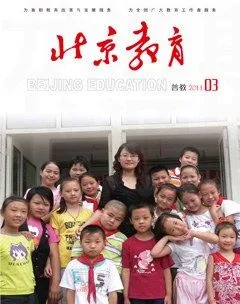有趣味的關聯
學術研究必須注重邏輯的力量和完整的過程,這是學術產生力量的基本要素。但尋找什么樣的內容作為研究的對象是學術產生影響力的關鍵所在。當前中學學術研究缺乏學術基本要素是一個問題,但更為嚴重的是學術研究內容空洞、單一和虛假,簡單地說,中學學術研究缺乏這個研究階段所應具有的靈活、可愛和溫暖。我認為造成如此現狀和以下兩個問題相關。
學術研究目標的異化。和工作相關的學術研究不能只是讓研究者本人高興,更不能在功利驅使下僅僅完成預設的目標。但捫心自問,今天中學的學術研究如果能出自于研究者本人的濃厚興趣,即便是自娛自樂已經是很奢侈、珍貴的行為了,更多的是為晉級或者證明自己地位提供一個合理依據,這就是研究目標的異化。我認為,中學學術研究目標中有一點至關重要,那就是通過研究幫助孩子們獲得智慧、溫暖心靈并感受知識帶來的快樂。
整體文化觀的缺失。我們并不缺乏很多具體領域的深入研究,甚至可以說探討各種解題方法的文章已經“蔚為壯觀”了,思考各種意義和必要性的文字更是多得數不勝數。但我們卻嚴重缺乏生動的、新鮮的內容,導致雖有深入研究但缺乏更精深的理解,眼界狹窄,只能在有限的領域打轉,這說明我們似乎更缺乏的是整體文化觀的建立。長期以來,我們設置的學科藩籬已經讓很多學生和老師筑起思維的高墻,與其說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不如說是不肯走出自己劃定的勢力范圍。但這樣的結果是,我們的知識越來越抽象,學科界限越來越擴大,知識似乎成為了某種權力,絕不容許他人染指。這不是知識和文化的本來面目,其實高考方案中設立文科綜合和理科綜合的根本用意也在于此,那就是打開不同學科的道路,讓思維自由通行。
中學學術研究一定要注重趣味性,建立讓思想四通八達的網絡,最終才能讓孩子們感受知識的溫暖和快樂,因此,中學學術研究的一個重點就是要思考怎樣構建有趣味的關聯。
這是一個有點陌生的概念和表達方式,下面以筆者讀過的兩篇和長城有關的文字后展開的聯想為例,看看建構起一些有趣的關聯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意義。
一篇是美國人Peter Hessler寫的《Walking the wall》,另一篇是中國日報記者周黎明的《太空看長城采訪記》。 前一篇文章至少讓讀者了解到以下事實:
1.研究長城的學者或者愛好者中,有很多外國人,具有影響力和研究達到精深水準的基本上是外國人(這對于把長城視為民族象征的國人來講,未免有些尷尬);
2.世界上沒有一所大學有專門的長城研究學者,即便作為長城的東道國,學者們的興趣似乎也不在此。外國人是這樣認識的:在中國,歷史學家一般專注于政治體系研究,而考古學家則致力于挖掘古墓。長城在傳統學術領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甚至對于某個獨立的專題,如明長城,嚴謹的學術研究成果也鳳毛麟角。
3.文章的主角,美國人David Spindler(石彬倫)研究長城采用了實地考察和文獻研究的方法,可謂遍走長城和找遍世界各地和中國長城有關的書籍。
4.長城有太多我們未知的領域,例如長城的長度,1985年,中國的衛星調查認為,北京地區有390英里的長城,但David Spindler發現的要比這一數字長得多。
《太空看長城采訪記》則充滿了太多的玄機,記者周黎明從一個流傳很久的——長城是唯一能夠從太空用肉眼看到的建筑——這個說法開始產生懷疑,進而展開一系列調查研究,得到了更加讓人撲朔迷離的答案。
筆者從這兩篇文章開始展開聯想,在幾個領域來回穿插,建立了這樣一些有趣的關聯。
歷史學意義上的關聯
長城如何成為能從太空用肉眼看到的唯一建筑?這個說法是如何形成的?根據“國際長城之友”的創辦人威廉·林賽的研究,這個說法起源于西方,最早的源頭是英國歷史學家兼旅行家斯圖克利1720年漫游歐洲,在記述羅馬哈德良長城時說:這長城如此宏大,只有中國的長城超越了它,而中國的長城如此之巨,可能可以從月球上看到。
這就是美麗說法的起源,然后經過不斷的揣測與口傳的描述,這個說法開始頑固地在西方生長。1793年,英國軍官帕里什上尉隨英國使團到承德覲見乾隆皇帝,途徑古北口長城,后根據印象畫了一幅水彩畫,又被加工成版畫開始流傳,畫中的長城非常宏偉壯觀。
1907年至1908年,英國人威廉·蓋爾花費兩年的時間徒步長城,拍攝了大量的照片,并撰寫了史上第一部調查、記錄、研究長城的專著。
1923年2月,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的一篇文章如此寫到:依天文學家所言,在月球上肉眼可見的唯一一件人類作品是中國的長城。
1929年,英國人海斯寫了一本小冊子《中國的長城》,其中有這樣的句子:長城如此巨大,大約能從火星上看到(進一步夸張)。
這些真實的記錄和道聽途說、藝術夸張雜糅在一起,逐漸演變成為西方人所謂的市井神話:長城是能從太空用肉眼看到的唯一人造建筑。
1972年,美國阿波羅17號登月總指揮尤金·塞爾南表示,他在太空旅行中看到了長城,為這個讓中國人充滿自豪感的西方市井神話作了最有力的佐證。
這是這個說法的歷史變化。其實根據長城這個話題,可以順帶出很多有意思的歷史細節。比如:修長城的季節一般是在春天,此時天氣晴和,而蒙古襲擊者還不活躍。因為蒙古人南下全靠膘肥體壯的馬,寒冬過后,馬尚在恢復之中。夏天太熱,蒙古人受不了酷暑,蒙古人的弓弦是獸皮做的,濕氣讓弓弦無力,所以襲擊大多發生在秋季。再如,從秦始皇開始歷朝歷代都面對同樣的難題: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擾。從修長城就可看出不同朝代的外交政策,唐朝基本上沒有修城墻,說明唐朝善于應付邊境沖突和有著自信靈活的外交。
科學意義上的關聯
那到底能否從太空上看到長城?
2003年10月“神5”上天,楊利偉太空歸來說他沒有看到長城,后來中國科技館館長王渝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只有長寬都達到500米的物體才有可能從太空被看到。這對一直以來我們引以為自豪的那個西方市井神話產生了一定的沖擊,是科學勝利了?還是感情輸了?
2005年,中國日報的周黎明到美國休斯頓探親,正好趕上美國宇航局的華裔宇航員焦立中在太空站執行任務,于是他們建立聯系,啟動了太空看長城計劃。
但問題隨著觀察的進展而變得越發復雜起來,焦立中沒有給出看到或沒看到的回答,而是給出了一個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回答:能看到,但無法辨認。為什么會是這樣一個答案?因為在晴天,地球上的高速公路等很多建筑物都能被看到,埃及的金字塔也能被看到。但長城不太規則,而又處在山野之中,所以焦立中說他似乎是看到了,但不能確定,于是傳回照片。周黎明把照片送到中科院遙感應用研究所魏成階教授那里求證。求證的結果令人大吃一驚,原來焦立中認為的可能是長城的部分,連山脊都不是,恰恰是山谷和河床。科學上的地圖分析遠比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認識要復雜得多,況且這是相機“看”的結果,還不是通過肉眼得出的結論。
但問題是美國的尤金·塞爾南說他看到了長城,該如何解釋?于是周黎明和塞爾南取得聯系,并求證了當時他的太空飛行距離是160公里左右,經科學的推斷證明從這個距離幾乎不能看見長城。但塞爾南卻非常確信:就是長城,一眼就看到了!周黎明于是又和專家進行分析論證,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塞爾南看到的很可能是黃河,不是長城。但他應該沒有故意撒謊,很可能在美麗神話的迷惑下,以為長城能一眼望到。
在進行完科學的關聯之后,筆者把思維的觸角伸向航天,即便今日航天科技水平日新月異,但對于廣闊的世界,人類依然還顯得那么幼稚和無助,也許我們看到了太多的成功,而忘記了我們也曾經有過那么多的傷痛記憶,比如美國的挑戰者號爆炸。于是,筆者看了很多的關于挑戰者號失事的材料,從占有的材料中,又發現下面兩個有趣的關聯。
政治意義上的關聯
當面對災難以及公共危機時,國家的處理對策具有深遠的影響。當年美蘇爭霸的結果是蘇聯隕落,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其實這一結果從航天斗法即可見一斑。爭霸過程中,美國的很多技術都得到了很好的應用與發展,而蘇聯的技術就僅僅停留在了軍事領域,這和公開、透明的政策密切相關。例如,蘇聯當年在航天探索上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蘇聯人的思路是報喜不報憂,這樣的結果是科學失去人情味變成怪物,而美國把每一次的失敗都變成了持續發展的動力。在挑戰者號失事后,里根總統很快就發表了一篇電視講話,里面有這樣一段話:“我一直對我們的太空計劃充滿信心與尊敬,今日發生的事情一點都不會降低這種信任與尊重。我們不隱藏什么,我們不掩蓋秘密,我們一切都在大家和公眾面前,這是自由的方式,我們一刻都不會改變這點。我們將繼續我們的使命,將會有更多的航天建設、更多的宇航員,是的!還將有更多的志愿者、百姓,更多的教師。這一刻,沒有任何事情結束,我們的希望和旅行繼續!”
連一次失敗都成了自由價值觀的勝利,你不能不佩服美國人的公共危機處理能力。有了這樣鮮活的材料,再來回望歷史,分析冷戰就有了超越課本的歷史注腳,而且還帶著人的溫度。
英語和文學意義上的關聯
在讀了大量的英文原版資料后,我突然發現,無論是應對公共危機還是安撫情感,前提是必須有發自內心的藝術的表達方式,文學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比我們想像的要大得多。
里根的兩篇演講用獨特的表達方式所產生的藝術美感和情感沖擊力,今天讀來,依然保持著那種傷感的慣性。現節選兩段:
“挑戰者號的成員們用他們的生存方式榮耀了我們,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今天早上我們最后看到他們向我們揮手道別,然后擺脫大地執拗的束縛去觸摸上帝的面容。”
“我們今天齊聚于此,沉痛哀悼我們失去的7位勇敢的美國公民,共同分擔我們內心深處都能感受的悲傷,也許在相互的分擔中,才能發現抑制傷痛的力量,才能尋找到希望的種子。”
無獨有偶,在挑戰者號失事后,當時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也發來了一封不一樣的唁電:“我們至今懷念著哥倫布,他是探索人類未知領域的先驅;我也懷念挑戰者號的勇士們,他們同樣也在探索未知世界,我的自豪感和悲痛感同在,不過我想辦法用自豪感壓抑我的悲痛感。”
繼續搜索,又有一篇美文出現,那就是當年阿波羅登月時,美國做了最壞的打算,即登月失敗,宇航員犧牲,為此當時的尼克松總統準備了一篇失敗演講:命運注定這些登陸月球進行和平探險的人將在月球上安息。兩位勇敢的人已經知道自己無法生還。但他們知道其犧牲將為人類帶來希望。他們為人類探求和認識真理這一最高貴的理想而捐軀。他們將被親友、國家、世人哀悼;他們更會被敢于將子民送往未知之地探險的地球母親所哀悼。他們的探險,鼓舞世人團結一心;他們的犧牲,讓人類四海一家皆兄弟的情誼緊密相連。在古代,人類會抬頭仰望星空并在星座中看到英雄;在現代,人類也會看到自己的英雄,但我們的英雄是新鮮的血肉之軀。未來將有更多人追隨其腳步,但他們會找到回家的路。人類探索宇宙的雄心壯志不會因此而被放棄。這些犧牲者是第一批,將在人們心中永垂不朽。每一個在夜晚仰望月亮的人都會知道在那個世界有某個角落始終吸引著人類。
這是多么難得的英語教學和文學教育的材料,不是抽象的單一素材,這里面有科學、情感、政治與藝術。
通過以上歷史、科學、政治與文學四個方面的關聯,我們可以看出,僅僅是多一些好奇心,利用手邊不需費太多力氣的材料,我們就能編織出一張縱橫交錯的知識與文化的網絡,情感就會在這個網絡里通行,學術問題將變得不再枯燥和生澀,而是充滿生機與趣味。
最后,我們必須要重申一下,無論是任何工作,可能學術研究尤其如此,都需要一種難能可貴的品格——熱愛與勇氣。再回到第一篇文章中,文章的主角 David Spindler把人生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一項得不到官方和研究機構認可的事業中去,他能把全部生活——穩定的收入、愛情、人身安全——都拿去冒險。但他無怨無悔,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快樂。有人說,有時這種固執地追尋一個非同尋常的建構行為看來是唐吉柯德式的,但實際上支撐這一切的是完全的理性。這同時讓筆者想到了蘋果公司喬布斯的一段話:“我確信唯一能讓我堅持下去的就是我熱愛我所做的事情。你必須發現你所熱愛的東西。你的工作將占據你生活的大部分時間,但唯一能讓你寬慰的是你所做的是件偉大的事情,而唯一能做偉大事情的方法就是無限的熱愛。”學術研究不一定都要搭上生活的全部,但一定離不開興趣以及進而產生的熱愛。■
□編輯 王雪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