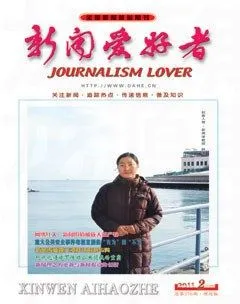現代化語境下傳媒公共領域的重塑
西方語境下的公共領域與現代化
公共空間的結構與性質對社會變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同結構與性質的公共領域在現代化進程中扮演了不同角色。
所謂“公共領域”,指的是介于國家與社會之間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場所,大致包含了大眾傳播媒介、公共知識分子、現代政黨等要素。
這一理論源于西方,所謂“資產階級公共領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是以“資本主義市民社會”,即建立在產權明晰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與交往為存在土壤的,獨立的大眾傳媒與公共知識分子扎根其上,廣泛而深刻地介入公共政治生活,為社會代言,而國家也借由他們保持對社會的監控與協商,在這一過程中,市民社會逐漸從重商主義與專制主義之下獲得解放。
技術、資本等要素的相互作用推動了近代西方的現代化:地理大發現以及隨后的工業革命帶來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崛起與市民社會的勃興,民族國家逐漸形成,早期的發展以君主專制與重商主義為特征,而隨著民主制度的建立與完善,社會開始日益拒絕專制權力的介入。
傳媒在這一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西方傳媒自誕生起就以贏利為取向,以自立于國家之外的“第四等級”自居,通過信息“無差別傳播”溝通社會,監督政府,向導國民,雖然商業化不可避免地帶來媒介倫理的缺失,但總的看來,西方傳媒與國家之間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張力,在拒絕權力直接控制的同時,也維系了社會的獨立與繁榮。
理論來自于特定歷史環境,不能強行套用,即便是“西方社會”,具體到不同國家仍存在著諸多不同:擁有“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分封制度與古老法制傳統的英國,專制王權對地方社會向來控制不強,15、16世紀的海外貿易與殖民擴張確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英國的統治,“光榮革命”達成了新貴與專制王權的妥協,英國近代報刊也由此獲得了制度上的生存空間。而法國則因其國內階級成分復雜,社會矛盾尖銳導致了革命的爆發,法國近代民族國家最終以共和國的形式出現,法國近代報刊的誕生較之其他國家更多戰斗性,而普魯士市民社會面臨著諸侯割據與專制王權的雙重壓力,近代報刊多依附于專制王權,商業報紙則發展緩慢,遠遠落后于西歐諸國,脆弱的新聞自由直到二戰時期也沒有實質意義上的保障。
“消極社會”與“依附型公共領域”——中國的情況
公共領域溝通了國家與社會,西方公共領域的發展雖存在個別差異,但仍存在很多共性:
首先是制度基礎,既法律對產權的保障,如《人權宣言》,美國憲法等都確認了這一原則。
其次是結構屬性,私有產權與普遍的商品交換賦予市民社會經濟權力的同時,也給予了公共領域獨立于國家控制的資本,公共領域同國家的張力始終存在。
最后是發展路徑,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互為因果,相互促進。市民社會壯大發展的過程也是公共領域不斷擴張轉型的過程,從革命報刊到政黨報刊再到商業傳媒,公共領域的轉型也推動了市民社會的發展。
然而,中西方社會無論是社會經濟形態還是地方組織形態,與國家制度都存在巨大差異,倘若將西方社會概括為“積極型”,那么傳統中國則是“消極型”。
從經濟形態看,中國屬于馬恩經典作家定義的典型東方亞細亞社會(Asiaticsociety),缺乏嚴格意義上的產權,即以法律形式表現的經濟所有制關系,正如經典作家總結,缺乏私有財富,特別是缺乏土地私有權是亞細亞社會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王朝斗爭和軍事征服引起的社會政治結構的周期性變動,并沒有帶來經濟結構的本質變革,土地所有權和農事活動的組織仍舊掌握在實質上的地主即國家手里,自耕農依附于小塊土地,貧雇農依附于地主,手工業者則往往與農民合二為一,共同構成了經濟上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西方語境里被寄予厚望的城市,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含義也完全不同,在西方,政治上獨立的城市,是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而在東方,城市是由國家“人為”創造出來并從屬于農業和農村的,它只不過是強加在社會結構之上的“王侯領地”,從“利出一孔”到“重農抑商”,限制商業活動是中國歷代統治者奉行的政策,有限的城市商業活動被嚴格限制,城市生活無法改變社會總體經濟形態。
在國家制度與地方社會組織形態方面,傳統的帝國政治體制精致而復雜,在國家層面,皇帝及其血緣親屬構成了“家庭權力核心”,這一權力核心與為之服務的帝國官僚體系一道,組成了一個封閉的政治系統,這一系統拒絕社會參與,警惕社會權力的制度化介入,相反總是試圖將其控制力擴展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在地方社會,族長、地主、士紳等地方精英構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地方自治系統,在與官僚體系合作治理地方公共事務的同時,也通過所謂的“文化權力網絡”控制地方。
從結構功能的角度看,在這樣一種“帝國集權政府——地方士紳精英——民間草根社會”三層社會結構里,普通民眾的利益訴求往往很難超越地方,輸入更高層級的政治系統,封閉的地方治理結構與帝國集權官僚體系,共同構成了民間社會利益表達的體制性障礙,這一表達的體制性障礙與小農社會個體權益意識的天然缺乏相結合,加劇了普通民眾國家認同感的淡薄與對鄉村之外公共政治生活缺乏了解,社會既無法凝聚與表達自身利益,也沒有順暢的參與渠道遏制權力的擴張,推動政治健康發展,一旦國家權力肆意妄為到一定程度,則會觸發社會的強勢反彈,進而改朝換代,如此往復構成了一個“國家——社會”消極互動,社會循環停滯的怪圈。
“消極型”社會帶來的是“依附性”公共領域:“結黨營私”,“君子不黨”,“黨”在中國傳統語境里只表示由個人利益與政治傾向而結成的小集團,既無直接的社會階級基礎,也沒有合法存在的制度空間,以致連語意本身也略帶貶義,“朋黨之爭”被認為于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近代意義上代表特定階級,有鮮明的政治理念,圍繞國家政權展開爭奪的政黨并未出現,而知識分子與讀書人,在“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度刺激下,將進入并依附于官僚系統作為目標,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不可想象,只有如李贄、黃宗羲等被摒棄或游離于體制之外的知識分子才能在歷史上留下曠古之音,至于所謂“傳媒公共領域”,其依附性和消極性也非常明顯:
首先,官辦媒體始終占據主流,有研究者認為,組織傳播而非大眾傳播是中國古代新聞傳播的基本屬性。①從唐代《邸報》到宋代《進奏院狀》再到明清官報,地方或中央官僚機構主辦的報紙,作為唯一合法存在占據主流話語權,報紙既承載了官僚體系情報交流與社會控制的職能,自身也作為等級社會的一部分,將“士”以下的普通民眾排斥于受眾群體之外,這一傳播理念上可追溯到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論述,與“新聞即民主”相去甚遠,實踐中無法滿足社會所需的信息流動。
其次,民間傳媒在夾縫中畸形發展,無法為公眾代言。市民小報以信息傳播的高時效性與可讀性受到民間社會的歡迎,但在歷史上沒有制度存在的空間,實踐中屢遭打壓,從北宋到明清至民國,“報案”不斷,文字獄更是登峰造極,“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