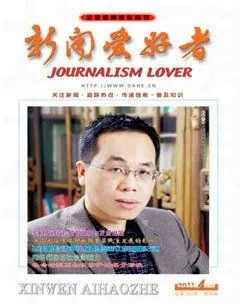《桃花源記》藝術新探
任何好的思想內容,都必須借助完美的藝術表現形式來表現,才能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感染讀者。換句話說,也就是深刻的思想內容只有與完美的藝術表現相結合,才有可能成為久傳不衰的佳作。那么,東晉詩人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的藝術手法是什么呢?
且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
作者娓娓道來,貌似平淡無奇,其實不然。聯系后文,我們可以說,“漁人”的這次遭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偏偏就被“漁人”遭遇了,這種可遇而不可求的遭遇,不恰恰正是“漁人”的“奇遇”嗎?“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其景美不勝收。想想陶淵明生活的時代,兵戈不息,戰亂頻仍,整個社會到處不都是斷壁殘垣,滿目瘡痍嗎?外界的景象同這里的美景相比,此處美景豈得不為“奇景”!正是這里的“奇景”吸引了“漁人”,讓“漁人甚異之”,故引發“漁人”尋幽探勝之“奇想”,他才“復前行,欲窮其林”的。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桃花林的盡頭,就是溪流的源頭,在那里發現了一座山。要知道,一個以打魚為生的“漁人”,在那樣一個社會里,生活的重擔是多么沉重地壓在他的肩頭!可是,眼前之景讓他陶醉,使他“忘路之遠近”,一直順著溪流且行且欣賞,直到溪流的盡頭,發現了那座山。這“奇景”誘人,不是最好的說明嗎?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有“小口”之山道多矣,不足為奇;但有光便有光,無光就無光,這里卻是“仿佛若有光”,不能不引發讀者奇異的感受。這就是進入桃花源社會的“奇門”。果然,“仿佛若有光”的神奇吸引著“漁人”,使他“便舍船,從口入”,于是,似平凡但又神奇的景象再次出現了,那個山洞“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桃花源社會終于撩開神秘的面紗,連同桃花源里的人們一同出現在“漁人”面前了:“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這里的“土地平曠,屋舍儼然”,“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與外界和平年代,太平盛世也無二致。但須知,對于看慣了兵災戰禍,聽慣了在戰火蹂躪下人民痛苦呻吟的“漁人”來說,眼前的景象怎能不令其大吃一驚!特別是這里的人們,“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無論是老人,還是頭發下垂的兒童,都是那么精神愉悅,恐怕在當時的外界社會,是找不到的。“漁人”真的是世外遇“奇人”了!
桃花源里的人們見“漁人”,先是“乃大驚”,繼而“問所從來”,“(漁人)具答之”。一番問對之后,疑惑盡消,于是熱情好客的桃花源人們“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在那個糧食尚不足以養家糊口的時代,桃花源人們對一個素不相識的偶遇的“漁人”尚且如此熱情款待,恐怕也是當時外界之人難以做到的!這淳樸的風俗自當也是“奇俗”。
酒宴之間,賓主的話匣子打開了,桃花源社會里的人們向“漁人”介紹了他們來到此間的原委:“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原來這是一群“避秦時亂”而“來此絕境,不復出焉”的人,這不正是一群“奇人”嗎?自避亂絕境至“晉太元中”偶遇“漁人”,一千多年過去了,外界的事情當然一概不知,“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桃花源人們竟然連外界改朝換代的大事都不知道,對外界發生的一切,他們只能“皆嘆惋”。讓人稱奇,卻又合情合理。
這里,讀者更應當注意:桃花源社會的人們因不堪戰火之苦而避亂隱居,那么生當陶淵明所處的那樣一個亂世,陶淵明又該怎么辦?顯然,桃花源社會的人們已為陶淵明做出了榜樣。作者在奇異故事的娓娓敘述中,就已經把陶淵明對現實的憎惡和對理想的追求和盤托出了。
飽嘗了外界戰亂之苦,避亂“來此絕境”的桃花源人們,當然不愿意重新回到遭受殘酷剝削與壓迫的外界社會,他們過慣了“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①的自在生活,所以當“漁人”“停數日,辭去”之時,他們叮嚀囑托“漁人”:“不足為外人道也。”但這次的“奇遇”怕是以后很難再有,而桃花源社會,桃花源人們留給“漁人”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沿著來時的路歸去之時,“漁人”是“處處志之”。可是,當武陵太守得到“漁人”的報告,“遣人隨其往”,竟然“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連“南陽劉子驥……聞之,欣然規往”,也是“未果”,“后遂無問津者”。桃花源社會偶爾露了一下“崢嶸”,卻又忽然不見了,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而去桃花源之路前文似寫得可尋可見,后又突然難尋難覓,雖名曰“奇蹤”,亦不為過。《桃花源記》所記之事,亦可謂“奇事”矣。
綜觀《桃花源記》全文,雖然乍看好似平淡無奇,實則處處設奇,雖譽為“奇峰林立”,也不為過。《桃花源記》雖處處蘊奇,但整篇文章非但不給人以荒誕不經之感,而且恰恰相反,它卻令人感到真實可信,其原因又何在呢?原來,文章之奇又是借助平凡的事物來表現的。
首先,《桃花源記》文筆質樸自然,通篇無生僻艱澀之字,更沒有佶屈聱牙之句,看來似乎是平淡無奇的。但這些看似平淡的語言,敘述起來卻是那樣從容不迫,層次井然,細膩逼真,娓娓動人。作者以漁人行蹤為線索,以漁人所見所聞為根據,處處給人以耳聞目睹、身臨其境之感。所以,盡管文章奇峰迭起,讀來卻是那樣親切,令人信服。
其次,作者的奇特幻想全部是借助平凡的事物來表現的。桃花源里沒有瓊樓玉宇、奇花異卉,也沒有悟道仙人、珍禽異獸,有的只是土地、房屋、桑竹、雞、犬和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為每一個讀者所熟悉。但是,就是這些平凡的事物,在作者的筆下卻組成了一幅優美、和諧的畫卷。“土地平曠,屋舍儼然”,不是外界的斷壁殘垣,滿目瘡痍;“雞犬相聞”,不是外界的兵荒馬亂,雞飛狗跳;“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同外界人民因兵災戰禍的蹂躪和賦稅徭役的殘酷壓榨而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痛苦呻吟,更形成鮮明的對照……這些極平凡的事物就是如此和諧地組合在一起,猶如一幅奇妙的圖卷,顯示出陶公對現實的不滿和對桃花源這樣的理想社會的熱烈向往。
其實,“凡”和“奇”有機結合,“凡”中蘊“奇”的基調是作者一開始就定下了的,并且貫穿著文章的始終。“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極為平常的一句話,交代了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和發現桃花源這神奇社會的人和他的職業。作者似乎在告訴讀者,這是一個平常的漁人的經歷,是一件平凡的事情;但是作者把故事發生的時間安排在“晉太元中”,讓人無從查考,這似乎又在暗示讀者注意故事的傳奇性。然后,循著漁人的行蹤——經桃林,越山徑,桃花源社會終于在“豁然開朗”的天地里出現了。但作者卻沒有讓這個社會的主體——桃花源中人立即露面,而是著力對這里人們的生活環境作了一番側面烘托:“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通過這步步深入、層層展開的渲染,桃花源人們終于出現了:“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悉如外人”四字,把桃花源人們以極平凡的面目展示在讀者面前。不僅如此,而且桃花源人們竟然連外界改朝換代的大事也不知道,似乎是愚魯的,實在平凡極了;但他們卻對一個素不相識的外來客人“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這樣,既顯出這里的和平與安寧,也顯出這里人民的生活富足和風俗淳樸。同外界人們的生活相比,又是一個奇跡。至于下文,如上所述,作者更是在不動聲色的敘述中充分顯示了故事的傳奇性。
由此可見,《桃花源記》是掩蓋于平凡的外衣之下的一篇奇文,“凡”中蘊“奇”,“奇”由“凡”生,是它的藝術特點。正因如此,才使文章既變幻莫測,又似實有其事,令人信服。我想,把清人沈德潛《唐詩別裁》中評論李白絕句時“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使人神遠”②的話移來作為對《桃花源記》的評價,應是十分恰當的。只不過《桃花源記》是散文,而非絕句而已。
“凡”中蘊“奇”,并非只有《桃花源記》一篇作品如此,陶淵明的全部作品,特別是那些恬淡清遠的田園詩,何嘗不是篇篇皆然呢?他的人格是那樣平凡而偉大,他的作品是那樣“天然”而“真淳”,飄然靜穆與“金剛怒目”本來就是矛盾統一體的兩個方面。有其人方有其文,孰云非然呢?
注 釋:
①《桃花源詩》。
②轉引自游國恩:《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
③陶淵明:《移居》。
(作者單位:周口師范學院中文系)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