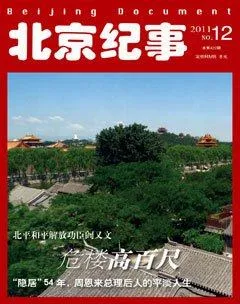塵封的歷史(下)
歷史已經塵埃落定,但閃爍在其中的那些真實、那些細節,至今還在被掩埋,我們的任務,是把覆蓋在上面的那層塵土輕輕抹去,露出歷史本來的面目。盡管它曾經是那樣殘酷,那樣讓人觸目驚心……
呂植中:愛國將領呂汝驥之子原民革北京市委秘書長
呂植中,是我采訪的這些將領后代中口才最好的一位。那天我們在玉桃園民主黨派辦公樓里聊天,不知不覺兩個小時過去,仍感覺有些話沒有說完。
他說,他父親呂汝驥1920年畢業于保定軍官教導團,教導團中有兩個人對他影響最大,一個是教育長徐永昌,另一個是同班同學續范亭。
徐永昌與呂汝驥是多年的上下級關系,徐曾任軍令部長、國防部長,抗戰勝利后,在密蘇里艦上代表中國政府以戰勝國身份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他在民國身居高位,地位顯赫,還有長期記日記的習慣,把身邊所發生的一切都記錄下來。可以說徐永昌的日記與蔣介石的日記都是當代研究民國史的極其珍貴的史料。
1924年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發動北京政變,組建國民軍,呂汝驥被編入國民軍第三軍第一混成旅第二營任少校營長,混成旅旅長就是徐永昌,此后一直跟隨徐轉戰多年。呂植中說,國民軍是一支進步的軍隊,堅決執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鄧小平等許多共產黨人以及蘇俄顧問都在國民軍中工作過。1926年初,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率先與北洋軍閥開戰,拉開了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序幕。
說到這里,呂植中從書柜里翻出一卷厚厚的紙,打開來給我看,那是一張從石碑上拓下來的拓片,字跡有深有淺,不像書本里的字那樣清晰,但若仔細辨認,還是大致能看出一些端倪。他說,這是保定軍校紀念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找到的一塊石碑,上面因有呂汝驥的名字,才拓印出一份給他。碑文記述了國民軍將領石掄元1926年初在與北洋軍閥的戰斗中英勇犧牲的事跡和他與好友的情誼。碑文開頭是這樣寫的:“石掄元字雅山,直隸高陽人,保定軍官教導團學生,同學中與劉金波、呂汝驥、楚憲曾、續范亭特友善……”呂植中在講解碑文時說,這場戰斗十分激烈,他父親也身負重傷,腿被打斷,劉金波在戰斗中也英勇犧牲。呂汝驥時任國民三軍一師一團團長,師長就是徐永昌。
呂植中說,2002年他隨民革中央訪臺,徐永昌后人送給他一本徐永昌寫的《求己齋回憶錄》,從書中才知道,是他父親一舉奪下灤州城而標志著北伐戰爭的結束。那是1928年9月,北伐軍與直魯軍閥聯軍在灤河膠著數日,直魯聯軍以灤河為屏障,垂死抵抗,徐永昌指揮的第三集團軍面對灤河“再無力前進”,就在此時,第三集團軍少將騎兵旅長呂汝驥率部在灤河最下游涉河,進行大迂回,突然殺回馬槍,一舉奪下直魯軍閥聯軍的最后堡壘——灤州城,這是北伐戰爭的最后一役,由此結束了北伐戰爭,這一天是1928年9月13日。徐永昌在書中寫道:呂汝驥有立霍去病功業之才。
說到續范亭,呂植中說這是影響他父親一生的好朋友,說著,呂植中又翻出一本雜志,找到里面夾著的一張復印紙,給我看他父親的另一份資料。那是一份密密麻麻寫滿英文的病歷,記述了呂汝驥1926年初在協和醫院做接腿術的經過,病歷中親屬欄內填寫的就是續范亭的英文簽名,可見他們之間關系的親密。這張難得一見的80多年前的老病歷,也是呂植中費盡周折從協和醫院病案室找到的。
續范亭也是一個頗有傳奇色彩的人物。1935年12月,面對日軍占領我大片河山,看到仍有國人麻木不仁,“男的長袍,女的短袖,不是行尸,便是走肉”,續范亭前往南京“文諫”蔣介石抗日,遭到蔣的不理后,想用自己的死來喚醒國人。他獨自一人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盡,并留下一首絕命詩:“赤臂條條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竊恐民氣摧殘盡,愿把身軀易自由。”當他獲救被送進醫院后,張學良、楊虎城等人親臨醫院看望他,給蔣介石施加壓力。可蔣介石卻讓特務監視他,只要發現他與共產黨有聯系就抓起來。續范亭出院養傷曾住在呂汝驥家。續范亭誓死不做蔣介石的官,后來,他到了延安,跟毛澤東成為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毛澤東、周恩來等很敬重續范亭。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下,各地相繼成立由社會各階層組成的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山西一時成為國共合作的典范。經周恩來推薦,續范亭擔任山西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主任。1947年續范亭病逝,毛澤東給他寫了副挽聯:“為民族解放,為階級翻身,事業垂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懷,有松柏氣節,典型頓失,人盡含悲。”
呂植中在給民革黨員講黨課時,常引用毛澤東的這副挽聯來說明為什么民革能與共產黨走到一起:一個是為了民族解放事業,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一個是為了階級翻身,共同推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
呂汝驥與續范亭是好朋友,抗戰時期,他們都在晉綏地區參加抗戰。續范亭任第二戰區高參、山西新軍總指揮,呂汝驥任晉綏軍騎兵師長、騎兵第四軍副軍長。抗戰勝利后,為了避免內戰,續范亭做過很多人的工作,包括多年好友鄧寶珊、呂汝驥等。呂植中說,他一直珍藏著一本《續范亭詩文集》,這是續范亭病逝后由解放區出版的,是續范亭夫人送給他父親留作紀念的,續范亭的革命精神對他父親影響極深。為了不打內戰,呂汝驥寧肯解甲歸田,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盡管老上級徐永昌乘專機來北平,說服幾位將軍跟著他回到南京,但此刻呂汝驥的心意已決,徐只得一個人返回向蔣介石復命。
呂植中說,早在1920年在靖國軍參加護法運動就結識的鄧寶珊將軍,曾與他父親一起商討過北平和平解放的事情。他父親隨傅作義起義后參加了解放軍,在解放軍高等軍事院校做教官,后來轉到民主黨派工作。他父親最終與共產黨走到一起的親身經歷,對呂植中影響很深。他說,他父親總教導他們:“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至于呂植中他自己的經歷也比較坎坷,他給我講述的也非常多,也非常精彩,但礙于篇幅,這里只能忍痛割愛。
覃珊:原國民革命軍第52軍軍長覃異之之女現任荷蘭飛利浦公司市場部經理
覃珊出生在1963年,是覃異之最小的一個孩子,她上邊有好幾個哥哥。因為是老來得子,父親和家里人都對她特別疼愛,所以她一直過得很順,在北京生,北京長,沒經歷什么坎坷。覃珊是在史家小學上的小學,北京二中上的中學,大學考的是北航分院,學的是精密儀器專業,畢業后被分到輕工業局下屬的手表元件二廠,當技術員。在母親生她的那年,覃異之已經從香港回到內地。
民國時期,覃異之擔任的最后一個職務是南京衛戍區副總司令,1948年他因為不愿意打內戰,從內地去了香港。他手下有個副官,是中共地下黨,過去就經常做他的工作,到了香港以后,那邊的地下黨又找到了他,動員他參加“周三座談會”。參加這個會的成員都是反對獨裁、熱愛祖國的民主人士。受他們影響,1949年,覃異之與黃紹、賀耀祖、李默庵等國民黨人一起通電宣布起義,徹底脫離蔣介石的反動集團回到內地,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香港起義”。回到內地以后,覃異之就在水利部任參議室主任(水利部部長是傅作義將軍),后來他又當選歷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委、國防委員會委員。等到覃珊大學畢業那年,他又擔任了北京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職務。
按情理來講,覃珊是覃異之在晚年才有的愛女,一直被父親視為掌上明珠,以他現有的權力,像其他大學畢業生家長那樣給自己的愛女找找關系,托托門路,到一家研究所或者機關上班,是件輕而易舉的事。覃異之卻堅決不肯這樣做,他對女兒說:“是國家培養了你,送你上的大學,現在國家分配你到哪兒,你就要到哪兒去。”非常公私分明,鐵面無私。覃珊當時還有些想不通,可最后還是聽從父母的話,去了手表元件二廠。到了工廠以后,她經常要下到各車間實習,了解生產情況,只不過因為她們是女生,沒讓她們干什么笨重的活計。后來,她還參加了工廠的質量控制小組,重新規范了新的生產程序,建立了全面質量管理體系,并通過了上級的驗收。就在這期間,她加入了北京市青聯組織。
覃珊說起她加入青聯的過程,也覺得蠻有意思。
“80年代中期,胡耀邦曾有一個批示:要充分發揮這些民主人士后代的作用。1987年鄭建邦就找到我父親,說您女兒在第二代中算比較年輕的(那時我才23歲),想推薦她做北京市青聯委員。鄭建邦當時就在民革中央聯絡部工作,和我們住一個院,彼此并不認識,只是他的祖父鄭洞國和我父親是至交。但是,我父親當時不知道青聯是怎么一回事,就說她剛參加工作,忙,沒功夫。后來還是我媽說,這是好事呀,可以多認識人(現在看來母親有讓女兒找男朋友的“私心”)。父親就又去找鄭建邦,這才讓我填表,要經過考查什么的。加入青聯一年后,由于工作的需要,組織讓我脫產專職做青聯工作,可工廠卻不同意,還是市委組織部發了一個調令,把我調出廠子。青聯有一個專做宣傳工作的內部通訊,就讓我去負責,我在那里一共干了兩年。”
覃珊雖然很早就不在青聯做專職工作,但擔任了三屆青聯委員。那個時候,青聯經常組織一些有意思的活動,她都積極參與。比如1995年,青聯舉行京港澳青年“抗日戰地行”活動,選擇的都是國共兩黨當年抗日的地點,包括盧溝橋、古北口、京西抗日根據地、焦莊戶等,當時有一百多人參加,都是港澳臺青年,以及大陸這邊抗日將領的后代。
這次戰地行,尤以古北口留給她的印象最深。因為覃珊的父親覃異之將軍,當年就參加了這場異常慘烈的長城保衛戰。她父親曾跟她講過,在戰場上他們對日殺敵已經殺紅了眼,身為團長的他,幾次都想冒著槍林彈雨,沖到最前線,為戰友報仇。如果不是身邊衛兵拼命拉住他,他早就戰死在那里了。古北口的向導介紹,戰爭結束后,當地老百姓曾把這些烈士的遺體掩埋起來,還修了一座墓。到了文革,因為沒有人敢管,古北口烈士墳墓都荒蕪掉了。直到改革開放,重新認識這段歷史后,當地人才重新開始修繕維護。“我聽完以后,也是熱血沸騰,那時兜里僅有兩千塊錢,一下子就全都捐了出去。”不僅如此,覃珊聽說他父親這支部隊當時是從南方調過來的,穿的還都是涼鞋、單衣,沒想到到了北方天氣這么寒冷,供給又跟不上,還是當地老百姓和北平各界愛國人士給他們捐的衣物呢。
覃珊說,他的父親這一輩子打過許多仗,光是著名的大仗就有古北口保衛戰、臺兒莊戰役、徐州會戰等。他還愛寫詩,寫得還很不錯,這些詩許多都是他在長途跋涉的行軍途中寫的,其中有一首《夜行軍》是這樣寫的:“馬首懸新月,三軍氣若虹。夜寒茶當酒,星斗落杯中。”這首詩刊登在當時的一家報紙上,柳亞子老先生看到后,大為贊賞,就給她父親起名叫“詩人將軍”。張廉云大姐(即張自忠之女,曾任民革北京市委主委)也很喜歡這首詩。后來,她正好在學書法,還特意把它寫成大字,送給他們,現在還掛在家里的墻上。
“我父親與世無爭,覺得自己經歷過那么多次戰爭,許多將士都陣亡了,那些人的家里至今都不知道他們埋在哪里。和他們相比,自己能幸存下來,已經非常不容易,很知足了,所以從不與人爭什么名利。這點對我們家里人影響很深,這也使得我對功名看得很淡。
“父親留給我另一件印象最深的事,就是他去世的時候。他是因為肺炎住進的復興醫院,由于肺炎已是晚期,他只有切開氣管,借助呼吸機才能正常呼吸。在切開氣管之前,他最后說的一句話是:‘臺灣問題怎么樣了?’還有一句:‘鄧小平身體怎么樣了?’后來氣管切開,他就再也不能說話。我們就用筆在紙上寫,問他什么事,他就點頭、搖頭。我父親特別關心國家大事,訂了一輩子《人民日報》,每天都要堅持看。我每次去都要給他拿當天的報紙,雙手舉在他的眼前,他就躺在病床上,哪怕只能看見大標題,他也要看。一次,我忘記了拿報紙,就隨手拿了一張廣播報,舉給他,他就用眼珠子使勁瞪我。”
也就在這次談話中,我知道覃異之將軍是個孤兒,3歲時父母即已去世,他還有兩個妹妹,也都不幸早夭,是被外祖母一手帶大的。因此,他家里并不富裕,即便如此,外祖母還是很重視對孩子的教育,給他請私塾老師,教他識文斷字,接受傳統的孔孟之道等禮儀教育。覃異之早年非常好學,尤其喜歡歷史和古詩,這為他后來成為國家棟梁打下了很好基礎。我看過有關資料,很多地方都說覃異之是廣西壯族人,當我就這一點向覃珊求證時,她卻堅決予以否認。她說,她父親一直認為自己是漢族,而且是古代名將狄青的后代,十七代以前從山東遷過去的,后來改姓的覃。那時人們都跟他說:“壯族好,以后子女都可以跟著沾光的。”他聽了,就急扯白臉地跟人家急:“我就是漢族。”她父親就是這樣一個性格耿直、公私分明,甚至有點不近人情的人。
有一次,他出國去日本訪問,經常給他開車的司機跟他商量,能不能順便幫他買一個打火機,卻遭到覃異之的一口回絕:“我這是去訪問,哪兒有什么功夫逛商店。”
按照覃珊的話說,如果不是她母親,他這輩子不知要得罪多少人。但這也從另一方面體現出他從不拍馬屁,從不搞歪門邪道的可貴品質。文化大革命當中,周總理寫的一份被保護人的名單,其中有覃異之的名字,他們一家才免受沖擊。另外一個沒有受沖擊的原因,是覃異之在南京解放時,保護了當地的電廠等設施,并巧妙釋放了不少被關押的中共地下黨成員,作過貢獻。覃異之雖然過去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但他的屬下有地下黨員,他又參加過“香港起義”,是著名的抗日愛國將領。覃異之下屬的那位地下黨員,“文革”落實政策后還到過他家,跟他開玩笑說:“我這個正牌的都受到沖擊,你倒沒什么事。”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覃異之在新中國的地位和榮譽還是很高的。200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向抗日老戰士、愛國人士、愛國將領、國際友人頒發“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時,覃異之很榮幸地獲得其中的一枚,他的夫人和女兒覃珊,代替他領取了這枚珍貴的紀念章。
(編輯??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