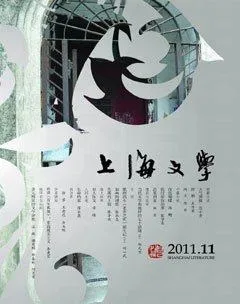如畫的理想
1
大概從六歲上幼兒園時起,我就喜歡涂抹勾畫。一年后上了盔甲廠第一小學(即匯文小學),大概是因為有了課桌吧,畫畫的愛好,立即就成了癡迷。記得我把課本每一頁的邊角空白都密密畫滿,被老師罰用橡皮擦干凈。大約在二年級那年的新年,我給班上的同桌和好友都畫了一張賀年片。
盔甲廠一小的同學們那時有一項享受:課間操后聽孫敬修老師講故事。須知孫敬修和收音機播出的他那勸善如流的娓娓故事,是北京1950年代的一個象征——孫老師遠遠在臺上講,我們全校千余名學生,就那么一班班原地站在大操場上,一片寂靜,聽得如醉如癡。
應該是我上三年級(1957)那年,孫敬修老師當了我們班的圖畫老師。不用說,我在孫老師的課堂上如魚得水,成績一色五分。只有一次例外:那次孫老師說畫自由畫,但也可以臨摹他拿來的一張。后來才知道全班都畫臨摹,唯有我一個獨自陶醉,在心在意畫了一幅《黃繼光堵槍眼》。萬沒想到,從來慈愛綿軟的孫老師突然不高興了,帶著氣給了我三分!
我震驚無比。圖畫課的三分,于我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此刻回想琢磨,或者當時我沒聽見孫老師改了主意讓大家都畫臨摹?抑或是那天孫老師有心事,而我卻表現得狂妄招嫌?
可能是后者。三年級的我在圖畫課上得意忘形,幾乎是無疑的。
一定是那時我尾巴翹翹的樣子,讓和善柔順的孫老師反感了……只可惜這反省,晚了半個世紀!
那個三年級是我人生中第一個厄運之年。唯能憶起的一件事,是和班上一個混血兒打了架,而班主任,我以為她決心要把我逼入死地,盤算給我學生手冊的“操行評語”寫“差”。因為她執犟地逼供,要我承認“屢教不改”。而這四個字,乃是將“勒令退學”的“差”級評語的原文。
我心里唯有一個念頭:要是承認了“屢教不改”,母親會出什么事?那一天母親勞累的影子充斥了腦海,我咬緊牙關,就是不回答這一句。天漸漸昏暗了,學校里已空無一人。班主任還在堅持問:“你說,你這算不算屢教不改?”
就在那絕望的時刻,突然孫敬修老師從一旁路過!
孫老師認出了我:“喲,這不是……他怎么啦?”班主任輕描淡寫:“他犯錯誤了。”
孫老師喃喃說:“是么。張承志在圖畫課,可是好學生呀。”
早想了事回家的班主任借坡下驢,死刑突然緩期了:“哼!看在孫老師的面上,今天就算了。以后再犯……”
今天我寫著依然感動無比。
多少年了,我牢記著他這幾句話的原因,尚不是為了追述我與孫敬修先生之間短暫的私淑之交,而是因為他的救援結束了“屢教不改”的糾纏,讓操勞的母親遭受連坐的恐怖,被化解了!
2
十大建筑的興建,終結了我們貧寒豐富的胡同生活。四年級那年,搬家轉學以后我發覺,朝陽區的熱鬧事(今天看來是藝術氣氛),要遠較城區高得多。合唱團,詩朗誦,不知不覺就忙得不可開交。很快我被選入朝陽區少年之家美術組,在一位姓董的輔導員門下,進入了準專業的美術訓練。
董輔導員是位極棒的畫家和教育家。
他用油畫和彩墨,分別畫了兩幅京劇肖像。我們底下嘀咕說,扮演蘇三的畫中人女演員,就是他的女朋友。
我久久地看著。油畫濃烈透明、彩墨揮灑自如,如在我癡癡凝視的眼前,展示著美術境界的可望不可即。
他對我們的素描訓練,完全是科班水準。美術組分為初中組和小學組,初中那伙大哥大姐已然是藝術家派頭,他們畫那種卷發的石膏頭像,忙著考入美院附中之前最后的臨陣磨槍。而我們小學組則永遠對著石膏六棱體或三角錐,每周日畫一個上午。董輔導員要求我們把自己積累的素描時間寫在畫紙上,他強調:你能找出的“面”愈多,你就能畫更長的時間。
已是三年饑荒的邊緣。美術組除了白紙、水彩、鉛筆之外,不能提供任何畫具。油彩像比夢還遙遠,輔導員的方針是堅定地畫素描。一次,他把吃剩的半個窩頭替換了石膏。我們一邊畫得眼花,一邊懂了為什么打基礎:窩頭真難畫啊。
創作畫的機會很少,但董輔導員不是孫老師,他讓我們“愛畫什么就畫什么”。這回我在心在意畫的是一幅《收麥子》,一輛大車上坐了幾個紅領巾,一位老大爺揚鞭吆車,夢想中心愛的馬,占了一半畫面。輔導員把我的這幅創作裝進鏡框,掛在美術組的墻上。這一回我可沒敢得意:滿墻的畫里數我這一幅最差。何況我已懂得,展示的作品未必優秀,有時是為了比較討論,才掛到墻上的。
一天,看見董輔導員端詳它,我們也圍過去。輔導員轉過臉問我:“你是不是見過趕車的坐在右邊?”
我茫然。他卻高興地說:“我一直覺得有些怪,今天終于發現,老大爺坐在車轅右邊!一般趕車人是坐在左邊的……”
我也猛然看清了!就在那一天,一種關于生活真實與畫面平衡的思路,植入了我的心里。
每個星期天,從三里屯步行走到下三條,喊上一個美術組的伙伴,出神路街,進入壇口,走過靜謐的日壇,推開紅墻小院的木門,削尖幾支中華牌的鉛筆——唉,日壇公園里的少年之家!難忘的美術組的每一個小時!
還有好多事,反正弄不清了。比如我們小學組曾來了一個據說是張仃兒子的小孩,是我的住在白家莊美術界宿舍的小學組伙伴祝重壽(一次我在一份雜志上又見到這個名字)領來的——但后來提起此事,人們說,張仃的小孩?就是張朗朗呀。我愣了,張朗朗與我也有一面之交,怎么比那小孩壯多了?雖然無關緊要,但有了機會,我要問問張仃先生的夫人、詩人灰娃先生。
初中組有一個苗條高挑的女生,在小學組眼中簡直像一個仙女。寫這篇散文我突然悟到:她一定就是我的恩師翁獨健先生的三女兒翁如蘭!直感不會脫靶,除她再無別人。讀研究生時我和她很熟,但是從未談過她的畫,她肯定覺得念蒙古史的學究怎么會畫畫呢。“文革”中,她因為一幅漫畫《百丑圖》在美術界出名招禍,無人知道她的素描基礎也相當了得。
——猜錯了也可能。那就是說,在那個時代,美術音樂各界,都是“五陵年少”和窈窕才女的出沒之地。
而在當時,如我的一個少年,對周圍人際是遲鈍的和不觀察的。我的視線和感觸,牢牢地聚焦于另一些地方——
那次董輔導員在畫那幅油畫蘇三。他手持調色板,目光平視,胸有成竹。在小學組嘰嘰喳喳圍觀之間,他手點色到,一支油畫筆宛如魔棒。
畫面上那個濃妝的畫中人,一筆一筆地活了。難以言傳,無可話語。濃烈的、閃亮的、透明的、魅人的油畫啊,你把一個小孩的心擄掠了!
我對那幅油畫肖像不能釋懷。
多少年了,我依然用童心中殘留的那幅畫的印象,去衡量見到的流水一般的畫作。人們嫌我評論的苛刻,卻不知我心里的貯藏。在我心中,那幅油畫是完美的。它干凈凝重,瀟灑如夢,肖像比模特更加無瑕。它給我留下了油畫高貴、不可侵犯的教訓,而我一生都把它用在了別處。
3
我忘了為什么自己沒考美院附中。
也許是因為初中組他們畫得太棒,我一邊看著自認不如于是溜了?
也可能是因為那時的學畫——多少意味著一點生活的余裕,甚至家境的富裕。初中組沒有意識到,他們似若兩界的談吐舉動,被一些少年敏感的眼睛注視著。也許就是因為那某一種差別,我甚至連思想斗爭都不曾有,就悄悄地退后,離開了我少年時代的第一個理想。
不是美院附中,而是錯入了重理輕文的清華附中,泰山壓頂的數理化和歇斯底里的外語課,猛地終止了我的快樂涂畫。
隨即是強風席卷的革命。
理想在激烈地置換著。沒有誰說他想當醫生或者歌唱家。
我就更是一樣,大字報上,忘了插圖,待到某一天早晨醒來,睜開兩眼打量外面時,世界已換了塞北草地一面平鋪的、殘酷的雪原。
在內蒙古大草原的四年沒有意識到應該畫速寫和創作——足以說明我不是畫家坯子,缺乏藝術感受。
真的,怎么我就連想都沒想過一次畫畫呢?我滿腦子都塞滿了革命、大隊、蒙語、羊群嗎?我視野里充斥的只是汗敖包、薄勒嘎斯太渾地、額爾登陶勒蓋、泰來姆么?我的潛意識里只存在明珠爾的額吉、穿破的羊皮德勒和折裂的氈嘠達、晚上歸牧時吃得橫出的羊肚子、在夏天辛苦挖出來但被人在秋天盜竊的為了過冬的羊糞磚?
反正就是沒想起來畫。
哪怕我們大隊死了一個叫黃秀玲的女知識青年,我們用紙板畫了一套她的英雄事跡,包在包袱皮里騎著馬挨戶在牧民中宣傳——那套畫主要是我畫的——我依然沒想起來畫畫這件事!
若是心在別處,就說什么也沒用了。
這種沒有描畫蒙古草原的遺憾,一直到了1976年第一次在新疆伊犁草原發掘時,才突然從心里躥了出來。炭筆、鉛筆,我叫苦連天地涂著,埋怨著自己怎么在內蒙古居然沒有一根鉛筆。
一次和昭蘇的蒙古巴郎白音合西格一塊兒,深夜里先是步行,后來搭上一掛蒙古人的馬車,踏著美麗難言的夜景,一直從三公社(今天應該改名叫阿合牙孜,或者又改成幾團幾分場了)走回夏臺。
也許只有美景的沖擊,才打破了漫長的惰性。我一邊用炭筆唰唰涂著,一邊對那西蒙青年解釋沒畫內蒙古的原因:“沒工夫呀!那會我們是牧民……”
可能就是這么回事。
我們在蒙古草原的插隊,與那些特權精英全然兩樣。很難解釋成什么脫胎換骨,只能說我們真的變了,變得不僅忘了自幼的愛好,甚至觀點也融入了他者和異類。
游牧生涯給予我的對美的感受,沒有出現在畫布上,卻繞了個彎子差強人意地隱現在我的散文小說里。只是我一直沒來得及說:文學是最粗糙的藝術。由于它手段的簡單(碼字敲鍵盤)和元素的枯燥(無色無韻),它藏污納垢,容忍了那么多惡棍。
我有時也會留戀和后悔。
每次去畫展我都禁不住激烈的興奮。我對每一張思路低劣的作品都能看進去,因為羨慕其基本功的硬度。我對每一幅著名熱賣的大作都不能茍同,覺得它們唯有那么一點色彩能力。
寫累了時,我會陷入遐思,幻想和昔日小學組的伙伴們一塊兒迅速經過美院附中,獲得色彩的秘訣。然后,然后可就不再這么煩人地敲鍵盤啦,我滿心的激情會催我一直畫到傾吐凈盡,抒發酣暢。
但是騅不逝兮時已逝,我明白:雄心不是無知的虛妄,繪畫不是自戀的變態。我會由于喜愛偶爾動筆,會出版自己積攢半生的畫作小品,也會最后完成念念不忘的幾個畫面,但是我注定今世不是畫家,我無力再鍛煉小學組以上的基礎了。
4
這是一個文人騷客如蠅似蟻一擁而上、狎書玩畫的時代,這是一個假畫臭字如垃圾堆塑料袋一樣污染中國的時代。
為了區別,在出版這本收集了數十年速寫、草圖、畫作的心愛小書時,YMksjRCBaPp1lW8FTPv3WQ==我想強調——
我不冒充畫家。這本小書收入的并非“文人畫”,也不敢做美術的炫技。正相反,眺望著自己遲疑的線條和失準的色彩,堵噎我心里的,唯有達不到繪畫境界的遺恨。
我再次掂量了自己——終此一生我只能是一介作家了,雖然我也很喜愛其他語言,包括色彩的表達。
和此書的姊妹作、攝影集《大陸與情感》一樣,此書宗旨并無改變。描寫我的三塊大陸,蒙古草原、黃土高原、天山南北——闡釋大陸上各異的文明,為生息于斯的民眾辯護,記錄他們與我的關系。
只不過這一本的手段,是草圖、速寫,以及繪畫。兩腳踩上的土地,也更擴展到了歐洲、日本、地中海的西半、加勒比與中南美——都是這個地球的關鍵地域。
青海人民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小戴和美術編輯小楊,與我已是比兄弟更深的“同志”關系。由于共有的志向,他們渴望把印出的書,做為給我的齋月禮物。19日深夜,他們從印廠回來后,給我發來短信——
“讓我們一起期待她的問世。”
如上追述,甚至與許多吃著美術飯的職業畫家都不同——畫家不僅是我整個少年時代的理想,而且我還有過一段不算短的學畫史。所以,在自警和不吹噓的同時,我也不掩飾自己的另一種語言憧憬,不掩飾此生要畫成幾幅油畫的野望。
不知我能否說——
這不是什么才能的炫耀,而只是一種學習的記錄。是的,也許已經到了總結的時候:從孩提的往昔,到人生的遲暮,就是這如畫的理想,以及不歇的學習,使我愈來愈扎實地靠緊了——他者與世界,并逐漸完成了一個作家的故事。
基于新著《涂畫的旅程》序言改寫
2011-08-21,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