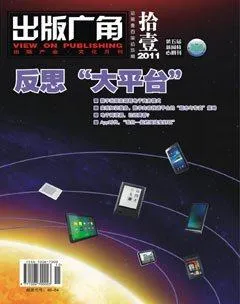數字出版應超越電子商務模式
2011-12-29 00:00:00任翔
出版廣角 2011年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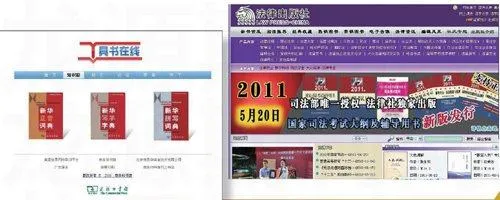


任翔,資深出版人,創新出版(國際)工作室總監,澳大利亞創意產業與創新重點研究中心博士,曾任職于知名出版社與出版集團,擁有十余年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從業經驗。目前致力于數字出版研究與國際在線出版合作。
數字出版已經從概念變成了潮流,出版產業的數字轉型也成大勢所趨。與國外以出版商為主體的數字化不同,國內數字出版呈現出平臺主導的趨勢。在數字出版初期,平臺主要由非內容方構建:比如,由技術商方正建立的番薯網,內容集成商模式的中文在線,數字圖書館模式的知網,硬件廠商創立的漢王書城。近幾年,大型內容商開始創建自己的綜合數字平臺,比如中國出版集團的大佳網,盛大文學的云中書城。此外,通信產業與電子商務的傳統巨頭也紛紛涉足數字出版平臺,最具影響力的當屬由中移動運營的移動閱讀基地,而淘寶的淘花網和當當、京東即將上馬的在線出版平臺也令人矚目……
可以說,中國數字出版已經深深打上了“平臺”的烙印,大平臺幾乎成為商業模式的不二選擇——整合內容、打通渠道、形成集聚效應等等戰略屢見不鮮。縱觀國內的大平臺,雖然數量眾多,看似熱鬧紛繁,其模式內核卻驚人的相似——大平臺做的其實都是電子商務。這一模式能在中國大行其道,并非偶然。首先是Kindle與蘋果應用商店模式在美國的成功,國內數字出版人羨慕之余,都想復制這一成功模板,于是,人人都做內容電商平臺;其次,電商模式本身最易于操作,也最易于理解,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直接數字化印刷出版的商業模式,也就是書店分銷模式;第三,中國的商業文化好大喜功,數字出版企業追求政績、喜歡大而全,喜歡掌控產業權力,所以平臺成為群雄逐鹿的戰場,大家都想借平臺強勢而主導產業鏈。但是,電子商務模式真的適合于數字出版嗎?中國內容電商平臺出現了哪些問題?什么才是符合數字出版發展規律的商業模式呢?
從這幾年實踐來看,大平臺模式的效果并不理想,平臺競合也沒有取得業界公認的商業突破,這引發了業內人士的諸多反思與疑慮。本文不想分析具體策略的成敗得失,而是聚焦于大平臺模式的本質——電子商務,來探討目前數字出版的思路局限以及未來商業創新的方向。
一、電商模式的結構性風險
首先,簡單談談電子商務模式的本質。當年亞馬遜以邊際利潤的概念轟動納斯達克——用產品聚集的馬太效應吸引用戶,用規模經濟獲取超額邊際利潤——引發瘋狂追捧,并吸引了巨額投資。邊際利潤是電商模式的精髓,其基礎是規模效應,而規模效應來源于三個方面:規模性采購以降低進貨成本,渠道整合以減少中間商成本,擴大消費者規模以維系薄利多銷。在實體銷售領域,電商模式縮短了由生產者到消費者之間的距離,優化并壓縮了產業鏈。但是,電商平臺也因此成為連接生產與消費的唯一樞紐,從而掌握了渠道霸權,主宰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為了維系渠道霸權,電商必須承擔巨額成本——物流、倉儲、進貨成本,還要面臨眾多不確定因素,最主要的是用戶需求的不確定性。如此巨大的經營風險使電商別無選擇,只有持續擴大規模,以規模效應來分散風險,以規模經濟來分攤巨額固定成本。這就是電商模式的基本框架,這也是為什么,電商模式——無論是淘寶、當當、還是各類團購網,都一定要“大而全”。
那么,這一模式適合于數字出版嗎?
第一個疑問來自于規模。為什么人人都知道邊際利潤的奧妙,世界上卻只有一個亞馬遜?因為,亞馬遜具有獨一無二的產業鏈規模和產業影響力,這不是一般電商可以復制的。憑借超級規模獲取超額邊際利潤是電商的終極層次,而不是普遍狀態。反觀國內的數字出版行業,2010年,電子書整體產值只有14億元,電子刊物6億元。就個體平臺而言,業內公認的模式最成熟、“錢景”最好數字出版企業——學術數據庫供應商知網與萬方,兩家網站2009年銷售收入總和也只有5億元人民幣。這樣的產業規模,即便集中所有資源于一個平臺,能否形成足夠的經濟規模效應,還是個疑問,況且分散于大小十幾個平臺?換一個角度講,國內目前發展最快的數字出版平臺是中移動,這一模式的成功,根本原因是中移動CP業務早已高度集成化,數字閱讀內容可以與其他信息服務整合,打包賣給消費者;換言之,中移動的數字閱讀借力于其業已形成的規模優勢和產業鏈強勢。但是,其他大平臺,誰的關聯業務有這樣的規模優勢?所以,用電商模式做數字出版,中國多數企業的家底兒還不夠大、不夠強。
第二個疑問來自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差異。把基于實體商品的電商模式套用到虛擬經濟里,能否行得通?網絡書店算是一個成功例子,不過,其售賣的商品——印刷圖書——依然兼具實體商品與虛擬商品的特點;而數字出版平臺銷售的則是100%的虛擬產品。數字出版,作為基于信息、文化和知識的服務,它遠遠超越了簡單的買與賣。尤其是知識的獲取與傳播,絕不是簡單的實物交易,無論是產品特性,定價藝術、渠道通達、還是促銷策略,都與實體商品有很大不同。所以,目前大平臺的做法——把虛擬內容明碼標價,放在網站上,等著用戶放入虛擬購物車,然后付款下載或瀏覽——違背了虛擬產品的經濟特點,這會引發很多問題。比如說,數字盜版泛濫;讀者不認可數字內容的價值;除了內容大賣場,數字平臺無法進一步實現附加價值,等等。
第三個疑問來自于潛在的渠道霸權與渠道依賴。傳統出版產業曾深受渠道霸權之苦,書店渠道的掌控決定了圖書暢銷與否,書店系統的高退貨率和長回款賬期讓出版社叫苦不迭,等等。這些內容方的噩夢,正在數字出版大平臺上重現:能否打通數字渠道,能否在平臺獲得顯著推薦位置,能否得到高額利潤分成,成為數字內容商制勝的關鍵。取悅渠道,而非取悅最終讀者,成為最有效的競爭策略。如果大平臺模式未來成為中國數字出版的唯一渠道,那么,產業結構和價值鏈非但不會優化,反而會形成更強的渠道霸權,這是數字出版應用電商模式最大的潛在風險。與渠道霸權對應的,是內容方的渠道依賴。目前數字出版的現狀是,內容商觀望而不行動。這種觀望的實質,其實是渠道依賴,內容放在等待強勢渠道的出現——比如數字版的新華書店,在等待一個可以依靠的堅強臂膀。渠道依賴的根源是內容方在數字時代的思維方式依然是基于印刷模式的。也就是說,大平臺模式下,內容方沒有足夠的意愿與自信去開拓終端讀者市場,這將成為行業發展的一種思維桎梏。
二、中國大平臺的主要問題
電商模式應用于數字出版,具有上述結構性風險。隨著大平臺在國內的高速發展,很多潛在風險已經演變為實際問題,而且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首先,平臺為了追求規模效應,競相選擇“大而全”的定位。幾乎所有數字出版平臺都想一統江湖、無所不包,恨不得一下子把全世界的數字內容資源都攬入囊中。從形式上看,這種大而全模式簡直就是十幾年前超級書城的數字翻版。瀏覽目前主要的數字出版平臺,內容幾乎千篇一律:原創網絡小說,經典文學作品,舊版暢銷圖書等等,各個平臺間沒有本質差異,已經嚴重同質化。此外,由于多數大平臺自身不生產內容,而目前可供選擇的數字內容有限,所以,個大平臺幾乎都押寶在大眾暢銷書上,這也進一步加重了同質化。可以說,在大平臺模式下,數字出版儼然成了汗牛充棟的堆積品種,而數字閱讀在滿足個性化、差異化需求方面的優勢蕩然無存。
其次,由于缺乏差異化戰略,同質化的大平臺只有依靠價格戰來競爭,無論是盛大與漢王的閱讀器硬件大戰,還是某網站推出的一分錢一本書的促銷,都是在失去差異化、個性化優勢之后的低價競爭策略。但是,大平臺打價格戰的本錢卻并不豐厚。首先,平臺運營的成本很高。雖然販賣虛擬內容可以節省物流倉儲等成本,但維系平臺運營、DRM等依然花費不菲;其次,大平臺并未掌握內容定價權。一方面,優質內容資源掌握在傳統出版社手中,數字電商內容購置成本越來越高;另一方面,內容商對于電子書售價的干預權非常大,例如《春宴》的數字版居然出現了越賣越漲價的不正常現象。定價權的缺失,是中國大平臺無法媲美亞馬遜的重要原因,Kindle電子書的暢銷很大程度源于低價,其價格之低甚至引發了歐美出版商的廣泛不滿,但是誰也撼動不了亞馬遜的產業鏈強勢。第三,最重要的是,作為數字內容產品,用戶需求的價格彈性遠不如實體商品,換言之,降價能否換來市場規模的擴大,也是一個疑問。盛大的半價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也沒有改寫市場份額的格局,便是一個例證。目前,各大數字出版平臺都面臨著尷尬的競爭局面:不降價,死水一潭,吸引不來讀者;降價引發出版商不滿;最尷尬的是,薄利也難多銷。
第三,大平臺模式并沒有給數字出版帶來盈利,相反,卻陷入了“不賺錢”的怪圈。很多出版人將盈利性不足歸結于盜版,其實是很片面的。應該說,盜版的根源在于把電商模式簡單地套用于數字產品,在于忽略了實體商品與虛擬商品的本質差異。從盜版商的角度講,面對幾乎為零的復制傳播成本和盜版帶來的高額商業利潤,這樣的無本買賣,總會有人鋌而走險;從讀者角度講,虛擬商品的高定價沒有說服力,讀者沒有看到數字出版的附加價值,再加上電子閱讀的局限和缺點,正版電子閱讀沒有給讀者一個足夠的付錢理由。目前的大平臺模式沒有能夠真正整合內容資源,并將售賣零散的單一電子書內容轉換為基于數據庫的信息服務,而后者才是數字出版應有的商業模式。不客氣地講,用簡單、粗放的電商模式做數字出版,那么盜版是必然。杜絕盜版的關鍵問題是提供給讀者附加的信息增值服務,提供無法輕易盜版的數字內容產品,面對這一挑戰,基于電子商務模式的大平臺幾乎無能為力。
第四,作為數字內容中間商的大平臺面臨著無米之炊的尷尬。這幾年,國內數字出版遭遇了嚴重的內容瓶頸。這一方面由于傳統出版社的觀望與保守態度,尤其是對盜版的擔憂,使多數內容方拒絕將最新的、暢銷的內容授權于數字平臺;另一方面,數字版權運營非常混亂,各大平臺缺乏清晰的內容定位,缺乏專業的、有經驗的版權經理人,很多大平臺不加選擇地搶購出版社的數字版權,甚至出現了讓出版社哭笑不得的業余經理人,比如,不問出版社的出版范圍就談價格。由于平臺的粗放發展,成熟的出版社在他們身上看不到數字出版的未來,自然也就不愿意將旗下的優質內容授權給“外行”們。從這個角度講,造成今天數字出版內容瓶頸的根源,更多的是平臺的業余和數字出版的亂象,而不是出版社的保守。當然,從出版社角度講,被動地等待超級平臺的出現是一種戰略失誤。
三、從大平臺到差異化
比較傳統出版,數字出版的變革體現于對內容的深度整合與加工,提供高附加值的信息服務,向讀者推送個性化內容,以此來實現生產消費的雙贏。這是數字出版應有的商業模式,但是在中國數字出版業,這一應有模式正在被 “大平臺”理念所扼殺。電子商務思維、大平臺模式正在把數字出版變成數字內容的大賣場,這種簡單粗放的大平臺非但不具備可持續性,而且會耗費大量的數字出版資源,誤導整個產業的發展方向,進一步拉大我國與西方出版業的整體差距。
電商模式與大平臺之所以流行,是因為我們對數字出版的認識尚處于初級層面。很多人嘴上滿是炫目的概念,其商業模式和行動卻體現了陳舊的觀念。電商思維的本質依然是數字化的傳統出版,依然是販賣單一的數字內容。唯一的不同是,出版社以前出售紙本圖書給書店,現在出售數字內容給大平臺。很多從事數字出版的業者,其思維依然是紙本的,而不是立足于信息服務和全媒體版權運營的。此二者的根本差異在于,出版商與讀者之間將不再是通過中間商鏈接,而是直接互動。未來數字出版業務是提供知識服務,是終端讀者關系的維護,是知識聚合中心的構建。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對數字出版商業模式的探索,有必要打破電商思維,減少大平臺依賴,不要迷信馬太效應,應該走一條個性化的、差異化的、多元化的道路。不要把數字出版做成電子商務!
具體來講,數字出版的商業模式要實現兩個轉變,即,由大而全轉向差異化,由平臺主導轉向內容方主導,或共同主導。這兩個轉變其實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在數字出版時代,內容商與渠道是不能截然分離的,靠獨特內容來滿足特定渠道,靠不斷的內容服務來維系渠道,這才是數字出版模式的基礎。然而,大而全的平臺模式,以中間商為核心的電商理念,正在背離這一基礎。差異化道路的根本,不但在于平臺思路的調整,更在于內容商的積極參與。相比大平臺,內容商自建專業化小型平臺應該是更具前景的模式。
這涉及另一個熱點話題,那就是內容商,尤其是出版社要不要自建平臺?這個問題,如果問任何一家西方出版集團,甚至是有一定規模的獨立出版社,對方的回答多半是肯定的。因為在一個成熟、正常的出版產業,出版商在數字化轉型中的主體作用不容置疑,而自主平臺的必要性更是行業共識。但是,中國的特殊情況使數字轉型的主動權掌握在了非出版社勢力手中。更糟糕的是,這種格局偏差進一步削弱了出版社后續發展獨立平臺的意愿。我們看到,很多出版社、甚至出版集團都放棄了自主平臺的開發。
目前,在大平臺模式面臨諸多爭議之時,內容方應該更積極地參與平臺與渠道建設,結合自身內容優勢,打造完全不同的差異化、個性化的數字出版商業模式。這不但事關個體出版社在數字時代的命運,也關乎整個產業的走向和未來。這一轉型如果成功,至少專業類出版社會重新煥發生機,并且開拓出高附加值的信息服務模式,從而由內容出版商轉型為信息服務商。在出版產業整體轉型方面,出版社和內容方對于渠道的介入有利于優化產業鏈,提升內容方在產業鏈的地位,并且獲取經營戰略上的主動。這一內容方與平臺均衡的產業格局,最有利于中國數字出版的健康發展。相反,如前所述,一個充滿渠道霸權的數字出版業,絕不是理想狀態。
最近,亞馬遜大力推廣數字圖書館和讀者包月服務項目,最近又推出了震驚業界的X光智能內容搜索鏈接系統,從中可以看出,這個電子商務的鼻祖,已經意識到了數字出版的獨特性,并在積極探索適合的新模式。國內一些有遠見的專業出版社也開始嘗試自主平臺,無論是內容數據庫,還是銷售本版電子書,比如,社科文獻出版社的皮書數據庫,商務印書館的在線工具書,科學出版社的科學e書房, 法律出版社的在線電子書業務,等等。雖然多數平臺仍處于起步階段,在信息服務的深化、模式的完善以及產品的推廣等方面有諸多不足,我國內容商為主體的專業性平臺畢竟邁出了第一步。
對于仍在觀望的出版社,尤其是中小出版社,一方面,要明確自身數字出版戰略的方向,擺明與現有大平臺的關系,切忌在數字出版上過于依賴大平臺。應該講,由于目前的大平臺競爭,內容方的授權沒有排他性的限制,所以出版社的內容往往可以同時出現于多個平臺,這是很好的風險分散策略,但是,更好的風險規避策略是使用不同類別的平臺和立足差異化的市場。另一方面,要克服自建平臺的畏難情緒,敢于適當投入。其實,出版社自建平臺遠遠沒有想象的那么難。很多出版社都有自己的網站,也有運營隊伍。立足于出版社網站,結合本社的出版特色,不失為一條轉向專業內容網站的捷徑。
對于以出版集團為單位上馬的數字平臺,應該對電子商務模式的局限有清醒認識,對于大平臺的潛在風險更要提高警惕。電子商務模式看似簡單,看似直觀,看似容易操作,其實是門檻最高、風險最大、也可能最不適合于數字出版的模式。而且,中國現在不缺“大而全”的大平臺,缺的是特色鮮明、定位清晰、用戶細分的平臺。出版集團往往投入巨大的資金、人力和技術資源建立平臺,這時一定要避免政績工程思維,避免重復建設。在定位方面要有別于現有的各種大平臺,要努力跳出大平臺的紅海,去追尋差異化的藍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