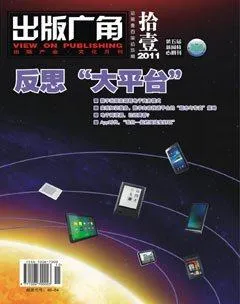論近代報刊的整理與出版
[摘要]無論是收藏界還是學術界,對近代(指19世紀初至1949年)出版的報紙與雜志都越來越重視。學界的重視帶動了出版界對這些近代報刊出版工作的空前的重視與投入,由此產生了一大批規模大、分量重的出版物,這反過來推動了相關研究的發展。但是,在取得可喜成績的同時,近代報刊的整理和出版工作還有一些值得思考和改進的地方,本文試對相關出版情況做一簡單的梳理,并略談個人淺見。
[關鍵詞]近代報刊 整理 出版
一、近代報刊簡況
清末,隨著西方印刷技術和傳播思想的傳入,真正意義上的大眾化報刊開始蓬勃發展起來。1822年9月,由葡萄牙人主辦的葡文報紙《蜜蜂華報》(A Abelha da China)在澳門創刊,“該報以鼓吹立憲派的主張為宗旨……是中國境內出版的最早的近代化報紙” [1]。在當時的辦報群體中,外國來華傳教士是主流。這些傳教士創辦的報刊“不僅對基督教在華人中的傳播,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而且對中國近代報刊的發展極具意義” [2]。方漢奇先生的《中國近代報刊史》說:“到19世紀末,外國人在中國一共創辦了近200種中、外文報刊,占當時我國報刊總數的80%以上。”[3]如果方先生的這個統計數字無誤的話,那么,到19世紀末我國境內出版的近代報刊總數當在250種左右。這些報刊中有許多是開報刊業之先河的,在中國報刊史上占有較重要的地位。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廣州紀錄報》(The Canton Register,英文報)、《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英文報)、《萬國公報》(1868,初名《中國教會新報》,后為擴大銷量更名《萬國公報》,后維新派辦的第一份報紙也襲用其名)等。自1895年康有為創辦《萬國公報》開始,維新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創辦了一系列有較大影響的報刊。
20世紀初的十幾年,我國出版的報刊量激增。《中國近代報刊名錄》(史和、姚福申、葉翠娣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書收錄了1815年至1911年間出版的中文報刊1753種、外文報刊136種,當然這中間包括了一些境外出版的報刊。由于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等重量級出版社加入了期刊編輯和發行的隊伍,使得報刊文化更具特色。“近代中國出版文化的特色之一,是‘書店期刊’的盛行。具體地說,就是書店于出版圖書之外,還定期印雜志。”[4]
到了20世紀20年代,報刊又經歷了一次爆炸式的增長。據平保興先生的統計,僅“1921—1922年間,我國出版了780種報刊” [5],這是指當年還在運作發行的報刊。這一時期的報刊出版有兩個鮮明的特色:一是共產主義理論和革命元素大量涌現,二是女性期刊的大量出現。
20世紀30年代,報刊出版整體質量和數量依舊比較高,僅1935—1936年間全國報刊總數就達1458種[6]。但受戰爭和物價因數的影響,許多期刊旋起旋滅,存續時間相當短暫,這是這一階段的一個顯著特征。40年代的報刊總體的量呈下降趨勢,1944—1945年間出版報刊數量為1028種(未包括解放區的報刊)[7],這恐怕依然是因為戰爭因素在起作用。
在1981年出版的《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1833—1949)》中,收錄了全國50家圖書館1957年以前所藏的中文期刊近兩萬種,如果加上失收部分和外文部分,光是近代期刊的種類就超過了兩萬種,對學界來說,這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二、近代報刊的整理與出版
從解放到現在,全國許多出版單位都對近代報刊的整理和出版工作非常重視,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取得了較好的成績。總的來說,這一方面的工作大致可分為如下四個階段:
1.初始階段(1949—1966)
其實,這一階段的前5年,出版業和全國其他的各行各業一樣,百廢待興,因此,尚未關注近代期刊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以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為代表的出版單位整理、影印了一批民國時期的報刊。比如,人民出版社在1954年到1956年間影印了《新青年》《每周評論》《政治周報》《解放日報(延安)》《中國工人》等刊物。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上海文藝出版社影印了一批文藝類的民國刊物,如《巴爾底山》《正路》《萌芽月刊》《文學新地》《文化月報》《時代文藝》《海風周報》《新流月報》《新興文化》等。
此時,幾份重要的報紙也被整理、出版了,如北京圖書館影印了《人民日報》(中共晉冀魯豫邊區中央局機關報,1946年創刊,1948年停刊)、《東北日報》《新華日報》(1938—1947),中華書局在1965年影印了《湘報》。
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解放》《共產黨》《共產黨人》《中國農民》《中國青年》《中國文化》等。
由上我們可以看出,這一階段出版單位關注的目標主要是共產黨以及左聯、創造社、太陽社等進步文學團體主編的一些重要報刊。
2.停頓階段(1967—1979)
受“文革”這一大環境的影響,這一階段對近代報刊的整理、出版工作處于停頓狀態,未出版任何此類刊物。
3.復興階段(1980—2000)
20世紀80年代初,人民出版社又重新啟動了“文革”前的對民國報刊的影印整理活動。其時,該社又影印了《北京大學日刊》《晨報副鐫》《晨鐘》《大公報》《建設》《救國時報》《熱血日報》《漢口民國日報》《少年中國》等刊物。
這個時候,上海書店(原上海古舊書店)作為一支新生的力量,在民國報刊整理、出版領域異軍突起,也出版了一大批此類報刊。比如,《申報自由談》《生活教育》《生活日報》《月月小說》《新小說》《繡像小說》《新新小說》《小說林》《筆談》《太白》等。
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廣東人民出版社等單位的加入,一批規模較大的報紙如《華商報》《盛京時報》《申報》《晉察冀日報》等先后被影印出版。
到了90年代,中華書局陸續推出了《中國近代期刊匯刊》系列圖書。這套書收錄了《清議報》《強學報》《時務報》《昌言報》等19世紀末有著較大影響的由維新派等創辦的近代報刊。進入21世紀后,中華書局又陸續推出了該套叢書的第二輯,收錄了《國風報》《民報》《湘報》《譯書公會報》等近代報刊。90年代中期,江蘇古籍出版社和上海書店出版社聯手出版了大型報刊《中央日報》。
4.鼎盛階段(2001—)
進入新世紀以后,近代報刊的整理工作進入鼎盛階段,這具體表現為參加單位的數量進一步加大,圖書的選題也更加系統和深入。20世紀的整理工作以期刊的單品種影印為主,而進入21世紀后出現了許多以題材為單位的匯集多種期刊的大型叢書,如《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民國國術期刊文獻集成》《晚清珍稀期刊匯編》《民國時期集郵期刊匯粹》《民國新聞期刊匯編》《民國畫報匯編》《胡風主編期刊匯輯》《中國近代中醫藥期刊匯編》等。一般來說,這些叢書的規模較大、內容系統而全面,雖然它們中有的讀者面較窄,但對使用者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
三、對近代報刊整理、出版現狀之思考
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版界通過這些努力為學界提供了豐富的原始材料,推動了學術的發展。綜觀近代報刊的出版現狀,我認為有幾個問題值得出版界、圖書館界和學界進一步關注:
1.出版力量不均衡。有的品種反復出版,如《海潮音》有多家出版單位進行了影印,這固然是因為它比較重要,但在客觀上也造成了出版資源的浪費,與此同時有一些十分重要的在中國境內出版的外文期刊卻少人關注。
2.人名、篇名索引等配套工具的編制比較滯后。在文獻的量非常龐大時候,這無疑影響了已出版圖書的利用。
3.由于有些報刊的總量非常大,因此造成了出版物定價高昂,影響了出版物的銷售和推廣。有些報刊是綜合類的,某些特定科研單位也許只對其中部分文章感興趣,如果其所占比例過小,使得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也會影響銷售。解決這一問題的較好辦法是將同一期刊或不同期刊的同類內容輯出,單獨出版。這樣做既可以降低成本與定價,又細分了市場,擴大了銷售面。比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匯編》系列,該系列包括《東方雜志學術類編》《經史關系》《敦煌學研究》《春秋學研究》《三禮研究》等。
4.相關數據庫的建設。目前,與近代報刊相關的且較有影響的數據庫有國家圖書館的《民國時期文獻專題資源庫》(讀者可以通過該資源庫查閱民國期刊4350余種)、上海圖書館的《民國時期期刊篇名數據庫》、重慶圖書館的《清末民初報刊篇名索引》等。這些數據庫容量都比較大,但是可以根據現在陸續出版的近代報刊對之進行完善。
(作者單位:上海辭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