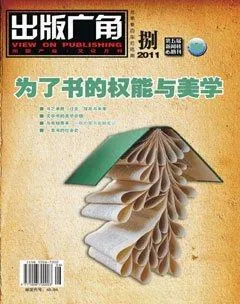梅光迪和民國的學人社會
作為學衡派最早的創始人梅光迪,在當下學衡派名聲日隆之時,其名卻隱而不彰,顯然與他著述傳世不多有關。與民國同時代學人相比,梅光迪本身就“述而不作”,惜墨如金,著述相對較少。同時散見于各報章雜志,搜求不易。也由于受到政治氣候的影響,梅光迪和學衡派都被列入“地主階級文學”代理人的行列,其人其文更是湮滅不聞。人們對于梅光迪的了解和研究,受阻于與梅光迪相關的文獻、尤其是他本人的著述相對稀見。
因此作為學衡派的研究者,當筆者讀完由梅鐵山、梅杰二位梅氏后人為其家族先賢梅光迪最新編輯而成的《梅光迪文存》時,感到由衷的寬慰和欣喜。毫無疑問,這是目前為止,收錄梅光迪著述最全的一本文集。這為梅光迪個人的研究、學衡派的研究以及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又增加了很有分量的新材料。
學衡派本身就是一個學人社會。關于梅光迪和學衡派的關系,各種資料明白無誤地顯示梅光迪是學衡派最早的發起人。但是從1923年起,也就是《學衡》雜志僅創刊兩年不到,梅光迪就再也沒有給《學衡》寫過文章,他曾對他人表示:《學衡》雜志辦得不好,與他本人再無關系。似至這一時期,梅光迪與學衡派已經不再有任何瓜葛。對于這一樁公案的來龍去脈及其原因,一直以來眾說紛紜。在仔細閱讀《梅光迪文存》之后,就會發現:第一,梅光迪與學衡派之間,無論從思想上、情感上還是個人交誼上,從來沒有中斷過聯系。1932年,在學衡派最為重要的組織者劉伯明去世九周年之際,梅光迪撰文沉痛悼念,表達了梅劉之間,其實也是與學衡同仁之間深沉的感情。1938年,梅光迪聘請學衡派的老朋友柳詒徵來浙江大學任教。梅對柳的評價極高,認為柳詒徵與馬一浮“他們兩個的組合或可周知有關中學和中國文化的知識,目前在中國還沒有第三個人可以和他們相比。”第二,我們可以從本書中發現梅光迪與《學衡》雜志分手的重要原因,他認為《學衡》“只模糊而狹獈地局限在一些僅供學術界閑時談論的文哲問題上”,對于新人文主義的傳播缺乏更具高度的理念和好的手段,“缺乏必要的標語和戰斗口號”。
胡適與梅光迪的交誼一直是人們感興趣的話題。他們二人從好友變成文化思想上的“對頭”,這既是二人之間私人的情感糾葛,同時又超越了私人關系,成為影響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重大事件。《梅光迪文存》收錄梅光迪致胡適書信46通以及相關短文一則,可以令我們對二人的關系有更深入的了解。這些文字清晰地反映了二人關系的演變:從未識之前相互仰慕到初識一見如故,再到主張對立,發動形同水火的論戰。值得指出的是,雖然雙方的文化主張勢同冰炭,但梅光迪仍然珍視與胡適的友誼,收到胡適的信,他回信說“讀了很快樂”。他也并非對胡適“全盤否定”,胡適創辦《努力周報》,梅光迪即致信表示:“《努力周報》所刊政治主張及其他言論,多合弟意,兄談政治,不趨極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于社會”。文存還收有梅光迪向胡適借錢的書信,足見梅氏仍然視胡適為“自己人”。
《梅光迪文存》還為我們解讀馬一浮任教浙江大學一事提供了一些有參考價值的細節。馬一浮在當時已經在學界負有盛名,但他拒絕任教于任何新式大學,包括蔡元培與蔣介石的邀請,也予以拒絕。但抗戰初期,他卻就教于浙江大學。個中原因,歷來說法不一。梅光迪作為禮聘馬一浮的當事人,他在書信當中披露的一些細節,或許有助于我們了解事情的真相。馬一浮來浙江大學,并不是因為高薪吸引,實際上馬一浮薪水并不高,“每個月300塊錢”。最關鍵在于“我們以古代對待大師的標準對待他”,“他不會像其他教授那樣講課,而是一周兩到三次公開對全校師生開講座。另外,他還單獨給一些資質很高的學生做單獨指導,這些學生一周去他的住處一到兩次”。梅光迪還專門制定了馬一浮開講座時學生必須遵守的禮節。馬一浮拒絕前往新式大學任教,是他一直認為這種方式有失師道尊嚴,“古聞來學,未聞往教”。而浙江大學“以古代對待大師的標準對待他”,實際上在馬一浮身上,恢復了古代書院的師生關系與授課制度,深刻地體現了老師的尊嚴,這深合馬一浮的書院理想,才前往就教。可以想見,馬一浮能去浙大任教,與梅光迪的舉薦與奔忙也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