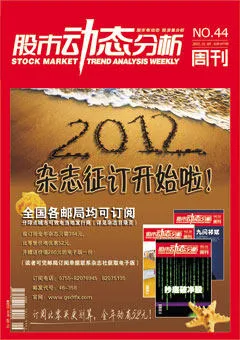洋和尚不諳A股情商的經
上期本欄將看A股今年大勢失準的國際投資界大佬一一羅列了一遍。這里筆者以為有必要說明:此舉絲毫不代表對這些大師級人物有任何不屑與不敬,更不意味筆者據此自鳴得意或竟自以為比大師們還要高明。正如西諺有云“盡管鷹有時飛得比雞還低,但雞永遠飛不了鷹那么高。”對于年輕的中國投資界來說,大師們所取得的成就永遠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對象,是需要自己付出終身努力的奮斗目標。
至于為何他們在預測A股走勢時栽了跟斗,依筆者之見并沒有什么特別費解之處。首先,這些預測大部分是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順口而出的隨機之答,更多地是出于他們平時的觀感,而非專門進行研究后的結論——他們投資的主要方向畢竟不在A股而在其它標的。而實際上,他們對于中國經濟的了解還遠未到深刻的程度。更何況A股的一個明顯特性是向來與宏觀經濟運行鬧獨立,你把歐美行之有效的經驗邏輯搬過來測度A股的運行程序不管用。
還有一點是他們絕對忽略了或沒有考慮到的,就是A股市場高速擴容給大盤帶來的巨大壓力。我們不妨試著假設一下,如若沒有IPO與增發,曹仁超先生所預測的“2011年上證指數的低點在2800點以下、2500點以上,上阻力在3200點以上、3500點以下”或許有可能應驗。即使有出入,大概亦差之不遠……遺憾的是股市永遠沒有如果。
我們還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作出深一層的補充解釋:人的預測能力,很大程度是基于一種前瞻性記憶現象。在既往的實踐活動中,人們會將自身的經歷感受存儲于大腦中,并形成經驗。當以后再遇到類似的生活場景時,記憶中的經驗或印象將會被“喚醒”并形成判斷,從而產生預測。我們可以相信:存儲于上述那些境外大師腦中的經驗記憶肯定是國外市場的,而不會是A股的。突然這些經驗記憶因其具有某種普遍性或許會適用A股,但始終隔著一層。再說運用起來要使二者完全契合也需要一個過程。這樣在研判A股走向時出現看錯病或下錯方的情況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哪怕接診的是聲名顯赫、經驗老道的洋華陀。
中國的證券分析分析完全是從零起步的。早期從事這個行當的人都得靠自己摸索。故筆者自涉足股評以來一直非常重視海外的著名分析師是怎樣評論滬深A股走勢的,抱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心態以求學得兩招。最早是從香港的波浪大師許沂光開始,然后是某某大師、某某股神這個那個的先后關注了大約有十來二十位,可以說是把歐美凡有些名氣的都搜羅過了。若問我跟蹤近廿年的感覺——說出來大家可別不信:我的結論是遠來的洋和尚念不好經,預測A股大多不靠譜,甚至南其轅而北其轍!當然也不能一竹竿打了一船人,說對了的總是有的。但按概率算也應該有了,這就難說有多大參考意義與價值了。這樣慢慢地時間一長,再遇到媒體上的轉發某某國際大師說A股將如何如何,我看還是看,但不會再太當回事放在心上。原因是不再迷信,覺得外人大多水土不服,最了解中國股市的還是中國人自己。也正因此我對國內各大證券機構(當然包括基金)競相用高薪聘請“海歸”任高管或操盤手、以是否有留洋經歷或學位作為任職的標準嘖有煩言,認為浪費錢財,是個絕大的錯誤!實際上,選用土生土長、有多年實踐經驗的“土鱉”可能更稱職,且性價比也更理想得多。
上述錯誤之所以產生并大行其道,緣自過分強調智商在股市中的作用、而漠視情商對于股市博弈的影響是密切相關的。人有人性,股有股性。一個國家股市的“性格”——即其運行的特征、節奏與規律,是由該國的民族心理所培養的證券文化環境所決定的。若非長期地浸淫于該國的證券市場,并在其中摸滾爬打三到五年乃至八年十年,是談不上對于這個特殊的對象有透徹的了解的。股諺說選股如選妻、炒股如談情,惟有長相廝守、耳鬢廝磨,才能如摸透愛侶的喜怒哀樂一樣洞悉股市的性格,才能保證如同在情場一樣在股市的博弈中立于不敗之地。須知在股市中,情商和智商一樣重要,有些時候甚至可能更重要。因為智商有利于你認識經濟,情商還能助你進一步認識股市的本質特性與博弈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