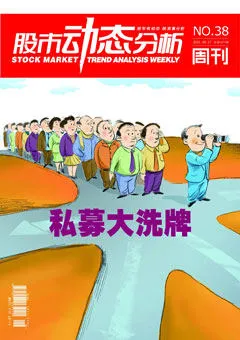三年之后
有人問我對四季度市場的看法,因為對方說只是為了了解投資人的看法,并非征求投資意見,我便不痛不癢的說了兩句。完了,他給我做了一道題目: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性,十分整潔,喜歡做事有條不紊,井井有序,他最可能的職業是什么? A 農民;B 圖書管理員;C 醫生;D 律師。
我說是醫生。他說不對,答案是農民。解釋道,中國有9億農民,而其他職業不過幾千萬人,從概率來說,農民的可能性最大。結論便是:人要做出很理性的判斷是很難的,都會被習慣性左右。大意是我對市場的看法也并非理性。
這我絕對承認。每個人對于市場的判斷基于自己的教育背景、思考模式、乃至生活圈子,你無法在金融圈問一圈后,就判斷出普通的投資人到底對市場是悲觀還是樂觀,或者投資人的平均倉位是多少。何況他這道題目,其實有誤導的成分,如果問題是“在中國有位三十歲的男性,十分整潔,做事有條不紊,那么他最大概率是什么職業?”那么或許我真的會純從概率角度考慮,而之前的問題模式下,我的理解是,“一位農民、一位圖書管理員、一位醫生和一位律師之中,他最可能是哪一位”?備選的樣本不同,答案便會完全不同。
有人在參加過一次投資圈的俱樂部活動后,便放棄了,因為大家發表觀點都有所保留,真真假假,難以分辨。但就算是理想狀態下,均開誠布公,說出自己的真實觀點呢?所謂的“自我實現預言”又會實現,因為每個人行為匯總后,不可避免又對市場產生影響——尤其是這些手中還有一定話語權的人們。
所以市場總是很難有什么確定的定量,可以作為充分條件以判斷市場走向。市場總是在變化,昨天發表的觀點今天就會失效,更正觀點惹得外界對自己信心喪失,不如裝聾作啞或者干脆死咬到底。
歐洲的問題并非沒有被預料到,只是似乎比預期的嚴重。好笑的是,不知道什么時候,中國成了金主,統統來找中國伸手要錢。不得不說,即便是這些整天在街上游行抗議加稅延長退休期或是領取退休金過活的歐美人,怕是比中國不知多少地方的老百姓有保障的多。舒服日子慣了,讓他們節衣縮食實在很難。只可憐中國納稅人的錢,希望不會被一次又一次的亂揮霍。
不過歐洲的問題再嚴重,也有兜底的,就是德國。等到德國受不了了,宣布免除債務提供援助等等,這波鬧騰也就暫告段落。
國內的問題目前還看資金面。據說現在連銀行的短期理財產品都賣不動了,而半年前,常常是一搶而空;甚至有傳言說,銀行愿意接受高利貸的資金,令人咋舌。至于民間的高利貸更是普遍,連我老家所在的小城市并非沿海一類商貿城市都十分盛行,令人不免擔心:要么某一環節資金鏈斷裂,引起大震蕩,要么政府趕緊令行禁止,懸崖勒馬。
中小銀行剛剛上繳了700億資金,這流動性的河水也干得差不多了,弄成大旱的狀況怕也不是政府本意。政府也發表觀點:近來災害連連,說明我們的基礎建設還很薄弱,所以在這些方面還要有很多投入。這便是典型的對沖手段:畢竟不能依靠樓市來拉動經濟,其他方面還是不能少。水利、軍工都是重頭。
還有放出資金的方面,可能便是樓市,中心城區之外的樓盤率先降價,媒體已直稱“拐點”到來。如果房價下滑(當然不會太大),相應反而會有大量的資金出逃,成為“熱錢”的主要來源。
投資品和消費品在投資人眼中最大的不同便是,前者是越跌越不買,而后者是越跌越搶,就像年終大促銷一樣。因為后者買到的是當下享受,立即可評判;而前者買的是未來預期,既然是預期,若是產生變化,心理上的痛苦甚巨,又無法獲得彌補,自然令人望而卻步。當然不是說要逆勢而為,但在下跌之中,千萬別閉上眼睛。
不知不覺,雷曼兄弟倒閉已經三年。堅持過三年,怎可在此時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