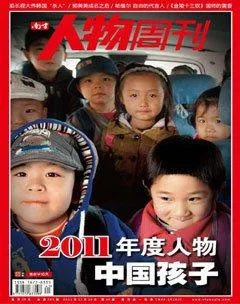【變】2011年的世界
2011-12-29 00:00:00趙靈敏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45期





2011年,國際上最激動人心、也最出乎意料的變化來自中東北非。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小販的自焚,似乎在一夜之間點燃了這一地區人們反抗暴政的星星之火。從埃及到敘利亞,從也門到巴林,人們紛紛走上街頭,要求那些掌權已久的專制統治者下臺。突尼斯的本?阿里總統明智地選擇了出走這種相對體面的下臺方式,也門總統薩利赫也最終簽署了下臺文件,而當國30年、年已83歲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被送上了被告席。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的結局則更富有戲劇性:在經歷了北約長達216天的轟炸和長達5個月的內戰后,他在家鄉蘇爾特的一個下水道里被捕,在凌辱和虐待后死去,尸體被放在冷庫里供民眾參觀。
在過去很長時間里,一種廣為流行的看法是,中東伊斯蘭國家很難走上民主化道路,民主在中東地區是一個例外,即所謂“中東例外論”。但過去一年這一地區的變化表明,民主和伊斯蘭是可以相容的。經此一役,中東國家體制中的民主因素無疑將大幅增加。而且,與“民主路線圖”等主要由統治者和外力推動和強加的民主不同,此次的變化是自下而上的。這代表了中東民主的社會基礎正日趨成熟。這也正是全世界為中東的變化歡欣鼓舞的原因。但是,舊制度可以在一夕之間被推翻,新制度的建立卻總是異常漫長,要生成與伊斯蘭傳統政治結合的具有中東特色的民主政治,遠非幾次街頭運動所能完成。埃及、利比亞當下的混亂,也正是源于此。
更讓人擔憂的是宗教勢力的乘勢而起。穆斯林兄弟會旗下的政黨在埃及下院選舉中獲勝,利比亞反對派決定用伊斯蘭法來統治國家,伊斯蘭政黨領袖擔任了摩洛哥的首相。這再一次因應了亨廷頓的著名論斷: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往往成為宗教勢力取代世俗勢力的過程。由于敘利亞和伊朗的危機還遠未解決,“阿拉伯之春”的最終走向,仍是一個未解之謎。
2011年,隨著希臘、愛爾蘭、葡萄牙主權債務危機的升溫,歐洲債務危機開始從歐元區外圍國家向核心國家蔓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法國都面臨了不同程度的債務風險。債務危機的擴大和蔓延,接連在歐洲引發“政壇地震”,不到一年的時間,先后有五國總理去職。多國開始為重印本國貨幣做準備,歐元解體的風險迫在眉睫。大難當前,在經歷了長時間的推諉、相互指責和無所作為之后,在12月初的歐盟峰會上,英國之外的歐盟全部26個成員國,包括歐元區17國和非歐元區9國,一致同意以政府間條約的形式締結一份新的財政契約,以強化財政紀律。
歐元危機根本上反映的是歐盟內部的文化差異:地中海沿岸各國注重生活享受,寧愿借債也要滿足生活享受;而德國代表的日爾曼語各國則強調勤奮和量入為出。而歐盟峰會上的決定,實際上就是將強調財政紀律的“德國模式”推廣到全歐洲。但英國的反對使得重修《里斯本條約》、強化財政違約懲罰機制的努力成為不可能。這次峰會被認為是“拯救歐元的最后機會”,但由于缺乏能立竿見影緩和歐債危機的舉措,市場的擔憂有增無減,歐元匯率繼續下跌。歐洲央行的官員已經表示,歐元區債務危機料仍將持續兩年的時間。
歐元的危機凸顯了美元作為國際避險貨幣的作用,資本大量回流美國使得美國成為這場危機的贏家。但這絲毫無助于美國國內政治經濟問題的解決。盡管促成了從伊拉克的撤軍、打死了恐怖分子拉登和奧拉基,但國內失業率的居高不下和黨爭的日益激烈使得奧巴馬的連任前景極不樂觀。7月底,民主共和兩黨圍繞著提高國債上限你來我往的“政治秀”,表明目前的黨爭達到了前所未見的激烈程度,反映了兩黨巨大的意識形態差異和美國政治深刻的兩極分化。美國政治是否會越來越極端化還有待觀察,但今年以來多家美國重量級媒體對美國貧富分化加劇、藍領中產階級塌陷和社會上升通道被阻塞現象的報道,卻讓人擔憂“美國夢”是否還能延續。而“占領華爾街”運動,在不到3個星期里,星火燎原,爆發成一個全美性的大規模民眾抗議活動,更是為美國當前的社會矛盾敲響了警鐘。
俄羅斯的“強人”普京也遇到了大麻煩。2011是他統治俄羅斯的第12個年頭,過去12年里,他一直在努力打造其作為俄羅斯國家“恩人”的形象:努力恢復昔日的帝國榮光、高油價帶來的經濟持續增長、養老金欠賬的償清、車臣戰爭,甚至他的強健體魄和精于體育運動也為他加分不少。今年9月,他剛剛決定明年要和總統梅德韋杰夫換位子,打算再當12年總統。很多俄羅斯人雖然感覺不舒服,但也無可奈何。俄羅斯人似乎和他達成了一個隱性的契約關系,即普京保證政治穩定、國際地位和生活水平提高,國民則自愿容忍威權統治。但沒過幾個月,他的好運就到了頭。12月4日的杜馬選舉,普京所在的統一俄羅斯黨雖然得票率為49.54%,但與2007年相比下降了14.76%,席位減少了77個。而選舉舞弊的傳言誘發了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最大規模的游行示威,人們公開要求普京下臺。盡管俄羅斯人對普京的需求還沒有消失,他應該還會在明年3月順利當選總統,但他需要更新統治方式,在民主和多元的基礎上和人民達成新的契約。
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也遭到了重創。3月11日發生在東部的9級地震引發了海嘯和核泄漏,更導致了菅直人政權的垮臺。野田佳彥在9月2日成為日本戰后第95任首相,也是近5年來的第6位,“無領導力的日本”由此可見一斑。而日本經濟自1990年代泡沫爆破后至今一沉不起,已經經歷兩個“迷失10年”,金融危機則打擊了日本的出口,目前日本的國債占GDP200%。在這種混亂不堪的情況下,地震無疑是雪上加霜。“地震會否令日本淪為二流國家”成為了全球經濟學家的熱議話題。
全球性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則導致了各國內部社會分化的加劇,發生在挪威和比利時的槍擊案以及發生在英國的下層社會無政府暴力騷亂,都是這種社會分化的產物。可以說,今天的世界是一個空前不確定的世界。全球化把各國聯系在一起,任何地方的問題都具有全球性的意義,但糟糕的是,目前幾乎所有的關鍵點都有問題。而在2012年,中、美、俄、法、印等國都將進行領導層的更迭,來年,我們恐將面對一個更為不確定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