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昌平 讓易碎的新聞不碎
2011-12-29 00:00:00劉玨欣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1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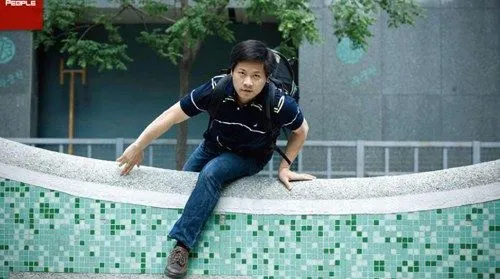
雜志擺進報刊亭,一下子就被人包圓兒了。補上貨,又被包圓兒了。“我們開始還以為是賣得好,這時候才知道要提防一下。”羅昌平說。
5月11日中午,羅昌平發了一條微博:“《財經》雜志在北京中關村、西直門等地遭惡意清攤,多次補刊無濟于事,后發現系《隱莊肖時慶》一文報道證監會前官員受賄1546萬元、內幕交易獲利約1億元,牽涉到六家上市公司,相關公司安排人在報刊亭大舉清購。”
同行朋友們不怒反樂:“還有人收購你們玩,羨慕死。”后來講起,羅昌平也樂,“好多年都沒發生這樣的事了,這手段好笨啊!”
不是每次都能把麻煩轉成樂子。去年《再問央視大火》發表后,有人撥通羅昌平家極少對外公開號碼、用他人名字登記的座機,惡狠狠地威脅:“在這個事情上你再說話,我們做死你,你已經斷了我們的財路,小心你的命。”
老板給羅昌平分析:你抓的不算七寸,雖然很影響他們生意,也沒完全毀掉他。結論是:保持低調,對方不至于鬧到魚死網破。
這位《財經》雜志副主編在微博的加V認證里沒提單位名稱和自己職位,只稱調查記者,這是他最喜歡的稱謂。
入行10年,羅昌平的調查報道涵蓋社會、時政、法治與經濟各領域,4次獲得過南方周末年度致敬。
他花5年時間寫成《遞罪——政商博弈的郴州樣本》一書,用自己的分析方式去記錄這個時代的一段歷史。他聽說中紀委最近有人訂走了200本,又聽說這本書被湖南、郴州兩級宣傳部集體采購,以為是封殺,卻看到一則新聞:郴州市某區人事局強化廉政知識學習,引導干部職工利用業余時間閱讀《遞罪》,組織觀看反腐警示片,及時打好防腐預防針——他有些啼笑皆非。
調查記者的調查經
“最近10年內的重大公共事件、重大案件、社會或政治層面上的人物,心里頭都要有底。有點兒像美國寫那個逝者,前段時間伊麗莎白?泰勒去世,《紐約時報》給她寫悼詞的,自己先去世了。文末注明此文作者已于什么時候去世。其實這和我們是一樣的,資料備份很早就開始了。”羅昌平在照片上像他的新聞一樣硬朗,但坐下來看,他笑容溫和,甚至有些娃娃臉。
同為調查記者的孔璞記得,剛入行時,她四處托人幫投簡歷,只有羅昌平不僅幫Zuvw/1LXK2lUtDJCvhflxg==投簡歷,還親自帶她上門面試。做第一篇稿,陷入困境,羅昌平又發來通訊錄,都是相關專業人士的聯系方式。“我朋友看了說,這都是記者吃飯的家伙,他都給出來了。”孔璞至今感激。
“我只是選擇最有效率的方式做事吧,投簡歷不如見面。至于通訊錄,我一直都是與人共享,這樣別人才能與你共享。”羅昌平對感激有點兒不好意思。
羅昌平手上經常同時做著兩三個題目。他采訪不大喜歡用錄音筆,要求證據能落到書證上,而不是口證。
采訪、研究、寫作是記者的三項基本功,其中研究是調查記者最應重視的功課。“我們報道一件事,至少要看5到10萬字的文字材料。比如《公共裙帶》,從2007年開始做到現在,算4年了。文章最后有句話,李薇和她的妹妹在2005年辦了暫住證,在2009年又第二次辦了暫住證。雖然這個東西很簡單,但不是人家提供給你的,得通過特殊渠道查詢。她所有關聯人的這些事,戶籍資料、工商檔案、信用記錄、土地交易等,全是通過全國各地不同領域的朋友幫我查的。”
那些看起來很難接近的調查,得靠人脈和內幕嗎?
羅昌平搖頭:“這個時代‘深喉’太少。公檢法、紀委能提供的非常少。只能靠自己的堅持。自己做題時,每周很抽時間去檢索每個關鍵詞,現在編記者的稿子,也一定會逐一搜索文章中的關鍵詞。先是普通的搜索引擎,可能還拓展到警方的戶籍搜索、央行信用系統、工商系統等。不斷地變換關鍵詞去搜,一般看十幾頁,或者更多。也許現在你搜不出來,可能過過半年就能搜出來。經常要不惜成本,比如特別重大的稿子,工商資料查詢就可以達到上萬元錢,交律師費和打印費了。”
急性子的他,做調查卻有足夠的耐心。他收集敏感案件的判決書,有的在宣判時幾乎不可能拿到,但一兩年后拿,就容易得多。“判決書里會有大量的細節是你以前不能掌握的。”
去年10月,他安排記者做《高官貪腐錄》,收集120個省部級官員的大名單,手里有其中近三十人的判決書。“用了半年時間,詳細統計120人的年齡構成、判刑情況、集中的領域、案發的時間等,從中尋找規律與邏輯。我們很重視分析方法,會邀請經濟學與法學的資深專家提供幫助。”
“不止是判決書,一切司法材料,甚至黨報材料,都可能是有用的。比如去年的安元鼎,南方都市報的龍志從公開資料找到了某一個縣,跟安元鼎簽訂了合同,作為政績在網上公開了。這就需要你不斷換詞去搜索。”
微博時代的傳播,讓羅昌平欣喜也擔憂。“想想我這10年路,當年還是比較清靜一點,會扎實做自己的東西。微博會讓更多調查記者浮躁,甚至一些優秀的調查記者已轉型為社運記者。現在還有幾個人,踏踏實實做一個新聞。比如說樂清事件,誰能在那真正呆3個月?”
第一份檢討
羅昌平清楚記得,闖到北京那天,2001年7月14日,是北京申奧成功第二天。他20歲,辭掉了湖南省電力廳一家專業電力雜志的穩定工作。什么也沒找好,就奔了過來。
初中畢業時,他遵循在水電站工作的父親的意見,以692分的拔尖成績(總分730分)考進水力系統的中專,學水利工程建筑專業,準備回家工作。那是畢業包分配的最后一年。
學校里,羅昌平是校報主編和廣播站站長,管理著二三十人。4個版的報紙,排版時要先剪下文章,貼在紙上,再翻印出來,發給三四千名學生。
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有學生沖去控制了校廣播站,播放國歌,引得群情激昂,全校學生開始游行。羅昌平第一次感到,原來傳播的力量這么大。
因為沒守好廣播站,羅昌平被勒令寫檢討。“那是我這輩子寫的第一份檢討。后來主管新聞,寫檢討成了常事。”
離開長沙闖北京時,父母連夜趕來相送,更想勸他留下來。“但我就是覺得年輕,應該要闖一闖。”羅昌平說。
北京廣安門的報國寺里,樹木蒼翠,大殿儼然,還有戊戌變法參與者曾住在里面的紀念碑。羅昌平進了這里的《中國商報》,當時它正從日報轉為周報。
羅昌平從來沒有接受過新聞專業訓練。他沒事就鉆報國寺的兩個側殿——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報刊資料室,研究全國的報刊資料,比如《南方周末》和《財經》,模仿他們寫作。
雖然遺憾于沒人指導,但也樂于沒有人管束。在《中國商報》的3年,他幾乎跑遍全國。“不是根據新聞走,而是根據自己愛好。想去哪兒,就去附近找一些很古怪的題做。很隨意的,坐火車可能半路就下了。或者在某個小城,有意思就多住一天。常常延著一條線,去找兩三個題。有時候就在網吧里寫,會發現旁邊都是玩游戲的。我就想,自己要是戰地記者,一樣能發回稿件。”
3年的游歷和讀書,就是他的大學。
他至今記得在《中國商報》的第一篇稿子——《為什么自己的首都我們只能暫住?》,八千多字。“前段時間我把這篇文章找出來,覺得現在重新發表一遍,也還非常合適,情況還是沒有變,甚至更難。當年我們進北京的門檻是比較低的,住、吃、入行門檻……拿到今天來比較,已經完全不可能了。如果我10年后再走一遍,可能就闖不出來。”
讓新聞不碎
2004年2月,羅昌平到《新京報》做深度報道。第一篇稿子,關于取消農業稅,寫一半,編輯不滿意,拿出紙筆劃井字。說橫向要采訪農委、稅務、財政、政府辦公室4個,縱向要采訪市級、區縣級、鄉鎮級、村級、個人5個。4乘以5就是20。你要采訪20個點。“我一輩子都記得清楚。”羅昌平在桌上重復劃著井字說:“這幾乎影響我現在所有調查的邏輯,做完那個,我豁然開朗。”
2006年5月,他已經是《新京報》深度報道部主編。因為《“雙規”再次收權》系列報道,既是作者、又是編輯、還是分管部門主編的他,不得不離開。
他可以選擇去薪水較高的互聯網,但猶豫了一下,覺得那不是自己想要的,就去了《財經》雜志,又成了普通記者。“上到某一個位置,再下去還是蠻費勁的。”何況薪水只剩當主編時的一半。
每次最不高興的時候,他就回家,像充電一樣,回來就精神飽滿了。“做這行,失望失落的時候,其實很多。”他讀過的學校已經被拆遷了,他跟人開玩笑說“回家的路上他們拆了我所有的記憶”。微博和MSN的頭像,他用《天堂電影院》中的小男孩多多,“影片中的故事與我們的經歷很像。”2008年,他給父母蓋了漂亮的房子,一畝地,水直接從山里接下來。還好,他覺得自己仍有可以回去的故鄉。
2010年,他出版了《遞罪》一書,用5年時間研究郴州官場腐敗系列窩案,提出“遞罪原則”,即“一旦第一個環節存在違法行政的錯誤,之后的任何一個環節將自動采取制度性護短,于是公權力針對公民權的侵權劣舉將在連環謊言的包裝與護衛下得以順利實施,由此無限度地侵害弱者。”
他希望記者能用自己的一種分析方式去記錄某個歷史片段。“新聞是易碎品,而好的記者一生的追求,正是讓新聞不碎。”胡舒立在《遞罪》的序中。
羅昌平答《南方人物周刊》問
人物周刊:你對自己的現狀滿意嗎?
羅昌平:生活指數滿意,新聞卻在谷底。
人物周刊:對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與他人分享?
羅昌平:成就?哈哈,現在遠遠談不上成就。新聞是易碎品,既要影響現在,又能記錄歷史。就必須堅持做下去,一條道走到黑。我不是聰明人,但有笨辦法,做最喜歡的事情,會投入別人數倍甚至十倍的努力,僅此而已。
人物周刊:對你父母和他們成長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們嗎?
羅昌平:我的父母生活在最底層,他們承擔了那個時代最大的苦難,卻給了我足夠的自由與獨立的可能;他們很窮,卻給了我最大的財富——能吃苦、不作惡。過去31年里,我一半時間與他們度過,一半時間在外飄泊,距離感加重了牽掛。我們最大的理解是彼此包容。
人物周刊:你對這個時代有什么話不吐不快?
羅昌平:講真話。
人物周刊:你對你所從事領域的前景怎么看?
羅昌平:這個時代太急功近利了,這個行業太急躁無常了,專業化程度遠遠不夠。在不少同行看來,新聞是一個沒有前途的領域,但如果不做,我們生存的環境、面對的系統將會更沒前途。改變不僅需要圍觀,還需要表達和參與。所以我會盡力堅持,并影響更年輕的一批人堅持。
人物周刊:你覺得你的同齡人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羅昌平:不管愿不愿意,我們這代人已被推到了歷史的舞臺。理想在墮落,市場在興起,無法獨立的生活與無法獨立的思考、人格并存。
我試圖用“末法的一代”來描繪同齡人。這代人正在呈現一種衰微之勢,一種前所未有的無力感,有價值上的分裂,有對歷史和文化的淡漠,又缺失情懷與常識,在飛速而碎片的流水作業中失去了方向。但是,低谷或許暗含著新生,因為我們少了歷史負擔,更容易與現代文明接軌。
人物周刊:你認為什么樣的人稱得上是有“領袖氣質”?如果一定要你選,你的同齡人中夠得上青年領袖的還有誰?
羅昌平:在《魔鬼詞典》里,領袖被戲稱為“衣服最容易臟的地方”。其實我挺怕“領袖”這個詞的。在這個時代,還是盡可能去掉個人色彩,回歸到事件本質更好。現在假的東西太多了。
人物周刊:責任和個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個?
羅昌平:個人自由,但總在為擔當而犧牲自由。
人物周刊:對你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或者一部電影?
羅昌平:沒有。不斷看,不斷完整。
人物周刊:你幸福嗎? 有沒有什么不安? 你現在最大的擔憂是什么?
羅昌平:幸福是比較級的,有奮斗的方向與可以回去的故鄉,就是最大的幸福。還好這兩點都有。
做這一行,不穩定影響肯定存在。發表《再問央視大火》時,收到過死亡威脅;簽發《安元鼎專職截訪》,受到過強權干擾;《公共裙帶》也承受了不同層面的壓力,好在可以堅持。不安來自內心,而非外力,比如感到時間不夠、知識短板、眼界受限等。
身為80后,他已成長為社會調查新聞的實踐者和推動者。他的正義感和責任感,使他在這個傳媒日益浮躁化的背景下,能堅守住新聞專業主義,“三問央視大火”、《郴州樣本》等作品,像一把尖銳的手術刀,把這個社會的毒瘤曝露在陽光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