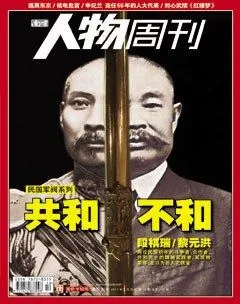臺灣“核四廠”背后的政治惡斗
從前面三座核電站一路順風(fēng),一路開綠燈,到“核四廠”延宕多年,遲而不決,決而不議,議而不建,建而不成,這冗長過程正刻劃著臺灣擺蕩于環(huán)保與經(jīng)建兩端,不知如何抉擇是好的萬般無奈窘境
上世紀80年代,美國三哩島核電站、蘇聯(lián)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兩次大規(guī)模核事故陸續(xù)發(fā)生。在臺灣島內(nèi),具有高度環(huán)保意識的知識分子莫不談核色變,把反對興建核電站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
遺憾的是,由于朝野政治勢力的強橫介入,使得這場原先自環(huán)保概念出發(fā)的反核運動,長期籠罩在一片政治惡斗的迷霧之中,一般大眾始終難窺究竟。
臺灣環(huán)保的兩難迷思
還記得筆者當記者時,曾于1985年到臺灣中部采訪過一起反對杜邦化學(xué)公司在當?shù)亟◤S的示威運動。這一運動被媒體稱為“鹿港居民反杜邦設(shè)廠事件”。事件的起因是,1985年8月,美國杜邦公司決定在臺灣彰化地方投資1.6億美元,設(shè)廠生產(chǎn)二氧化鈦。消息見諸報端以后,地方百姓反彈強烈。
當時臺灣威權(quán)時代即將進入尾聲,執(zhí)政的蔣經(jīng)國政府憂讒畏譏,惟恐針對反對運動(從早期的“黨外”到稍后的民進黨)稍事彈壓,便會遭致美國以停售武器為要挾,強行干涉施政,故而只好對反對人士多方讓步。杜邦化學(xué)公司的設(shè)廠計劃遂無疾而終。
杜邦事件是臺灣第一樁環(huán)保人士成功阻止高污染工廠設(shè)置的案例。年輕的筆者,當年眼見抗議人士在街頭搖旗吶喊,基于同情弱者的少年義憤,加之長期對美國霸權(quán)主義不存好感,不免私心同情屈居弱勢一方的環(huán)保人士。但是,日久見人心,某些環(huán)保人士與反對黨狼狽朋比,甚至進而搖身變成以權(quán)謀私的政客,難免令人懷疑他們發(fā)起運動的初衷,不過是早有預(yù)謀的利己行為。
島內(nèi)伴隨著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環(huán)保運動,發(fā)展至今至少已有30年。
于今思之,這種忽而以政治為核心概念、忽而又以環(huán)保為核心價值的扭曲的環(huán)保運動,一度使得島內(nèi)單純的環(huán)保運動走向死胡同。
杜邦事件無疑是臺灣民眾學(xué)習(xí)的第一堂民主環(huán)保課。島內(nèi)人民從杜邦事件當中,學(xué)到了通過議會辯論、專家學(xué)者的公開言論、社會團體及同儕的辯證互動,來判斷每一樁攸關(guān)民生福祉的重要議題。
由于集體環(huán)保意識的奏效,杜邦被阻擋在臺灣的大門之外。但是,選擇了環(huán)保而舍棄了經(jīng)濟建設(shè)的臺灣,顯然也就是在這個時間點上放慢了它的經(jīng)濟發(fā)展步調(diào),臺灣因此開始和兩位數(shù)的經(jīng)濟成長率告別,進入一個漫長的經(jīng)濟遲滯的休整期。這應(yīng)該就是一個成熟社會從狂飆、從少不更事,進入穩(wěn)定老練的“成年期”的一條必經(jīng)路徑吧!因此,環(huán)保一度被當政者詮釋為經(jīng)濟發(fā)展的絆腳石,同時被島內(nèi)資本家視為毒蛇猛獸。
然而,人們遭逢了類似此次日本福島核電站的泄露輻射危機時,才會猛然省思,環(huán)保實際上并不是毒蛇猛獸,它是可以拯救千萬生靈性命的公眾檢查機制。現(xiàn)代公民如果沒有基本的環(huán)保意識,他們何能參與或監(jiān)督執(zhí)政者的施政作為是否會危及公民的生存空間?
“核四廠”擺蕩在半空中13年
臺灣核電站的設(shè)立,到底是如何面對高張的環(huán)保意識的呢?核電站的設(shè)置,又是如何面對公眾和民意機關(guān)的監(jiān)督?
在臺灣4座核電站的興建過程中,前3座核電站的起造時間,適值一人(蔣介石或蔣經(jīng)國)或是一黨(國民黨)拍板就算的威權(quán)時代。而到了第四座規(guī)劃興建的時候,卻遭逢了沒有人能說了算的民意(或者民粹)高張時代。臺灣的4座核電站也見證了臺灣從天平一端的經(jīng)建掛帥時期,走向天平另一端的環(huán)保掛帥時期的戲劇性過程。
一份臺灣“立法院”列制的“核四廠”興廢時間表,可以看出臺灣第四座核電站從擬議規(guī)劃到備受各界非議,乃至民進黨執(zhí)政時期橫遭擱置,最后民進黨又自打耳光、唾面自干地宣布復(fù)建這一搖擺震蕩、左右不定的經(jīng)過梗概。
前面3座核電站是在蔣介石時代規(guī)劃開建,在蔣經(jīng)國當政時陸續(xù)完工運轉(zhuǎn)。第四座核電站則是在1983年2月,也就是蔣經(jīng)國擔(dān)任領(lǐng)導(dǎo)人的第六年,由臺灣電力公司提出興建方案。但是,到了1985年5月,由于地方百姓反彈激烈,反對核電站進入他們的生活空間,蔣經(jīng)國當局迫于無奈,只好暫時宣布“暫緩執(zhí)行”并“加強民眾溝通”。
1986年7月,臺灣民意機關(guān)經(jīng)過冗長討論,決議凍結(jié)臺灣電力公司編列的“核四”先期預(yù)算。直到蔣經(jīng)國去世,“核四廠”興建方案都沒有復(fù)活跡象。到了1991年8月,也就是李登輝當?shù)赖牡谒哪辏庞钟膳_灣電力公司提出了一個有關(guān)“核四廠”的可行性研究報告、環(huán)境影響評估報告及投資計劃。
1992年6月3日,“立法院”預(yù)算委員會通過了恢復(fù)動支“核四”預(yù)算的決議。1993年7月12日,“立法院”通過了“核四”的相關(guān)預(yù)算為新臺幣1125億元。
孰知,到了1996年5月24日,“立法院”竟然又通過一項決議,廢止所有核電廠的興建計劃案。經(jīng)過國民黨執(zhí)政的“行政院”申請向“立法院”復(fù)議,核四廠的設(shè)置方案才又死灰復(fù)燃。1996年10月18日,“立法院”又決議,核四廠的預(yù)算繼續(xù)執(zhí)行。
從蔣經(jīng)國執(zhí)政晚期的1983年,到李登輝當選第一任所謂“民選總統(tǒng)”的1996年,國民黨當局由于畏懼民間反核勢力串連成一股推倒國民黨執(zhí)政體制的巨大能量,只好犧牲核四廠,以換取選戰(zhàn)的勝利。無怪乎“核四廠”在整個1990年代,始終擺蕩在半空中,上不上,下不下。
核電爭議背后的政經(jīng)困境
基于國民黨的勝選考量,臺灣的第四座核電站數(shù)度稽延,多次被拿來當作與民進黨討價還價的籌碼。這種飲鴆止渴式的自救手段,最終導(dǎo)致缺電和經(jīng)濟發(fā)展出現(xiàn)瓶頸的困境。臺灣從1990年初期逐漸顯現(xiàn)的經(jīng)濟發(fā)展疲軟現(xiàn)象,又何嘗不是緣于國民黨這種蠅營狗茍的心態(tài)?
盡管如此,“核四廠”畢竟還是在國民黨失去政權(quán)之前,拍板定案的。這是經(jīng)過“立法院”決議的合法程序,是任何個人都無法推翻的。可是,當2000年陳水扁當選臺灣領(lǐng)導(dǎo)人之后,卻在當年10月27日由“行政院長”張俊雄悍然宣布停建“核四廠”。
雖然民進黨當局否定核電廠的動作,持續(xù)不到半年,就被迫收回成命,這么一來一回,搞了快三十年。這與蔣介石父子時代,幾年功夫就建好一座核電站的速率,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蔣氏父子當權(quán)時代,不光是政治體制與現(xiàn)今大不相同(民意機關(guān)是效忠兩蔣的不改選機關(guān),國民黨可以有效指揮一切政權(quán)單位),更大的分野是斯時(1960~1970年代之間)公民社會尚處于萌芽階段。這樣的社會型態(tài),中產(chǎn)階級的力量還十分微弱,故而十分有利于一元化領(lǐng)導(dǎo)的政權(quán)遂行寡占式的經(jīng)濟建設(shè)。
回顧臺灣經(jīng)濟建設(shè)發(fā)展的進程,兩蔣時代的確為后世子孫做了許多腳踏實地的實事。不像后來的領(lǐng)導(dǎo)人(李登輝、陳水扁)當政時期,政治人物留給人們的印象,似乎不外打架和吵架,很少在經(jīng)濟建設(shè)上下過苦功夫。不可諱言的是,李登輝、陳水扁個人的意識形態(tài),未必贏得人們的真正認同。奠基于蔣經(jīng)國晚年的臺灣公民社會,畢竟在李、陳兩氏手上,進一步得到了落實。
只是為了建構(gòu)公民社會,可能要在經(jīng)濟上付出倒退三十年的代價。好比為了是否建核電站,臺灣許多人為此紛爭喧囂二三十年,至今也沒吵出個眉目來,反而弄得社會族群分裂,意見雜亂紛陳,什么大事都做不成。
一言以蔽之,并不是有民意機關(guān)就沒有黑幕,并不是有眾多媒體監(jiān)督就萬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