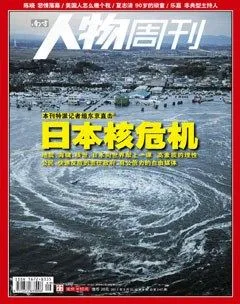區廣安 鬧市隱者的筆頭功
2011-12-29 00:00:00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9期

區廣安有許多身份,但在工作之外,他拿出來的名片只與藝術有關。他似乎是刻意地要把那個縱情筆墨的自己,跟日常那個案牘勞形的自己區分開來,薄薄的一方宣紙隔在中間。
區廣安的畫室遠可觀山,近可玩竹,樓梯旁掘著一方小池塘,流水不斷,池中錦鯉擺尾,古人玩物,而不喪志。在一塊裱好的清朝官服的云錦補服前,放著一捆竹書簡,區廣安靈機一動,掂一枚靈芝放上,“我認為三者放在一起有這樣寓意:讀書有靈氣,學而優則仕。”這不僅是他的吉祥口彩,也幾乎是其半生的寫照。
在廣州的鬧市之中,這里是他的清修之地,他的畫室“墨池春深閣”,掛著一副自書的對聯“頗得湖山趣,不知城市喧”。幾十年來,多少個日日夜夜,他在畫案上筆耕不輟,這是功夫。“功夫”在漢語里是一個多么有意思的詞,它即可以形容“水平”,也同時可以表示“時間”,這個詞透露出一切高超技巧與長久修煉之間的關系。
作為廣東國畫研究會的第三代傳人,區廣安可謂血統純正,他從六、七歲即師從嶺南書畫名家盧子樞的高徒袁偉強,成為袁的入室弟子。私塾式的習畫模式,言傳手摹,練就了他過硬的童子功。區廣安是南海人,康有為的故鄉文氣斐然,其師袁偉強雖飽讀詩書,因出身不好,不過是當地一個小學的美術教員,一生剛正清苦。“袁老師的一生對我影響巨大,他不僅教導我們掌握國畫的技法,還為我們學生留下精神財富。”他恭恭敬敬地捧出一只錦盒,戴上白手套,生怕傷了盒子里的寶貝,打開盒子,是一方粗礪的硯臺,袁偉強生前所用,驚人的是,硯臺已經磨穿,硯底一個大洞,邊緣的磨石又薄又脆。這是先生的遺物,在袁老師去世后,他的弟子們推舉區廣安代為收藏。區的畫室墻上,并排掛著盧子樞和袁偉強兩幅黑白畫像,一位是師祖,一位是師父,目光灼灼,天天在背后監督他苦練筆頭。
只有一種笨辦法
在廣東畫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黃般若、盧子樞、黃君壁為代表的廣東國畫研究會和方人定、高劍父為代表的嶺南畫派在民國時候的那場“大論戰”至今余煙繚繞,那是一個國門甫開、西風東漸的時代,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廣東國畫研究會提倡延續中國國畫傳統,弘揚國學精神,而嶺南畫派則主張中外融合,他們受到了大量西方和東瀛畫風的影響,并一度稱為廣東國畫的主流。對比嶺南派的名家輩出,廣東國畫研究會則一直相對寂寞。
人們用了將近一百年的時間,才重新認識到傳統的價值,那些曾經被我們忽視的好東西。廣東國畫研究會綿延至今,傳人寥寥,區廣安就是其中一個。
多年前,廖冰兄在看了他的畫展后評價區廣安:“他是個笨人,很笨,現在各種花招很多,辦法很多,結果他還是跟著古人,這么笨地去跟,但他跟進去,現在又成了。”
區廣安的“笨”,主要是他不隨潮流,不玩噱頭,不畫抓人眼球的概念,就像古人習畫自娛,主要是為了寄托情懷。想要技藝精進,除了多畫,別無他法。
散點透視畫丹霞
畫《千里丹霞圖》,他先后數次深入丹霞山區采風,“為山川寫照是畫家的必然使命,我每次去,都不拍照,只是通過記憶和體悟。”丹霞山地貌特殊,以“丹”、“雄”、“秀”、“靜”聞名,紅砂巖經過千萬年的層層堆積,形成了特殊的質感,他翻看了大量地質和人文的史料,研究怎樣用皴皺的獨特筆法來表現那一抹大地上的紅霞。他用朱砂著色,移步換景,把舵石、巴寨、僧帽峰等景致,貫穿著這些景致的,除了一帶錦江之水,還有若有若無的云靄,這種巧妙的布局把那些原本不可能出現在同一平面的景觀呈現在了一起,彼此獨立又互相呼應,橫跨數省的千里丹霞濃縮為15米的長卷。
長卷用的是中國畫最有特色的散點透視形式,這一視點突破了西洋畫焦點透視的局限,可隨心所欲地把本來不處在同一時空和經緯的景點,化來筆下。在長卷題頭,區廣安寫詞曰:“碧湖環赤崖,歷歷見朱砂,半壁懸空寺,深扃隱者家。心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