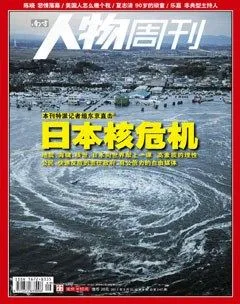一個美國人對于當下中國的深度觀察
2004年4月,我在紐約的生活百無聊賴。來自國內的消息千篇一律,關于奧運建設和世博會籌備的故事占據了所有媒體的篇幅。
突然,我在《紐約客》雜志上讀到了一篇題為《幼兒園》的報道,署名Peter Hessler,此人是該雜志駐北京記者。通篇不見宏偉敘事,內容只是北京郊區一個叫三岔的小地方,一個叫魏嘉的小孩和他的父母,還有智障聾啞的伯父的一些日常生活。小波瀾,小變化,小沖突,小抗爭。可是,那是整個中國在一個宏偉時代的宏偉變遷下的真實生活。
從那以后,我尋找一切他寫的東西。其實,他在美國已經小有名氣,因為一本他根據自己作為“和平志愿隊”的一員在四川涪陵教書的經歷所寫的書——《江城》。2008年,我完整地閱讀了他的英文著作《甲骨文》。他的中文名叫何偉。
何偉是一直和自己書寫的人物在一起的,從來不曾缺席。《江城》是他和他的學生、老師、鄰居、干部;《甲骨文》是和自己的同事、朋友、胡同里的鄰居;到了《尋路中國》,則是陌生地域里邂逅的搭車人、汽車租賃公司服務員、北京三岔的鄰居、浙江麗水工廠里的小老板和打工仔打工妹。
這些,全都是小人物,在底層隨著政治和社會變遷的風向而轉動的普通人,偉大人物和宏偉事件極少出現在他的寫作里。或許這既是何偉的寫作方法,也是他的寫作動機。我們的確生活在一個深刻變遷的時代,英雄此起彼伏,巨變目不暇接,但是真實的底層生活永遠都是那么卑微,那么無關宏旨,并且那么倔強和深入地改變著中國的圖景。這才是當下的中國,這才是被眾多宏大敘事遮蔽了的真實。
《尋路中國》由三段故事構成:他拿到駕照后沿著長城驅車前行,一路上的所見所聞;他在北京附近一個名叫三岔的小村莊租房子寫作,他的房東魏子淇一家,以及這個村莊所經歷的從自我封閉到商業化的歷程;他在浙江麗水所跟蹤的一個生產胸罩調節環的小企業的沉浮興衰和廠里的幾個工人的命運。
城墻一章,是中國人固有的傳統、根深蒂固的國民性、表面上的徹底改革與骨子里的守舊、面對全球化全面掃蕩時主動與被動的應對。一方面,物質化的過程不斷地改變著地表的形態并且凸顯人們欲望的翕張,另一方面,長期積存的傳統觀念、人情脈絡、對于法律的表面尊重和內心蔑視,也在起著作用。而恰恰是這些矛盾使得中國人在現代化面前進退維谷,尷尬無依。
村莊一章,則是一個靜謐隔絕的小村莊和它的村民在農村商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的變遷簡史。OijH697VjLtxwOLGd2bOvQ==在商業化(主要是旅游業)侵襲之前,他們勉力維持著困頓的生活;卷入商業化之后,他們依靠聰明才智迅速改變自己的命運,卻同時面對著信仰、社會結構和家庭價值的迅速解體。
工廠一章,是對浙江麗水小城尋求快速工業化的全息掃描:地方政府高歌猛進,摒卻一切障礙,包括環境、人心、政治、文化因素,務求一切以經濟發展為核心;小企業主篳路藍縷,一面是缺乏商業素質,缺乏必要的技術條件和資本積累,一面是向政府尋租,壓榨工人,還有一面卻是善于變化騰挪有道;早期的產業工人一面是跳脫農村束縛快速融入工業環境相互扶持善于學習,一面則是精明狡詐蒙昧無知。
這些小人物,與我們在歷史上見過的任何一個偉岸的人一樣,忽而人性光芒閃耀,令人著迷;忽而卑劣陰暗,令人咬牙切齒。他們被這個時代推著走,他們同時也推著這個時代走。不幸的是,這個時代,這個國度,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歷史上最令人期待也最令人恐懼的變遷:現代化。于是,這些小人物在一個宏偉時代中的微觀生態,令我們對于這個變遷變得不那么堅決甚至有些猶疑起來,因為它的前路晦暗不明,它的光輝與陰霾天人交戰,它的欲望和人性糾纏爭斗。
何偉在敘述麗水的時候曾經拿它和美國西進運動比較,一切的物質變化看起來都那么似曾相識,但是,卻欠缺那么多東西:沒有教堂、沒有獨立報紙、沒有公民社會,“當人們住帳篷的時候,當地的第一份報紙已經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當時,那的確是一個嚴酷的社會,不過,至少已經具有了早期意義上的社區和法律”。
給出的多少是某種實質性的論斷:這是跛腳的現代化。
有一段時間,我和歐美駐中國記者的圈子很熟悉,從來沒有發現像何偉這樣看待中國人的記者。他似乎深諳中國人看問題的方法,他了解中國人的行事方式,并且像他們那樣變通地運用人際關系,避開法律;但是在我看來,他最終是在用人的方式看待中國人,他們同樣光輝,也同樣卑微。
在三岔,魏子淇的孩子得了血液病要輸血。何偉知道血源不安全,于是和醫生爭執要動用私人關系。但是,他最終也沒斗過堅持利用醫院血庫的醫生。爭執之后,“我坐了輛出租車回到家,洗了個澡,一個人吃了晚飯。夜里,我感到一陣麻木。一剎那間,我在空蕩蕩的公寓里坐了起來,感到十分的無助,竟至無法呼吸。”
如果你要了解當下中國的真實生態,你就必須有這種窒息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