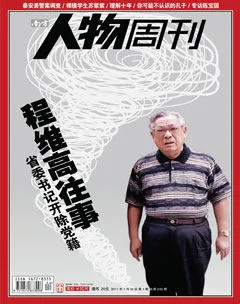找尋與確定中國在世界的坐標
2011-12-29 00:00:00陳斌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4期


2001年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12月11日,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第143個成員國。3個月前,美國紐約發生“9·11事件”。
這兩件大事,對中國外交——尤其是21世紀前10年的中國外交——均有重大影響。前者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有利于中國經濟實力和外交實力的提升;后者將美國的外交視界轉向反恐、轉向中東,減少了中國與美國因外交政策目標不同而碰撞的頻度和烈度,為中國施行既定的外交政策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實力之變與目標之不變
中國外交10年最大的變是什么?
是中國外交實力的提升。這得益于中國30年實行以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政策、融入經濟全球化潮流的開放政策,這些政策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達到了頂點。10年來,中國經濟實力不斷走強,2010年已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這必然導致中國外交實力的提升。
這種實力的提升得到了惟一超級大國美國的承認。
第二個問題:中國外交10年最大的不變是什么?是中國外交目標的一貫性,不僅是10年一貫,而且是60年一貫。
一個多月前,2010年12月7日,外交部網站刊出國務委員戴秉國的長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戴秉國再次闡述中國的三大“核心利益”,“一是中國的國體、政體和政治穩定,即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二是中國的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三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壞的”。
這可以說是對中國“核心利益”優先性序列最清晰的表述,因而也可以視為對中國外交目標優先性序列的表述,是理解中國外交的一個總體性綱領。據此,我們可以把中國外交分成3個層次:外線為經濟外交;中線為與主權相關的政治外交;內線為與基本制度相關的政治外交。
經濟外交
要談中國新世紀10年的經濟外交,繞不開2001年中國加入WTO。中國是以非市場經濟國家身份加入的。在最終簽署的加入議定書中,有一些限制性條款,其中一條很要害,在針對中國出口商品的反傾銷調查中,中國享受的待遇是“非市場經濟地位”。
由此,中國在加入WTO后頻頻遭受反傾銷調查,以2009年為例。根據WTO的《Globe Trade Alert Study》,2009年全球共發生130多起貿易制裁案,中國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多達55起反傾銷訴訟針對中國。
為此,中國經濟外交的一個基本點就是推進自由貿易。方法之一是由商務部主導,與相關國家進行一對一的談判,逐一讓對方承認中國為“完全市場經濟”國家,是雙邊外交。截至2008年2月,共有77國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包括新西蘭、新加坡和瑞士等發達國家,但不包括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美國、歐盟和日本。
在2010年5月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國承諾將“通過中美商貿聯委會,以一種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美國態度的軟化,是中國經濟實力乃至外交實力提升的體現。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承認,就像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外交承認一樣,其他國家是唯美國馬首是瞻的,美國挑了頭,其他國家就會趕上。
方法之二是建立自由貿易區,是多邊外交。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已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啟動。2004年中國提議中日韓三國研究“建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的問題”,目前中韓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仍在進行之中。
中國的經濟外交,除了體現普遍性、世界性的價值與原則如自由貿易(主要動機也是為了保出口、保增長、保就業,即受發展主義驅動的)外,更有直接的、鮮明的發展主義導向,這一點從“外交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口號中看出來。在中國,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經濟就像騎動著的自行車,速度不能太慢,GDP增長率不能低于8%,否則自行車就會倒下來,就會有就業及社會問題甚至危機,因此中國的政府必須是強勢的發展主義政府,對內有“產業政策”,對外保出口,時不時要推經濟一把;對內力撐國企,對外助國企走出去。
隨著經濟增長,中國企業大步走出去,演繹出許多傳奇,如2010年中國民企吉利完成了對Volvo的并購。但走出去的主體仍是國企,經濟外交為之開路,背后有政府撐腰,這與2003年以來“國進民退”的趨勢相一致,均是發展主義邏輯的必然結果。
以中國在非洲的存在為例,基本特征是經濟外交為國企走出去服務,也即為發展主義服務。中國對非洲國家,通常既投資改善該國的基礎設施,也投資開采該國的能源、資源,以基建換資源開采權。如2009年,中國意向在5年內給幾內亞投資70至90億美元,用于修建道路、橋梁、國家電網系統和灌溉引用水系統等基礎設施,以換取采礦權。幾內亞有全世界超過一半的鋁礬土礦藏,還儲藏有40億噸高品位鐵礦石等。在幾內亞,不難發現中國鋁業、中國電力投資集團等央企的蹤影。
中國在非洲地區的經濟合作特別是資源開采,被西方某些國家無端指責為“新殖民主義”,中國只有在這些問題上做得更好才能讓這些非議消失。
與領土主權相關的政治外交
與領土疆界相關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歐美發達國家面臨的領土或邊界爭議極少,幾乎沒有;發展中國家則面臨著大量的領土及邊界爭議,甚至走向局部沖突和戰爭。
中國現代民族國家仍在建設中。與中國陸地接壤的國家有14個,其中12個與中國簽訂了邊界條約。第一輪是20世紀60年代,中國與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爾、緬甸和朝鮮6國簽訂了邊界條約。第二輪是20世紀90年代,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老撾5國簽訂了邊界條約,與越南簽訂了陸地邊界條約。
中國的民族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并不顯著,在90年代濫觴而成為一股顯著的思潮,在新世紀10年繼續鼓而不泄,由思潮而成浪潮。2005年3至4月,由于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北京、上海和廣州等二十多個大中城市均出現了大規模反日游行。
這是由于中國可催生民族主義的題材(與領土主權相關的問題)豐富。在陸地上,中國與印度尚未有邊界條約。在海域上,中國與韓國有黃海劃界爭議,與日本有釣魚島和東海劃界爭議,與越南、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和文萊有南海諸島和南海劃界爭議。此外還有臺灣問題、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
就中國與領土主權相關的政治外交而言,作為第二線(中線)外交,在新世紀10年有不俗的進展。2005年4月,中國與印度簽署《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協定》,稱“邊界應沿著雙方同意的標識清晰和易于辨認的天然地理特征劃定”。
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2010年3月,中國向美國表示“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在漁權(背后是主權)爭奪上,2009年12月和2010年3月,在西沙群島附近海域,中國海軍分別查扣了3艘和1艘越南漁船;2010年6月底至7月初,在北部灣海域,中國漁政、海警查扣5艘越南漁船。
對日外交也日益強硬。去年中日釣魚島漁船事件即是證明。
這些行為為中國政府在國內增加了威望和合法性,但也有一些反彈,即周邊國家產生了又一波(因中國民族主義而起的)“中國威脅論”。
與基本制度相關的政治外交
新世紀10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反向經濟外交原則適用的國家范圍日益擴大,手法也越來越嫻熟。以前,為了換取一些小國“支持中國對臺灣問題的原則立場”等政治目標,中國常常是先期提供各種經濟援助,到后來就是減免貸款,實力所限,威力只能及于一些發展中國家。這些年來,尤其是2007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坐擁巨額外匯儲備,威力廣及世界,包括歐美發達國家。為了平息美國解決貿易逆差及讓人民幣升值的要求,中國常在戰略對話前夕或領導人訪問期間,對美國進行大單采購,自2006至2009年4年間,商務部每年去美國采購一次,采購金額分別為162億、326億、136億和163億美元。2009年,中國赴德國、瑞士、西班牙和英國4國,采購金額130億美元;2010年10月和2011年1月,中國分別承諾向希臘和西班牙購買債券。
與基本制度相關的政治外交,除了反向經濟外交,也有直接政治外交,這就涉及到談判和斡旋等。如2010年3月韓國天安艦被擊沉、9月朝鮮炮擊延坪島,朝鮮半島因之劍拔弩張,美國三大航母戰斗群更是齊聚西太平洋。理論上中國與朝鮮有同盟關系,簽于1961年的《中朝友好互助條約》,經過兩次自動續期,新的有效期截至2021年。中國仍是希望在六方會談的框架內和平解決目前的危機。
目前,有兩個版本的中國威脅論,一個是存在于中國周邊國家的,與領土主權相關的政治外交(第二政治外交),例如,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南海和釣魚島的強烈立場,引起了東盟和日本的反彈,越南強烈希望美國介入南海,8月越美在南海舉行了聯合軍演;日本則博得了美國日美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的承諾。
另一個是存在于世界,尤其是美國的,同與基本制度相關的政治外交(第一政治外交),例如,在朝鮮半島危機中,中國態度柔和,韓日美態度強硬,覺得中國不給力,美國三艘航母為此齊聚西太平洋,這一行為強化了美韓、美日同盟。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治標或許在于“韜光養晦”,治本就是一項系統性的工作。
宣示“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是一個環節。2003年11月,官方智囊鄭必堅在海南博鰲論壇發表題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的講演,首次提出中國要“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12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哈佛大學發表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闡釋了中國為何選擇“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2005年3月,溫家寶在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和平發展”(Peaceful Development)的概念,說“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是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要做實自己對世界、對國民的每一個莊嚴承諾,在人權保護與經濟發展兩方面都有建樹,才能在這個不斷走向“普遍同質國家”的世界中,找到屬于自己的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