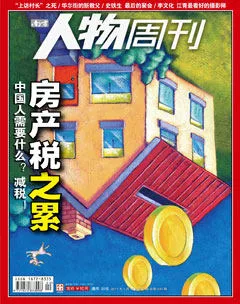2011年的最大危機是權貴繼續絞殺市場
2011-12-29 00:00:00葉檀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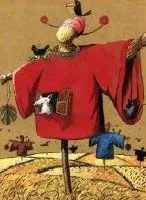
法國大革命爆發并非第三等級食不果腹,而是因為市場的自由貿易以及相關的權利被權貴剝奪
此文回答一個揮之不去的疑問,為什么我如此看好中國經濟卻不敢對中國未來抱有過多的樂觀?
一言以蔽之,權貴資本導致財富鴻溝越拉越大,尚無制服權貴貪婪之胃的致命武器。這無關經濟,有關經濟體制。
中國的市場腹地夠大,消費群體夠多,前30年已經積累了巨額財富,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每年固定資產投資在25%左右,中國需求可以左右澳礦與澳元漲跌,中國央行的政策可以影響亞太股市漲跌,2009年開始三四線城市房價直線上升——可惜的是,所有這些無法構成足以讓市場健康發展的“中國模式”,甚至,有沒有“中國模式”都讓人懷疑。
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并非中國特有。經濟史家格龍申科通過對南歐與東歐的研究,指出在市場經濟的初期政府傾向于深度參與經濟,更別說中國這樣一個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的社會。
政府主導市場在計劃經濟模式與市場初期的經濟體中大范圍存在,這并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因。同樣由政府主導,中國經濟在1949后的前30年與后30年截然不同,前后30年的不同在于,政府與市場之間形成了互相制約、互相促進的空間。
政府成為市場爭利者,也即成為毫無爭議的市場貴族。在房地產市場是一級市場的壟斷者,在證券市場是政策與國資的主導者,通過數十萬億國資的逐漸釋放,政府急速地將證券市場變成吸金管道。
政府中單獨的個人,以及與權力關系密切者同樣成為市場中的權貴,在資本鍍金時代財富集聚度大幅度提高。根據WIND資訊不完全統計,2010年上市的340多只新股中,持股市值上億元的個人股東高達824位,相當于平均每只新股上市就有2.4位億萬富翁產生。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調查顯示在股市上賺錢的股民不足20%,近70%的股民虧錢。這說明中國的證券市場沒有給大多數投資者帶來賺錢效應,一些圈錢的權貴企業上市讓大多數人變得更加貧困。如雙匯等公司停牌后連續漲停,給埋伏在內的投資者帶來了數億元的財富效應。
一旦證券市場的迷人魅力散盡,就會暴露吸血機器的真實面目。如果中國證券市場無法回到資源配置與公平交易這個根本,將成為第二個被民意唾棄的房地產市場。
房地產成為腐敗重災區。原河南滎陽市財政局長薛五辰擁有9套住房,建筑面積達1300平方米;原深圳南山區委書記虞德海擁有豪宅8套,建筑面積達940多平方米;原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戴國森家被搜出房產證十余本。一份流傳久遠的《多余安置房按暫定價銷售給外部人員名單》顯示,“樂清錢云會事故調查組”組長沈強擁有一套277.89平米的安置房,按照市場價估算,可為沈強帶來900萬的收益。
不能說政府不顧及低收入階層。從2009年開始,新的醫療體制改革實施,計劃在3年內新增投入8500億,折合每年約2800多億,加上2011年新增的1000億,2011年用于醫療衛生和個人醫保的總支出將達到4000億。各地最低工資也屢屢上調。
權貴在絞殺中國培育中產收入階層、培育內需的努力,200元的最低工資上調比例與動輒數億元的財產性收入,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當腐敗滲透到最低行政等級時,我們只能得出權貴絞殺市場的結論。
再強調多次也不為過:法國大革命爆發并非第三等級食不果腹,而是因為市場的自由貿易以及相關的權利被權貴剝奪;中世紀的密西西比泡沫并非市場不利,而是法國權貴階層在市場套現刮盡了所有的民財。
我們有一萬個理由可以證明在人口眾多的國家政府主導不可避免,“新加坡模式”是我們所能尋找到的最好模式,但我們有一萬零一個理由論證,我們欠缺“新加坡模式”的核心,那就是對于國民相對公平的法律體制,以及尊重市場效率的資源分配方式。
為什么對中國經濟未來仍抱有希望,是因為30年的市場積淀以及正在進行的內需改革;為什么我們時刻緊盯著權貴資本,是因為這一階層貪得無厭、不受規則制約,將在一夜之間毀滅改革成果,并且移民到大洋彼岸靠著瑞士銀行的賬戶繼續在民脂上過寄生蟲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