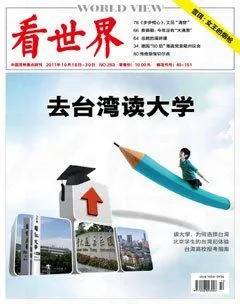鄭永年:解釋比改造更重要
2011-12-29 00:00:00王猛
看世界
2011年20期
鄭永年,1962年生于浙江余姚,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其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系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系,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系,中國政治。著有《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未竟的變革》等。
鄭永年近年在兩岸三地非常活躍,盡管他領導的東亞研究所目前已占據新加坡研究中國問題的壟斷地位,但他仍然聲稱,必須每天修正甚至否定自己的思維和觀點,“我最大的敵人是昨天的自己。”這頗有幾分“高處不勝寒”的味道。
對于中國大方向和大政策,鄭永年把握得比較到位也比較及時,并且他還善于運用中國大陸、臺灣地區以及西方都能接受的話語。但也有人指出,鄭永年畢竟長期沒有在內地生活,對于國內情況他雖然經常跟蹤,卻缺乏真實體驗。
對于這些外界的評論,鄭永年并不太在意。他更關注的是,中國目前這種急劇的變化。“你看到的可以是一個很糟糕的社會,也可以是一個改造得更好的社會。”現年49歲的鄭永年非常認真地說,“我希望活到100歲,好好地做學問,把中國解釋清楚。”
他只解釋中國
“中國太浮躁了,沒有理性思考的空間,但這個社會需要有人思考。”鄭永年笑言,所有人都把他當成一個專欄作家,但寫專欄只是業余愛好,他的主要學術著作都是用英文寫就的。而“解釋中國”正是他現在著力研究的課題。……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