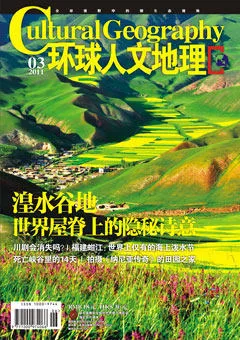地可以怨否?
最近看到研究中國藝術史的美國學者姜裴德(Alfreda Murck)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畫可以怨否?《瀟湘八景》與北宋謫遷詩畫”。湖南瀟湘是風景獨特的地方,在人們的心目中,那里有一派煙靄迷蒙的山水,散發著哀傷怨情。姜裴德指出,瀟湘的怨情主要來自古代一批謫遷文人詩作的渲染。歷史上在瀟湘地區撰寫詩文的作者,多為謫遷之臣,如屈原、賈誼、杜甫、柳宗元等。《瀟湘八景》是一組山水畫,作者宋迪到過瀟湘,貶官后與一班謫遷人物退居洛陽。姜裴德認為,宋迪在貶官之后滿腹憂傷,讀杜甫的詩句,觸發而作《瀟湘八景》。宋迪的《瀟湘八景》為:平沙落雁、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用姜裴德的話說,“不難看出,這些畫強調暗沉的天色與時間的結束,宋迪在以畫抒情,畫可以怨。”
含有怨情的《瀟湘八景》,好事者多傳之。瀟湘怨情,無論是詩也好,畫也好,都離不開瀟湘這塊地方,所以,詩可以怨,畫可以怨,其實,地也可以怨。甚至,如果詩句忘了,畫面忘了,而那塊地方卻依然“怨”在心頭。向“地理”灌注情感,反過來再以“地理”表達和記憶情感,是我們文化的一個傳統特色。古代文人灌注過愁情的地方,除了瀟湘,還有巫峽、汨羅江、無定河,以及較為抽象一些的“邊塞”、“天涯”和“一江春水”。這些攜帶情感的“地理”,在今天影響多少還在,可謂天長地久。
賦予特定的地方以特定的情感,是一個文化地理過程。“地理”一旦與特定的情感永久結合,它便成為一種情感符合。情感與自然景觀、地理位置的相互轉化,是我們古代人地關系的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那些寫遍名山大川的文人題刻,正是這種關系的直接記錄。近代曲學大師吳梅在《詞學通論》中說:“詠物之作,最要在寄托。所謂寄托者,蓋借物言志,以抒其忠愛綢繆之旨。”中國文人最善利用自然景觀也就是假手大地來抒情,李白也說過“大塊假我以文章”(“大塊”即大地)。
看到詩文情感與地理相結合,使我們又聯想到神話傳說、歷史故事、宗教思想、民間傳說等思想文化與地理的種種結合,比如涿鹿之野、咸陽古渡、馬嵬坡、飛來峰、景陽岡等,這些多種多樣的結合,無疑增加了大地的文化含量。中國是大地域文明古國,神州的文化含量極為豐厚,它們如同煤炭、森林、水源一樣,也是珍貴的地理財富。現在新發展起來的旅游地理學,正是發掘利用這類財富的一門學科。旅游是依賴地理移動才能完成的文化行動和感情行為,旅游一定要去異地,而異地的景觀情調一定要新奇動人,異地的文化底蘊一定要厚重深沉,方能滿足人們的身心。
提到旅游,我們又知道,具有主動精神的旅游者不喜歡像羊群一樣跟著導游走,他們愿意自己去發現、感受。的確,看人們旅游的方式和對象,可以知道他們的休養和志趣。據說,在收藏界,人分為三等,集郵票的人是“中學生”,集古玩的是“大學生”,藏古書的是“研究生”。對旅游者來說,志趣高者不在收攬美景,而在巡游古跡,憑吊懷古,又以哀怨為情界最高。游新漆的廟宇,看乍刻的石闕,其美學分量均不及吊汨羅江水,聽瀟湘夜雨,尋赤壁折戟。古人有“行萬里,讀杜詩”的傳統,今人有作“文化苦旅”的精神。中國式的旅游常伴有強烈的歷史感,和由此產生的穿越古今的悠遠心境,這即是我們的文化,也是我們面對祖國大地時無法揮去的情懷。
明代地理學家王士性,宦轍遍天下,在瀟湘,他深感娥皇、女英的古老故事,寫下“九嶷日落瑤華遠,哭斷瀟湘不見君”的哀怨詩句。今天,在東方古老文明中壯游的旅行者兼散文家張承志,在訪問美洲之后,對于美洲北部無人的高山森林,曾有這樣的令人深省的感慨:為什么這里沒有如同哈薩克天山那樣的傳說、風俗、道德和美好的文化呢?我至今喜歡那片自然,只是我明白我不能向它尋找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