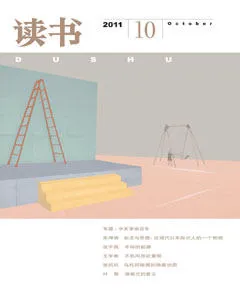總體性失敗與革命起源
著名的法國大革命史專家傅勒在《思考法國大革命》(三聯(lián)書店二○○五年版)中說,當一個歷史事件失去當下一切參照意義、不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后,“它也就從社會論戰(zhàn)領域轉(zhuǎn)移到學者討論的領域去了”。那么反過來說,如果這個歷史事件仍有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它就注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學者的討論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于“社會論戰(zhàn)領域”,成為社會關注的公共話題。
至少,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法國大革命一百六十余年后,法國仍然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公民必須挑選歷史,填寫出生年月,選擇舊制度或大革命。”現(xiàn)在,法國大革命才在法國政治中消失了,因為“今天,無論右翼還是左派,雙方的說辭都為自由和平等彈冠相慶,而圍繞一七八九年價值展開的辯論不再包含真正政治利害關系,也不再包含強大的心理投資”。
今年是中國辛亥革命的百年紀念,百年來,辛亥革命在中國一直具有強烈的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想象的鏡子,包含明顯的政治利害關系和強大的心理投資。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國共雙方在你死我活的大搏殺中都要爭奪“辛亥革命”的話語權。國民黨以辛亥革命的正統(tǒng)自居,將共產(chǎn)黨人作為“逆黨”;共產(chǎn)黨人則通過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共產(chǎn)黨革命”這一系統(tǒng)的“革命歷史話語”的建構,力證自己的歷史合法性,自己是孫中山先生的真正繼承人,不是別人正是國民黨背叛了孫中山。今天,“辛亥革命”、“國父建國”在臺灣一直是國民黨反“臺獨”的論述主軸之一,以此接續(xù)“一個中國”的歷史與現(xiàn)實的脈絡;民進黨對辛亥革命則態(tài)度曖昧。在大陸,辛亥革命作為“革命話語”中的一部分,仍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論述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地位正當性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同時又是對臺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有學者反思激進主義,批評孫中山、辛亥革命是激進主義,認為在清政府的“立憲”下,中國后來的歷史可能更少波折,這種觀點目前影響漸大。
在這種語境下,關于革命“意義”的論述不能不包含“強大的心理投資”,必然根據(jù)立場、需要的種種不同產(chǎn)生眾多面相,往往是各有其理,各是其是非其非,各執(zhí)一辭,實難互相討論。
但是,上述最后那種觀點,即認為辛亥革命是“過激”、是孫中山等少數(shù)幾個革命黨打斷了清政府主導的“立憲”過程,卻頗具可討論性。因為它實際是在革命“起源”的論述中展開其革命的“意義”話語。而關于革命“起源”的探討可能要比“意義”論述客觀得多,“意義”注重的是“闡釋”(Hermeneutics),“起源”側(cè)重的是“解釋”(Explanatory)。闡釋可以沒有邊界,解釋卻有嚴格限制;闡釋強調(diào)想象與建構,解釋注重實證與分析,所以“起源”比“意義”的“可討論性”強得多。
一
導致清王朝覆亡的武昌起義事起倉促,仿佛一夜之間一個碩大無比的王朝就轟然坍塌。其實,這是自一八四○年起,清王朝對中國面臨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懵然無知、應對失據(jù)、步步被動,各種問題、矛盾越積越多越來越尖銳的總爆發(fā)。因此,分析辛亥革命的起源,還真不能不從頭梳理。
鴉片戰(zhàn)爭后,清王朝之所以昧于世界大勢,因為舉國上下仍然沉浸在千百年來的“華夏中心論”、“華夏文化優(yōu)越論”、中國是“天朝上國”的優(yōu)越感中,認為只有中國典章制度、聲名文物才是“普世的”,因此只有華夏是文明的;而其他文明、文化都是“特殊的”、是一種“地方性知識”、是“邊緣”,因此是野蠻的。總之,這種“中心”與“邊緣”之分、“普世”與“特殊”在歷史中演變成文野之分,具體說就是“夷夏之辨”,要“嚴夷夏之防”,如果要變,也只能是以夏變夷,而不能以夷變夏。
因此,鴉片戰(zhàn)爭使林則徐認識到英夷船堅炮利的厲害,與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應對之策,卻遭到“潰夷夏之防”的嚴厲指責;旨在啟發(fā)國人“睜眼看世界”的《海國圖志》也遭冷遇。直到二十年后,曾、左、李在推行洋務時,“師長”之說才重受重視。
從一開始,洋務運動就阻力重重,極不順利。幾臨滅頂之災的清王朝在這樣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它對應不應該仿造洋槍洋炮洋輪等“救命之舉”竟猶豫不決。今日認為十分“溫和”的“洋務運動”,在發(fā)軔之時也被指為“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曾遇到強烈的反對。以現(xiàn)代大機器生產(chǎn)來造槍炮船艦、通電話電報,明明是統(tǒng)治者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卻遇到統(tǒng)治階級中冥頑不化者以“夷夏綱常”這類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的強烈反對。
例如,李鴻章從一八六五年起就提出要開辦電報事業(yè),卻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反對的主要理由是:電報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國”,因為:“夫華洋風俗不同,天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穌,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毀其家木主。中國視死如生,千萬年未之有改,而體魄所藏為尤重。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沖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心何以安?傳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藉使中國之民肯不顧祖宗丘墓,聽其設立銅線,尚安望尊君親上乎?”這種思路、這種邏輯推演、這種論證方式是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思維定式,因此,直到十五年后清廷才批準開辦電報事業(yè)。循此思路,鐵路建設遇到的阻力更大,從李鴻章一八七二年提出修鐵路到一八八九年清廷同意修,整整用了十七年時間。
在這些爭論中,“頑固派”很少從技術層面論證、反對新事物,而是從政治、道德、意識形態(tài)的“高度”來否定新器物的合法性。這種對外來新事物首先要質(zhì)問其性質(zhì)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泛意識形態(tài)化”的深厚傳統(tǒng)和話語體系,使主張架電線、修鐵路者長期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勢”。
從知識論角度說,列強的船堅炮利、電報鐵路,是國人對“現(xiàn)代”最早、最直觀的感受,人們遲早必然會感覺、認識到這些器物背后的現(xiàn)代自然科學知識,一種對中國來說全新的知識體系。
在中國傳統(tǒng)知識譜系中,只有儒學經(jīng)典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而自然科學知識的地位極低,“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只有苦讀圣賢經(jīng)典、尋章摘句、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術”一直被視為“雕蟲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近代從西方傳來的聲光電化等自然科學知識開始不僅被鄙視為“夷務”,而且與侵略聯(lián)系起來,主張學習者被攻擊為“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謀也”。
能不能“師夷長技”之爭的核心是中國社會轉(zhuǎn)型中西學(此時主要是自然科學知識)的價值問題,實質(zhì)是自然科學知識是否具有“普適性”,即究竟是一種“地方性知識”還是一種“普適性知識”。頑固派堅決反對引入,即認為這種知識不具普適性、不應為“我”所有,且是對“我”構成威脅的“他者”。洋務派強調(diào)其能為我用,是對其“普適性”的初步承認。其實,任何一種知識都產(chǎn)生于具體的“地方”,所以每種知識的源起都具有“地方性”,如果因此認為任何知識都沒有普適性,那么所謂交流、交往將沒有意義,不同文明之間根本無法溝通,人類也不可能發(fā)展進步。從發(fā)端于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在近代中國引入之初被稱為帶有歧視性的“夷務”,到具有地域性的“西學”,都被認為只是一種“地方性”知識。不過,在中國的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中,這種“地方性知識”遲早會被承認為“普適性知識”。
一八九七年秋,維新運動走向高潮,維新派在北京創(chuàng)辦了“西學堂”,后改名“通藝學堂”。其課程除外語、法政等外,還有天算、地理、礦務、格致、制造等。在維新派的策動下,“新政”對科舉考試的內(nèi)容做了某些改變,不考八股文而考策論,并破天荒地將“中西算學、聲光電化諸學”列入考試內(nèi)容。在中國的知識譜系中,自然科學知識第一次“合法化”。然而,慈禧發(fā)動戊戌政變后,新法盡廢,包括自然科學在內(nèi)的“西學”也受到影響。科舉考試仍考八股時文,自然科學知識合法化尚未施行就流產(chǎn),首次合法化努力嚴重受挫。時人報道說:“近月以來,凡都中士大夫有談及西學新法者,同寮之中均聞而卻避。蓋恐人指之為康黨,以致罹于法網(wǎng)。故自同文館以外,竟無人再敢言聲光化電之學,念愛皮西提之音。”通藝學堂也不得不解散。
只有在經(jīng)過“庚子”大亂、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之后,清廷開始“新政”,興辦學校,自然科學知識才重獲朝廷首肯。一九○四年元月,清政府頒布了《奏定學堂章程》,這是現(xiàn)代中國由國家頒布的第一個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行、推行的系統(tǒng)學制,是我國現(xiàn)代學制(包括中小學系統(tǒng))正式確立的標志。因該年為農(nóng)歷癸卯年,故稱“癸卯學制”。“章程”將自然科學知識規(guī)定為學校課程,在中國的知識譜系中,自然科學知識最終獲得了“合法性”。此時,上距鴉片戰(zhàn)爭已六十余年,下距清亡僅六七年光景。
現(xiàn)代中國自然科學知識從“夷務”到“西學”,再到“新學”、“通藝”,這種名稱之變實即“身份之變”,表明現(xiàn)代中國從開始僅認其為一種“地方性知識”,最終十分被動地承認它為一種“普適性知識”的曲折艱難歷程。
現(xiàn)代自然科學的引進都如此曲折艱難,現(xiàn)代政治制度的變革、是否承認其具有普適性必定更加困難。
二
甲午戰(zhàn)爭的慘敗,把政治體制變革提上歷史的議程。本來,一八九八年“戊戌維新”時清政府尚有一定的變革主動權,但它卻拒絕改革,無情鎮(zhèn)壓體制內(nèi)的改革者,喪失了一次難得的機會。
只是在經(jīng)歷了兩年后的“庚子巨變”這種大流血之后,它才在“內(nèi)外交迫”的情況下開始“新政”。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逃途中以光緒的名義頒下諭旨,表示愿意“變法”,當然仍強調(diào)“不易者三綱五常”。不過為時已晚,形勢已經(jīng)劇變,尤其是經(jīng)歷了庚子流血的巨變,懲兇、賠款,它的統(tǒng)治的合法性開始遭到普遍的懷疑。由一個合法性遭到嚴重質(zhì)疑的政府來領導進行對社會各階層利益進行調(diào)整和再分配的改革,的確有些勉為其難。更重要的是,在幾年之后再做這些已遠遠不夠,需要做更多的改革或妥讓。此時,局限于行政方面的新政已無濟于事,人們開始提出立憲的要求。
一九○五年日俄戰(zhàn)爭的結果,使許多人突然意識到這場戰(zhàn)爭“非軍隊之競爭,乃政治之競爭。卒之日勝而俄敗,專制立憲,得失皎然”。“此非日俄之戰(zhàn),而立憲、專制二政體之戰(zhàn)也。”“以小克大,以亞挫歐,赫然違歷史之公例,非以立憲不立憲之義解釋之,殆為無因之果。”社會輿論和觀念發(fā)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相信立憲可以富國強兵、可以救亡圖存,甚至某些原先反對立憲的守舊人物也轉(zhuǎn)而傾向支持立憲。這樣,原本影響不大、只是少數(shù)人的立憲活動因此影響大增,開始“復蘇”,不久就迅速高漲。
日俄戰(zhàn)爭的另一個重要后果,是一些留日學生由“愛國”走向“革命”。
面對獨立的學生愛國運動,清政府認為是“反清革命”,將“拒俄義勇軍”與從前的唐才常武裝勤王的自立軍相比,“名為拒俄,實則革命”。對此時尚未走向革命的“拒俄”學生,清政府一開始是嚴令禁止,禁而不止之后干脆鎮(zhèn)壓。正是清政府對學生拒俄運動的鎮(zhèn)壓,促使學生迅速激進化,開始轉(zhuǎn)向革命。蔡元培是“辛亥元勛”之一,但在當時,他在其參與創(chuàng)辦的《俄事警聞》上發(fā)表《告革命黨》等文,還勸立志“反滿革命”的革命黨人不應該“不追盜而徒責吾仆通盜之罪”,應與清政府共同抗俄。一九○三年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后,《俄事警聞》停刊,于一九○四年二月底改為《警鐘日報》出刊,蔡元培任主筆。正是在這期間,蔡元培變得更加激烈,在一九○四年還參加了軍國民教育會的“暗殺團”。
日俄戰(zhàn)爭使立憲風潮再起,革命派開始形成力量。這樣,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清政府、立憲派、革命派這三種政治力量究竟如何分化演變、究竟誰消誰長,最后是立憲避免革命、還是革命壓倒立憲,抑或維持現(xiàn)狀,端看哪方能洞察時勢、乘時運勢了。
三
一九○五年十一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chuàng)刊,力量相對弱小的革命派以此為陣地向立憲派猛烈進攻,而立憲派則主要以《新民叢報》為陣地奮起反擊,雙方展開了一場規(guī)模空前、聲勢浩大的激烈論戰(zhàn),持續(xù)了十五個月之久。論戰(zhàn)涉及清王朝的性質(zhì)、種族與民族問題、國民素質(zhì)、中國應該建立什么樣的政體、土地制度、革命會不會招致列強干涉引起中國崩潰等許多方面。但是,最緊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決定論戰(zhàn)雙方勝負的卻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問題。
簡單說,革命派認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憲。立憲派則認為,暴力只會導致血流漂杵,帶來巨大的災難,得不償失。他們寫道:“革命之舉,必假借于暴民亂人之力。天下豈有與暴人亂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終亦必亡,不過舉身家國而同葬耳。”他們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憲,清政府“終必出于讓步之一途”,可以實現(xiàn)代價最小的和平轉(zhuǎn)型。
在越來越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