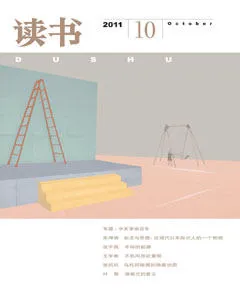范用與羅莎的畫
我的父親、母親與范用叔叔是相交近七十年的三聯老友。可以說,范叔叔是看著我長大,而我是看著范叔叔變老的。
八十年代,我常在文化界采訪組稿,與范叔叔的共同話題漸漸多了起來。每次去北京朝內大街一六六號辦事,我都要到五二○號房間去拜望他。碰到《讀書》的“五朵金花”在那喝咖啡,就和她們共享共樂。有段時間,文壇風云變幻,大家說話都很謹慎,而范叔叔卻仍在口無遮掩地針砭時弊,為一些文友遭遇的不公憤憤不平。我總是忙著把辦公室的門關緊,說:“小聲點!小聲點!”他總是擺擺手說:“沒關系,不要緊!”有次,范叔叔考我:“什么叫自由化?”我答:“越來越講不清了。”一向思維跳躍的他,突然問我羅莎現在在哪里,過得怎么樣了?
羅莎是媽媽羅萍的小妹,羅家六兄妹中最開朗活潑,也最有藝術氣質的人。她崇尚自由,個性獨立。為表示對德國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的敬仰,她獨自把我外公為她起的名廢了,改名叫“羅莎”。抗戰后期在大后方,她先在桂林美專學畫,一九四四年又跟著演劇隊撤退到重慶,經我媽介紹,在讀書出版社義務當了五個月的練習生。范叔叔說,他印象最深的是羅莎的笑。她大笑時會旁若無人地前后翻仰,仿佛全部精力都投入在笑的聲音和姿態中。別人有時被驚呆,她自己則非常享受,非常陶醉。在出版社,羅莎因為字寫得漂亮,又會畫,常給范用當下手,幫他搞封面設計,替他跑印刷廠,跟他學捆扎郵包。自從羅莎去成都藝專學西畫之后,范用就再也沒見過她。
崇尚自由、個性獨立的羅莎在“文革”中自殺了。一九六六年夏,在全國愈演愈烈的大批判聲浪中,鄧拓、傅雷等著名文人義不受辱,含恨自盡。羅莎并不是什么名人,連黨員也不是。她當時只是單位辦公室的秘書。因為文筆好一些,受到重用,被列為單位“三家村”成員。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對羅莎的肆意中傷,激起了她的憤怒。她“不識時務”,貼出大字報反擊,引起軒然大波。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羅莎在批斗大會前服“敵敵畏”自盡了。
我媽媽從不愿談這段傷心往事,所以從不向范用提起羅莎。
范叔叔聽我講述后神情沉重,不斷地重復說:“我很難過。太可惜了,真是太可惜了!”過了兩天,范叔叔打電話叫我去他家。在他臥室墻上,新掛出一個極簡樸的木質鏡框,框中鑲著一張鉛筆素描,是羅曼·羅蘭的頭像。圖紙已泛出微黃,看來有些年月了。范叔叔指著它說:“喏,羅莎送我的,掛出來紀念她。”這張畫經過戰爭的烽火、政治的浩劫,竟然在范叔叔手中完好地保存了下來,真令我驚訝和感動!它應該是羅家僅存的羅莎早年遺畫了。我很想替媽媽討要,但又不敢。上學時,我曾莽撞地向范叔叔討要《浮士德百卅圖》(群益初版)的精裝珍本,因為那是一九四七年我父親從頭到尾負責印出的。精裝本是布面的,只印了一百本,父親手頭沒有存書,所以我很想討要。那時,我不真正懂書,不了解范叔叔“愛書如命”,更不知道范叔叔正逢出書不順,脾氣很大。我的討要遭到我認為非常粗暴的拒絕。之后,他有半年之久沒有搭理我。我為此還委屈地哭了一場。那次的教訓,我是刻骨銘心的。這次,我只默默盯著小姨的畫,依依不舍地看呀,看呀,希望范叔叔從我的神情明白我的內心,就等他說一聲:“拿走吧。”
但是,我一直沒有等到,令我傷心失望。
事后向媽媽說起此事時,媽媽說:“能被你范叔叔收藏至今的每件東西,與書都有一段值得記憶的故事。”她說我們應當為此感到欣慰。
羅莎這幅畫究竟與書有什么相關故事呢?我一直想問問范叔叔。二○○○年,我退休回上海協助媽媽整理羅家家史,并把她寫的《童年記憶》一章寄給范叔叔。一天,郵局送來一個掛號郵件,像雜志一樣大小,薄薄的,硬硬的,包裝得很仔細、嚴實。拆開一看,兩層硬紙板中夾的竟是那幅我想得到的羅曼·羅蘭頭像!范叔叔還附了一張給我的便箋,說明羅莎在畫像右下寫的英文名字,和“作于一九四四年”。媽媽和羅莎訣別了近三十五年,終于在她生前見到了妹妹珍貴的遺畫。羅家幾代人,都感激范叔叔將它完好保存了五十六年。
關于這幅畫背后的故事,我原本以為與愛情有關。但那時范叔叔已有了兒子范里,羅莎也有了戀人,想想又不大可能。在得知真相后,我為自己有過的猜測感到羞愧。原來,范叔叔年輕時是羅曼·羅蘭的崇拜者,這位法國大作家具有的音樂修養,令酷愛音樂的范叔叔欽佩萬分。他不但欣賞羅曼·羅蘭書中關于音樂的描述,而且認為他的文字節奏也很具樂感。他能熟背羅曼·羅蘭的不少名句,如:“我曾經奮斗,曾經痛苦,曾經流浪,曾經創造??有一天,我將為新的戰斗而再生。”他一直熱衷于搜集羅曼·羅蘭著作的中譯本。在桂林時,起先他手頭只有陳占元譯的一本《貝多芬傳》,后來詩人洪遒送了他一本傅雷譯的《米開朗基羅傳》。他喜愛傅雷的譯文,發瘋似地從頭至尾抄了一遍。當時,洪遒對《約翰·克利斯朵夫》非常著迷,說這本書好像一部宏大的交響樂,有序曲,有尾聲,每一卷都像不同旋律的樂章。寫得真是美極了!這感染了范叔叔,他千方百計從桂林、衡陽、曲江、南昌四地的商務印書館,好不容易湊齊了一套四卷本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是傅雷的譯本。范叔叔愛不釋手,讀得如醉如癡。他早已與羅曼·羅蘭反戰的人道主義思想有著共鳴。讀羅曼·羅蘭的書,他更堅定地認為,人必須具有不屈不撓、永不氣餒的個性和意志,方能達到理想的彼岸。
一九四四年夏秋之交,日寇大舉進攻我國西南。在書業湘桂大撤退時,范叔叔將店里存書打了三十多個包,從桂林輾轉運到重慶。自己則隨身帶著一直珍藏的一批史料和書,包括羅曼·羅蘭的這幾本,還有周立波送的《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卞之琳的《十年詩草》、馮至的《十四行詩》、梁宗岱的《屈原》、紀德的《新的糧食》等書,以及聶耳日記的手抄稿。一路躲避戰火,撤退到重慶。在貴陽中轉時,書店同仁已疲憊不堪,身無分文,餓得吃不上飯。有人勸范用把書賣了,他死也不肯,說:“別的可以不要,心愛的書不能丟!”我父親賣掉一條西裝褲,大家這才吃上一餐鴨頭面。“真是香得不得了啊!”——多少年后,范叔叔已是三聯書店的總經理,并以“美食家”遠近聞名,但談起貴陽這頓“美餐”,還是念念不忘呢。
一九四四年真是令人悲喜交加的一年!中國北方抗日戰場開始了局部反攻,但國民黨在豫、湘、桂戰場的潰敗,又一次導致大片國土淪喪。日軍兵鋒所指,重慶為之震動。國統區特務政治愈加黑暗,韜奮先生受迫害在流亡生活中病逝;但同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曙光初現。羅曼·羅蘭在見到自己祖國獲得解放后去世了。羅曼·羅蘭三十年代出任國際反法西斯委員會主席。“二戰”時在病中仍堅持爭取民主、反對侵略戰爭,在中國文化人中享有很高威望。重慶文藝青年掀起了一股“羅曼·羅蘭熱”。范叔叔手中的那幾本藏書,成了大家傳閱的搶手貨。無奈,人多書少,只好依次排隊。羅莎當時就在店里當練習生,她整天纏著范用,求著讓她先看。范用說,她是學美術的,就先看《米開朗基羅傳》吧。誰知羅莎說她早讀過好幾遍了,非要看《約翰·克利斯朵夫》,并說:“我是有報酬的,可以預付!”羅莎亮出一幅羅曼·羅蘭的素描頭像,在范用眼前晃了幾晃。喜好收藏的范用馬上向她討要。正好,詩人何其芳借走的書剛還了回來,范用就此與羅莎達成了口頭交換協議。羅莎還書時,為范用背誦了其中她最喜歡的一段文字,還展示了據此段文字創作的一幅彩色寫意畫。畫面上,黝黑的危崖后面,正在冉冉升起的太陽已將天空染成了金色。羅莎沒有寫實畫出精疲力竭的克利斯朵夫,和他帶著同達彼岸的那個沉重的孩子,只是指著自己的畫,自問自答地說:“‘孩子,你是誰呀?’——‘我是即將到來的日子’。”不用說,范用自然很欣賞,馬上又向羅莎討要。可是,羅莎這次說什么也舍不得送范用了。
如果羅莎當年將這畫送給了范叔叔,后來它就不會在戰亂中丟失了。其實,范叔叔手頭與傅雷、羅曼·羅蘭有關的所有資料全都完整保存了下來,羅莎的畫只是其中之一。此外,還有何其芳借書的信,羅曼·羅蘭致隱漁函等等。還有,他抗戰勝利前在桂林和重慶精心剪輯了一本有關資料,戈寶權根據他提供的這批資料,寫了一篇《羅曼·羅蘭生平及其著作和思想》,發表此文的那期《群眾》周刊,他也一直保存至今。范叔叔說,與羅莎這幅畫有關的文化背景,他都寫在關于傅雷和戈寶權的文章中了。只是,當時沒有篇幅寫羅莎,他想以后單列一個題目,得先打好腹稿。
范叔叔的寫作習慣我知道,他說自己“寫東西很慢”。他曾初步擬了近二百個題目,想從童年寫到老年。每寫一個題目,都要看許多自己收存的有關資料,大致將腹稿框架打好后,便反復向別人講述,在一遍遍的講述中,激發補充新的回憶,然后一氣呵成寫下來,基本上沒有大的改動。關于羅莎,我有幸第一個聽他不連貫的口述。那是因為,范叔叔的老伴去世后,他的心情久久不見平復。二○○三年三月,他接受李子云和李黎的建議,來上海散心,與老友聚談,先在我家住了兩日。范叔叔和我都是“夜貓子”。在月朗星稀的春夜,他終于得閑,容我細問細談了許多事。
范叔叔最終沒有來得及寫羅莎。或許,他想寫但沒有寫出來的,還有另一些有關書與人,或歡快,或有趣,或曲折,或沉重,或可笑,或哀傷,或慘痛,或值得回味反思的故事吧。
這些飽熏著人類各種情感,又能折射時代風貌,卻稍縱即逝的歷史細節,就這樣隨著他的逝去,永遠地埋沒了。
(謹以此文紀念出版家范用逝世一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