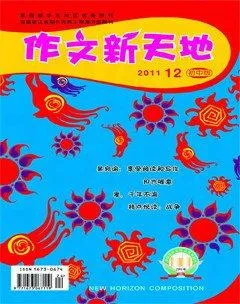維也納信使
那是在1945年的秋天,隨美國的第一批占領部隊,我再次來到維也納。我提前三個月來到那里,作為德語口譯官,參加一項談判任務,將那個城市分成四個聯軍占領區,就像之前在柏林進行過的那樣。我的德語很流利,因為我六年前才從柏林移民到美國——在美國我很快就符合條件參了軍,服務我的新國家并且為穿上他的軍裝而自豪。
一個周五晚上,我感到有些思鄉,便徑自走到維也納僅存的一座猶太人教堂去做禮拜。那兒有一群人看起來很可憐,大約五十個男女,面黃肌瘦,衣衫襤褸。他們說著口音很重的依地語,所以我猜他們是歐洲存活下來的猶太人,他們的種族原來繁榮興盛,現在卻被摒棄于此并且與世隔絕。瞧見我的美軍軍裝,他們全都圍過來歡迎這位來到教堂的友軍士兵。他們驚奇地發現,我居然能夠用流利的依地語跟他們談話。
隨著交談的深入,我可以判斷出自己原先的猜測是正確的。這些人是大屠殺的幸存者,他們聚集在教堂里是為了尋找是否有人知道自己的親人或朋友的消息。由于當時沒有從奧地利到世界各地的民用郵遞服務,這就是幸存者們用以打探親人音信的唯一機會。
一個男人膽怯地問我是否可以幫他將他的一封短信捎給倫敦的家人,告訴他們自己還活著。雖然我知道軍郵是不可民用的,但是我又能說些什么呢?這些人,實際上是從一座人間地獄活過來的,他們需要讓擔心的家人知道他們活下來了。我同意了,于是每個人請我替他們送信。
五十封信比起一封信多得多了:我在迅速思量著。往后退了退,我宣布說下一個周五晚上我還會來過禮拜并且收取短信,這些信要用英語、德語和依地語寫好并且信封不能封口。只要滿足這樣的條件,我都會用軍郵來發送。
第二周我信守諾言,再次來到那個猶太教堂。當我推開門的時候,那兒擠得水泄不通,所有的人都向我沖過來,將信扔給我。信太多了,我不得不請人找了一個箱子來裝。接下來我花費了一周的時間對信件進行安全檢查,確保里面只包含他們允諾的內容,然后將他們發往世界各地。我覺得棒極了,我知道這也許是那些人的大多數親戚們第一次得知他們所愛的人在大屠殺的恐怖中幸存了下來。這是一件好事,我認為,是一個小小的“義舉”。
大約一個月過去了,整件事已經從我的腦子里淡去,直到軍隊里的“信童”突然蹣跚著來到我的辦公室,滿懷抱著幾大袋的包裹。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詢問道。地上的包裹來自世界各地,都署名由我——阿諾德·杰爾下士——轉交給那些幸存者們。我沒有預料到這樣的結果。現在我應該怎么辦才好?
當天整個傍晚直到深夜,我和沃爾特——也曾是從德國來的一位流亡者——開車穿過維也納的滿街碎石,將郵包投給那些滿心驚喜和感激的幸存者們。
點評
戰火紛飛的年代里,也許一封信就是對那些千瘡百孔的心靈的極大的慰藉。正如文中所講,“這就是幸存者們用以打探親人音信的唯一機會”。這篇文章的一個成功之處在于它既沒有對戰爭場面的正面描寫,也沒有對英雄人物進行歌功頌德,有的只是默默無聞的普通人,但正是他們,讓我們透過慘絕人寰的戰爭感受到人間的溫暖,也讓那些身處絕望和痛苦邊緣的戰爭幸存者看到了生的希望。在無情的炮火和戰斗中閃爍著人性的光芒。在質樸的語言的背后,我們仿佛看到了一顆顆渴盼與親人團聚的心靈,質樸中飽含著深情。“一個男人膽怯地問我是否可以幫他將他的一封短信捎給倫敦的家人,告訴他們自己還活著”,“當我推開門的時候,我驚呆了。那兒擠得水泄不通,所有的人都向我沖過來”,諸如此類的語言發人深思、令人震撼。戰爭給無辜的民眾帶來了多少抹不去的傷痛和記憶!它的另一個成功之處在于用細節描寫打動人心:“思量著、退了退、推開門、驚呆了、沖過來”,這些詞語形象逼真地再現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巨大傷痛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