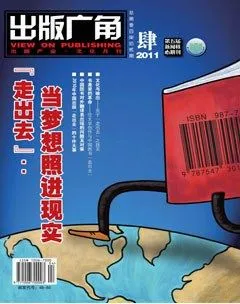盡享世外的寧靜\\和諧與安詳
《農歷》郭文斌 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 年10 月版定價:29.00 元
這不僅使得他在內心中依然獨享著一種世外的淳樸與浪漫,更重要的是,他在小說中所表現的其實更多是他的一種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是他對于人生最完美狀態的一種圖景化構建與訴求。
在上海這樣的喧囂繁鬧、競爭慘烈、生活節奏超快的國際化大都市,讀郭文斌的長篇小說《農歷》——這種完全唯美化的文學藝術作品顯得有點不合時宜。我邊讀邊一再想象著郭文斌的現實生活狀態。難道這個郭文斌就不是生活在當下充滿爭斗和欺詐的商業社會之中的嗎?莫非作家真的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真的可以獨自擺脫塵俗而身處世外桃源?一直讀到被小說名為《望》的附錄部分,我才明白郭文斌的確還是生活在現實之中的。他有著非常正常的現實生活、工作、家庭、妻兒……只不過,他的意識深處還牢固地保留著那種最遠古的田園牧歌的情境。這不僅使他在內心中依然獨享著一種世外的淳樸與浪漫,更重要的是,他在小說中所表現的其實更多是他的一種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是他對于人生最完美狀態的一種圖景化構建與訴求。
小說從人物塑造、情節設置到環境描摹,都極其簡潔單純。男女主人公五月、六月是一對涉世未深心地純真的少男少女。而小說的整體結構,則是由兩個小主人公在農歷一年中的重要節日里,按照傳統習俗進行紀念或者勞作時所發生的故事而組成。這樣的結構顯然體現了作者對于我國傳統文化秩序的留戀和崇尚。而這樣的一種完全依照自然時序生成的倫理秩序,又恰恰是他所理想的社會和諧安詳的深層結構性基礎。
就小說的主體內容而言,首先可以說是一部中國傳統節日民俗大全,或者起碼是我國西北一帶節日民俗的全景展現。其中嚴格按照天然時序,從作為舊年剛過,新年之初的元宵節,到作為年尾的大年,總kyRs5wRFmCvskmkwhkLUSw==共15個農歷的節日,小說以非常細膩明快的筆法,描寫和講述了這些節日中各種紀念的活動、程序以及步驟。而這些活動又都是以五月、六月這對姐弟的參與過程為線索展開,使得整個活動充滿人間情趣和俗世風情。
當然,小說對于西北民情風俗的表現,又絕不僅僅是簡單的、平面化的以及情景再現式的記敘和演示。其中更主要的還是對于我們民族悠久漫長的傳統文化之根之源的追溯與呈現。那些優美溫馨的民俗活動就如同是民族文化之樹之花;而傳統經典文化尤其是其中蘊含的充滿智慧和理想精神的思想觀念,則是其根。我們的民族生活中之所以能夠一直保留著那么程序嚴密萬世堅守的民俗活動,根本就在于我們民族文化的大樹一直都是根深葉茂,我們民族文化的精神,一直都在滋養著我們世世代代華夏子孫的心靈。如《清明》一章中寫五月、六月在集市買祭祀用紙,二人在選紙時極其用心和認真,因為他們內心有一種聲音:“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而當姐弟倆把這些傳統“家訓”和“家規”等等如同詩一樣的文字脫口背出的時候,不僅當即得到滿場喝彩,而且很多人愿意把紙送給他們,還邀請他們下次再來傳授他們的這些文化知識。這樣的情節不僅生動地表現出了我們的傳統文化精神后繼有人,而且尤其有著極其廣泛和深厚的社會群眾基礎。
此外,小說的藝術深度還在于,兩個混沌初開諸事懵懂的小主人公,在他們參與的所有活動以及他們的所見所聞中,總是不斷提出或者討論一些抽象性的、思辨性的、甚至帶有終極意義的各種問題。諸如:人是怎么來的?為什么有男人和女人?愛是什么?誠是什么?解放是什么?……很多時候,小主人公對于這些問題的追問和討論,甚至頗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之風,
如:
“草木為啥不能踩?六月問。
因為草木也是命?
啥叫命呢?
活著的都是命。
麥子活著嗎?
當然活著啊。
那它咋不說話?
它說呢,只是你聽不見。”
這樣的一些問題和回答,從一對乳臭未干的少年男女口中吐出,看上去也許顯得十分簡單和幼稚,可是,這些問題我們哪個人沒有疑問過的呢?而如果認真加以琢磨和掂量,這些問題當中,不也的確蘊含著非常值得追索和深入研究的問題嗎?其實這也正是小說采用返璞歸真的思維和筆法,引領讀者對于一些世界和人生的元問題以及本真問題的求索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