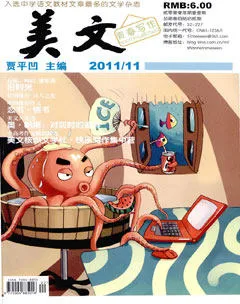突然想起你
動筆的一瞬間,才決定選擇第二人稱。桌角還攤著高考后一直沒有整理的筆記,上面說,第二人稱的作用是“抒情性與親切感,便于感情交流”。當時只認為是出題人牽強附會出來的固定答題模式,現在卻多少覺得有些道理。
因為相對于過于熟悉的“我”或者生硬的“他”而言,“你”這個稱謂,從來就不會產生距離感。
老班在黑板上寫下任課老師名單的時候,我正盯著上面陌生的名字發呆。你的名字出現的時候,我心里是著實“呀”了一聲的。與老楊的有口皆碑和老趙的毀譽參半不同,你在貼吧上的評價是出奇的一致:有意思。于是不由自主產生了無限的憧憬。
而對于傳說中很重要的第一面,我卻不得不慚愧地說抱歉。原本以為會念念不忘的細節最終還是被時間海漂白得模糊了容顏,只記得同桌那句“怎么長這樣”的滿是懊悔的抱怨。而那時我并不知道,這一粒不算飽滿的種子扎根在她的心里,在此后漫長的時光里會開出什么顏色的花來。
現在想來,你也確實不是想象中的英語老師的模樣。板寸頭,深眼窩,灰風衣下難掩略顯發福的身體和輕微的駝背,那一口帶了明顯地方口音的“南普”開場白亦讓初來乍到的我皺了眉頭,好感頓時大打折扣。
然而無數事實證明,“人不可貌相”這句話的真實性是不可動搖的。上課鈴一打響,你沒有像別的任課老師一本正經地介紹學科或者本人,而是轉身拿起粉筆,瀟灑地寫下自己的名字,又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揮筆寫下26個英文大小寫字母。我們盯著一黑板華麗的花體字,只停頓了一秒就報以熱烈的掌聲。
最后的結果是:一下課你就被捧著筆記本的同學團團圍住,爭先恐后地讓你在扉頁簽上字母。你也不客氣,拿了筆一個個地寫。從教室后窗的角度看過去,真是比大明星還大明星。
忘了是誰說過:一個驚喜并不意外,接二連三的驚喜才讓人期待。而你,無疑就是這種不斷制造驚喜的人。
先是第一節課就明確的人手一冊的單詞小本,到后來帶著罕見倫敦音的全英授課,還有課堂上妙語連珠的句子與層出不窮的單詞。我們逐漸習慣了你在講臺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眼睛一轉就來句“XX用英文怎么說”,然后在無數或崇拜或驚訝的目光中寫下對應的英文單詞,得意洋洋地在一片“唰唰”記錄聲里笑容爽朗。
而你,也從來不是被課本與教科書所束縛的人。薄薄一頁的單元單詞你輕而易舉擴展成兩三倍詞匯量的講解課,課文里的重點句型被肢解成各式新潮場景,就連練習中不起眼的短語在你眼中也宛若珍寶,常常讓前一秒還直呼“課本上沒有這個”的我們被下一秒找到出現位置的你辯得啞口無言。只好一萬倍的仔細加小心地研究教科書,卻還是掉進你隨處可見的陷阱里。
至于坊間傳聞的“監考時都在背誦牛津雙階”的邪乎的說法,我從最初的一笑了之倒戈成了忠實擁躉。也學會在沒有作業的課間向鄰班同學夸耀你的種種,自豪地宣告是你的學生,然后贏來一片羨慕的目光。
然而好戲才剛剛上演。
事情的發生有些突然。
每周六學校沒人道的補課,你一向深惡痛絕,卻無能為力,于是反抗的方式就變成了下午第一節課天南海北的神侃。從蠻荒時代的“physical label”到振臂高呼的“I’m confucius’ offspring”,夾雜著英文的評論層出不窮,倒也新鮮。
又是一個周六,你照例邁著四方步踱進了教室。我們都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你也并不在意,只是點中了當時坐在第一排的勞動委,象征性地提了幾個有關前幾天學的內容的問題。
彼時的他自然是好學生一輩,只是對個人形象不甚講究,高一那年說起他,浮現的定是胡子拉碴頭發如亂草的不羈形象。他卻接連幾個都沒有答對,無名之火“騰”地冒起,你不由分說嚷了一句:“XXX,你這什么樣子,我一眼就看個清楚!”然后數落著他的不修邊幅,小到個人修養大到婚姻幸福,我們笑著笑著卻逐漸發現了事情的不對勁。
最后怎樣收場我已記不清楚,過了周末卻驚訝地發現了煥然一新的勞動委,一改原先的邋遢形象,頭發熨帖地趴在那里,胡子也不見了蹤影,人一下子就清爽精神了許多。你卻像沒事人似的照講你的課,只是在目光偶爾瞟過他時閃過些許笑意。
幾年后,我讀到梁實秋先生的《我的一位國文老師》,念到那句“我一眼把你望到底!”的經典橋段,還是忍不住笑出聲來。
原來這么多年過去,老師這個行當,連臺詞都會一樣。
那年元旦晚會,你和老班合作的那曲《從頭再來》,在經歷了老班糟糕的忘詞和你張牙舞爪的表演之后,哭笑不得的我們最終記住的是你頗為迷人的嗓音。于是在“每日一歌”時,我們專挑了你的課前來唱《Take me to your heart》,然后起哄讓你來一曲。不曾想你也不忸怩,站在講臺上深情地跟著伴奏唱了起來。陽光微醺的午后,樹影斑駁的講臺,你深沉的男中音與微閉的雙眼,還有同桌一臉陶醉的表情,每每想起這些,我都忍不住彎起了嘴角。
可惜插曲終歸是插曲,高中的學習仍然是王道。高一下學期的課程,在起初的新鮮與好奇之后,逐漸顯出了真正的復雜與枯燥。你卻依然故我,在課堂上延續著喧鬧與搞怪,將本來就活潑的英語課發揮得淋漓盡致。看見講臺上眉飛色舞的你,我也逐漸相信,原來有的人,真的單純是為老師而生。他們不是學術精英,整日埋在書山題海中寫出一篇篇傲人的論文;他們不是領導骨干,在各種報告與會議之間長袖善舞游刃有余。他們只是普通的老師,站在三尺講臺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傳遞著“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的真諦。
高一的最后,我們都習慣了你出其不意的課堂聽寫與更加出其不意的揭曉答案。于是有了“我們有請這邊的XXX”“有請那邊的某某”的響遍全班的點名,有了“看到妖怪舉著把雨傘時我們都害怕地屏住了呼吸”抑或“我同桌重色輕友,一看到美女就不理我”的讓人噴飯的嵌入各種短語的漢譯英聽寫,有了“得單詞者得高分,得完型者得天下”的諄諄教誨。我手機現在還保留著當時偷拍你的照片,表情夸張而痛心,嘴半張,一看就是我們聽寫錯誤后你甕聲甕氣的“柴死了!”的抱怨。以至于如今懷念起那段歲月,還會感謝學業重壓下這一份關于英語難得的溫暖與美好。
而那首許諾過的《 As long as you love me》,在我們無數次的抗議與要求之下終于成了一句“下個學期再說”的將來時。后來才懂得所謂的諾言是最經不起推敲的虛擬語氣。我有時想,那個時候的你,會不會已經未卜先知,預測到接下來的種種,才會給我們一個并不算明確的期待?
得知你要離開,是高一的暑假。當時的第一反應,只是覺得所謂課程太過繁重任務太過緊張都不過是學校自欺欺人的借口,而正常的工作變動之下當然不會太過考慮我們的感受。給同桌打電話,遲遲地沒有回音,卻在看完她回的“之前的半個小時我已經成功把枕頭洗了”之后不禁莞爾。真可惜,到現在你也許還不曾了解她當時的小心思。課堂上一絲不茍的筆記,問過題之后不曾消退的臉紅,宛若夢囈的“我們家奇奇”的絮叨,還有除夕夜反復構思了多遍都沒有勇氣發出去的祝福短信。只有在拿到漂亮分數時,她才會羞赧地在你背后笑起來。
其實坦白來講,后來的英語老師倒符合期待中的模樣。一襲拖到腳踝的黑色長袍,黑色的齊肩卷發,總讓我生出英國女巫的錯覺。卻還是忍不住在聽到樓上的歡聲笑語的時候,想起原本屬于自己的一切,想起那個樹影斑駁的午后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美好瞬間。
最痛苦的不是不曾擁有,而是擁有過后再度失去。
后來在食堂遇見過你,你總不免勸誡幾句“注意飲食”;偶爾還會在學校的林蔭道上邂逅騎著小自行車鍛煉的你,車座吱吱呀呀的,一副不堪重負的病態;大清早起來,卻再也沒有見過你穿著背心,自顧自地在籃球場上玩得不亦樂乎。
朋友說,一次在操場上遇見你,興高采烈地上前打招呼,你寒暄之后樂呵呵地來了句:“你是哪個班的?”我只當個笑話聽了去,卻從不愿承認其中分明存在的真實性。
其實遺憾又何止這些呢?照畢業照的那天,你錯了過去,那張珍貴的相片上終究沒能留下你慘白的貝齒;記下手機號碼的時候,鬼使神差地抄錯了數字,我在數次的“發送錯誤報告”之后才發現是空號;即將開學的秋季,你被安排到了復讀班,紅磚的四層教學樓里再也見不到你健步如飛的身影。
就連那個傷感的暑假,我信誓旦旦地對同桌許諾要寫篇文章紀念你,最終也只是一個沒有結局的草草開頭而已。
張小嫻說,離別與重逢,是人生不斷上演的戲,習慣了,也就不再悲愴。
你是早就懂得的吧!
懂得離別的意義。所以才選擇忘記與釋然。
因為就像你第一節課說的那樣,所謂離別,不過是為了更好地開始。
直到此刻,在鍵盤上敲擊有聲的時候,我依然不明白自己寫下這些文字的原因。
如果一定要有理由,大概就是尊敬吧。
教師這個職業,從來都不是簡單的“教書育人”就可以概括得了的。你們就像麥田里孤獨守望的稻草人,每年仰望無數候鳥從頭頂飛過,在等到屬于你的群落時,傾盡所有和他們交談,卻并不期許他們究竟會理解多少。你會在當時認得這只的羽色,記得那只的聲音,然后微笑目送他們遠離,飛向更高遠的天空。卻在來年更多的候鳥之間迷失了視線,逐漸將無數面孔重疊,只記得當年的鮮衣怒馬,卻忘了歲月流逝中自己蒼老的容顏。
就這樣,在這個寂靜的午夜——
突然想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