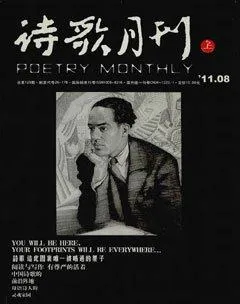聶魯達的“詩人形象”在中國
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 1904—1973)是拉美文學史上繼現代主義之后崛起的又一高峰。由于“他的詩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復蘇了一個大陸的命運與夢想”,聶魯達于1971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在《西方正典》中哈羅德·布魯姆將聶魯達與博爾赫斯、佩索阿作為西班牙語美洲文學經典的代表人物,稱他們為“西葡語系的惠特曼”。而1949年以來當代中國對聶魯達接受和其“詩人形象”的塑造過程則顯得復雜多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聶魯達成為考察當代中國復雜的政治文化場閾和文學接受語境的晴雨表。總而言之,聶魯達在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接受過程中充滿了變化且從文學史、社會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面反映了當代中國的特殊狀況,所以多側面、立體地研究當代中國對聶魯達的文學接受狀況、反思當代中國文學接受的語境、特點以及存在的問題就尤為重要。顯然當代中國不同時期對聶魯達的具有差異性的接受與傳播乃至詩人形象的塑造,不同時期的政治、文化、文學語境以及讀者的接受是密切相關的。在此意義上每個時代的讀者包括翻譯者和被翻譯者都是被“規訓”和設定出來的。而從讀者的角度而言上個世紀50~70年代和80年代之后顯然是具有相當大的差別的兩個時期,政治年代的讀者被灌輸的是政治的文學,而不受政治禁忌的文學時代讀者需要的則是更為多元化的文學。盡管特雷·伊格爾頓強調文學接受主要決定于文學作品本身的構成,而文學作品的每一部分的構成都暗示著它所期待的那種接受者。但是不同時期、不同時代的讀者在同樣的文學作品中所能夠閱讀、接受的部分都不可能是完全自主的,而是會程度不同的受到當時的社會和文學接受語境的影響。回顧半個多世紀以來聶魯達在當代中國的接受,無論是國家主流話語的塑造,官方刊物和媒體的傳播與譯介,還是更為寬松的政治和文學語境下對聶魯達的接受,我們都能夠更為清晰地看到這種接受的過程同時也是過濾和重新塑造的過程。而不論是政治年代的政治詩人,還是在現代性美學的張揚和大眾文化的視閾中的愛情歌者與傳奇詩人的形象,都印證了文學的接受與傳播過程由于顯豁或隱在的諸多復雜因素的影響而導致的文學形象的偏頗與變形。而這種接受和塑造過程中的偏頗與變形,詩人的經典化或者去經典化的過程都呈現了當代中國文化和文學語境尷尬的變動性特征。
縱觀當代中國對聶魯達的接受與塑造以及聶魯達文學形象在不同時期的變動,我們要追問的是,聶魯達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詩人?是“政治詩人”、“人民詩人”,還是“愛情歌者”與“傳奇詩人”?對于聶魯達而言,“西方世界的讀者,大抵比較喜歡他的抒情詩,而東方的讀者則更欣賞他的政治詩。歷來關于聶魯達評價的爭論,基本上便是從這兩種觀點出發的”①,而事實證明聶魯達的文學形象是相當豐富的。除了人們熟知的政治詩和愛情詩之外,聶魯達后期對生命、生存、自然的帶有哲理性的沉思詩作同樣值得重視。應該說聶魯達的文學世界正像是一個多側面的棱鏡,相當復雜并不斷變化。而回溯半個多世紀中國對聶魯達的文學接受過程,我們看到的是遺憾與偏頗。顯然當代中國對聶魯達的接受與塑造使得聶魯達的文學形象不斷發生位移與變化,甚至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影響,聶魯達長時期地被貼上了政治詩人和愛情詩人的標簽。無論是政治年代的政治詩人的塑造,還是在多元文化語境下的愛情詩人、傳奇詩人的塑造,聶魯達這位豐富多變的詩人形象都不斷地被單一化了,他的豐富性,例如滾燙的革命熱情、愛情欲望、故鄉情結、自由精神、哲理反思、人文情懷、知識分子的良知以及語言天賦、詩歌技藝等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忽略。聶魯達的詩歌話語譜系既有愛情詩、政治抒情詩,又有晚期在《元素的頌歌》、《元素的新頌歌》、《頌歌第三集》等詩集中大量的向自然宇宙、日常事物的致敬與探向內心深處的沉思,顯現出詩人在時間的無情流逝中本體性的關于生命、死亡的哲理性省思以及難以擺脫的宿命性喟嘆,昭示出另一種冷靜的哲學家的精神。基于此,首先應該確認聶魯達不是一個單一的政治詩人或愛情歌者,而是一個多側面的立體詩人。
縱觀當代中國對聶魯達的接受與塑造,以及聶魯達文學形象在不同時期的變動,我們要重新審視和剖析聶魯達的政治詩人和愛情歌者以及傳奇詩人的形象。我們要追問的是聶魯達是如何從一個政治詩人被轉換為愛情歌者、傳奇詩人的?聶魯達在不同時期的接受與塑造中其形象被單一化、刻板化背后的社會、政治文化、文學語境、媒介文化、接受者等到底起到了怎樣的影響?既然聶魯達是一個如此豐富多變的詩人,那么為什么在當代中國對聶魯達的接受過程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聶魯達的文學形象不斷發生變化甚至被反復的單一化和窄化呢?
“政治詩人”形象的確立與傳播
建國后三十余年的時間里關于聶魯達的研究主要是袁水拍、蔡其矯、艾青、蕭三、郭小川、郭沫若、鄒絳、徐遲、周而復、萬光等人在譯介聶魯達,以及與其交往的過程中所撰寫的文集序言、短論及散文性的回憶文章。此外就是當時的《詩刊》、《人民日報》、《譯文》、《光明日報》、《紅巖》、《延河》、《文藝報》、《讀書》、《世界文學》、《世界知識》等報刊對聶魯達詩歌和詩論的譯介,并且這種譯介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這些文章多限于當時國內政治文化語境和國際形勢,更多從政治、革命、階級的角度對聶魯達的身份、詩歌、詩論、散文予以評價,而聶魯達也因此成為國際和平衛士、政治抒情詩人和革命詩人的形象,甚至在更多的時候聶魯達被中國文學界塑造成了一個具有政治家和革命家身份的詩人形象。
1952年,著名的詩人艾青的《和平書簡——致巴勃羅·聶魯達》顯然就是從當時智利國內的政治情況以及國際政治形勢的角度出發,把聶魯達塑造成了美洲大陸上一個高大的為自由、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爭的英雄形象。而在國外,尤其是在蘇聯和亞非拉國家,從上個世紀40年代一直到80年代,由于相似的政治文化環境和國家意識形態以及文學觀念的相近,關于聶魯達的譯介和研究狀況與中國大體相似。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文本是蘇聯作家庫契希奇科娃和施契因合著的《巴勃羅·聶魯達傳》(胡冰、李未青譯,作家出版社,1957年),在這第一本關于聶魯達的傳記作品中,聶魯達的政治身份和政治經歷是被反復強調的,從而塑造了他政治詩人和民主戰士的形象。而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與聶魯達的交往與中國的艾青與聶魯達的交往也極其相似,具體情況可參見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的相關描述。聶魯達在1950年代的兩次中國之行(包括多次的蘇聯之行)在當時甚至很長時期看來都被賦予了文學之外的政治寓意。而1960年代初期,聶魯達和古巴的交往、對古巴人民斗爭的支持以及詩歌歌頌都影響到了中國對聶魯達的積極接受與傳播,聶魯達的詩作被后來對中國影響相當大的古巴革命領袖切·格瓦拉譜成歌曲。實際上,無論是中國還是蘇聯在上個世紀50~70年代對聶魯達的接受與塑造都首先是出于政治意識形態上的考慮。建國后對聶魯達的詩歌接受主要是出于政治意識形態以及社會主義文藝建設和發展的考慮,那么從這一點上聶魯達的政治性強烈的詩歌,或者說寬泛意義上的政治抒情詩被大量的譯介就是最為合理的時代需要了。聶魯達是在建國初期作為“政治詩人”形象被大力譯介的拉美詩人。1950年代,重要的報刊《詩刊》、《人民日報》、《文藝報》、《譯文》、《光明日報》、《紅巖》、《延河》等都刊載過聶魯達的詩歌和詩論,并把聶魯達看作是偉大的“和平斗士”。實際上這一時期強大的政治選擇性和意識形態性決定了文學接受和文學過濾是極其嚴格、狹窄甚至“畸形”的,因此,聶魯達在這一時期的文學接受過程中被塑造成了“政治詩人”的形象。
作家的接受與傳播不僅與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文學環境密切相關,而且文學刊物、大學教育、文學史寫作、教材編寫、詩歌選本等因素都對作家的接受和傳播甚至經典化的過程都是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而在上個世紀50~60年代中國對聶魯達的接受與傳播過程中,在日漸緊張的政治年代,作為主流刊物的官方樣板刊物《詩刊》以特有的詩歌生產和傳播方式對蘇聯和亞非、拉美等進步國家詩人和詩歌作品的大力推介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政治作用。而在對外國詩人的接受過程中,《詩刊》以相當大的篇幅和力度介紹聶魯達,以其不可替代的官方重要的國家級刊物的影響肯定和確立了聶魯達“政治詩人”的文學形象,而與此同時也過濾掉了聶魯達詩歌寫作的豐富性。
英國學者邁克奈爾認為在現代社會政治進程中,大眾媒介是介于政治組織和公民之間的第三個要素。在此前提下,媒介的傳播過程就是有選擇性和傾向性的,這樣,媒介在政治年代就更大程度上成為政治訊息的傳播者,并且其本身參與了政治文化的構建。就中國而言,上個世紀50~70年代,政治運動的媒介傳播主要是紙質報刊和電臺廣播,這一時期形成了以《人民日報》、新華通訊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有線廣播站)為核心的集中統一的媒介傳播網絡。這一時期的媒介傳播網絡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政治宣傳和文化教育。因此,聶魯達的文學形象的塑造與傳播也只能限定在極其嚴格的政治層面。《詩刊》在從1957年創刊到1964年因為政治和社會原因停刊的這段時期,基于其與國家領導人的特殊關系和其相當重要的媒介地位,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詩歌尤其是亞非拉社會主義國家的詩歌的譯介和傳播,特別是對聶魯達文學形象的塑造與確立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詩刊》作為建國后相當重要的詩歌刊物對塑造聶魯達“人民詩人”的文學形象起到了推動作用,而《詩刊》如此集中而大量的發表聶魯達的詩作、詩論以及相關的評論文章是值得重視的詩歌史現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詩刊》創刊號除了發表毛澤東的舊體詩詞十八首和毛澤東《關于詩的一封信》外,用了相當多的篇幅刊登聶魯達的兩首詩《國際縱隊來到馬德里》(袁水拍譯)、《我的祖國是春天》(戈寶權譯)并配有聶魯達的照片。這也拉開了《詩刊》推薦和宣傳聶魯達的詩歌、詩論、散文和演講報告的序幕。《詩刊》1957年8月號發表袁水拍翻譯的聶魯達的詩作《中國大地之歌》。同年9月號《詩刊》發表聶魯達的《詩和人民》。《詩和人民》是1957年8月15日聶魯達在中國作家協會、詩刊社和北京文聯為歡迎聶魯達等4位智利詩人的詩歌朗誦會上所做的演講,同時會上聶魯達朗誦了自己發表在《詩刊》上的《中國大地之歌》。在《詩和人民》這篇演講中,聶魯達強調詩歌和人民的關系,認為詩人和群眾接觸是很重要的,指出一個詩人不能忘記本國人民斗爭是詩人應有的責任,“如果一個詩人他對人民沒有責任感,就寫不出任何好詩來”。可見,聶魯達關于詩人與人民和現實關系的論述與當時中國國內的文藝觀念完全一致,所以能夠被反復的肯定和評價就是常理之中的事情。而正是這篇名為《詩和人民》的演講使得中國的文學界將聶魯達看作是“人民詩人”的代表。但是值得注意的卻是1957年9月號《詩刊》所刊發的聶魯達的演講《詩和人民》正值反右運動的高潮期,而有意味的是聶魯達除了強調詩人在任何時代和人民的密切關系外,還提出了當時反右運動不可能接受的文藝觀點,即聶魯達強調詩人除了寫政治和斗爭題材外還應該寫愛情詩。但是聶魯達的這種可貴的對詩人責任的忠告(既要寫政治、人民,也要寫愛情、自然)卻被當時中國的詩人、雜志和讀者所忽略和過濾掉了。在當時的政治文化語境和偏狹、僵化的文藝觀念下,中國文學和詩歌界是絕對不可能接受聶魯達關于愛情詩的寫作觀念,因為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之下,寫作愛情詩已經成了最大的禁忌,所以,在長時期內,聶魯達的愛情詩的傳播在中國成了空白。
由于眾所周知的政治文化的影響,當代中國對國外詩歌和文學的接受,無論是從其國界范圍還是在政治意識形態美學的取舍上都是相當狹隘甚至階級化的。建國后30年的時間里,中國對外國文學的接受更多是一種以政治意識形態和階級文學作為取舍的唯一標準的過程,所以在建國后,只有蘇聯、拉美和亞非的一些帶有社會主義特征的文學得以譯介與傳播。在政治化的接受視野中,聶魯達被簡化為“政治詩人”與“人民詩人”。而隨著1965年中蘇關系的惡化,拉美左翼也分為了親蘇派和親中派,親蘇派的拉美文學不再被翻譯。而在更為激進的左傾化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對外國文學的接受幾乎成為一片空白,只有少量的“黃皮書”和“灰皮書”在極小的范圍內秘密流傳,而即使是經過過濾的政治詩人以及和平戰士角色的聶魯達也是作為蘇修主義者被禁止提及和傳播,“1955年和1957年,聶魯達來京。但是不料后來聶魯達也蒙上了不白之冤,他的作品再也沒有介紹到中國來過。直到最近幾年,我們的文學刊物上才重新出現他的名字”。聶魯達在當代中國所經歷的由接受到禁閉,再由禁閉到再接受的過程具有說服力地呈現了這一時期接受語境的復雜多變。在逐漸加劇的極左路線的政治文化語境之下,中國對西方文學的態度是二元對立的。在所謂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文學和西方資產階級文學的空前緊張的矛盾沖突中,西方文學更多被視為落后、反動的資產階級文藝形態而被批判與否定。而與此相應,亞非、拉美國家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和現實主義特征的文學作品則被視為有力的戰斗武器而被大力譯介。顯然,建國后當代中國在不同時期對聶魯達具有差異性的接受與不同時期的政治文化和文學語境甚至讀者群都密切相關。反過來這些被規訓出來的接受者又以共同的閱讀期待視野和標準來篩選和評價被接受者。基于此,在上個世紀50~70年代文學翻譯和接受嚴苛的過濾和篩選過程中,聶魯達這位“政治抒情詩人”的愛情詩就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中國讀者的閱讀視野之外。
從“政治詩人”到“愛情歌者”、“愛欲詩人”
在長期的文藝接受和傳播的狹隘的文藝觀念和強烈的意識形態影響之下,聶魯達豐富、多元的詩歌成就不能不被過濾和刪減掉,而聶魯達的人民詩人、政治詩人的這種刻板印象只有到了1980年代后期以來才發生了轉變。當代中國對聶魯達的接受過程不斷發生變化,綜而言之經歷了政治詩人、愛情歌者和傳奇詩人的三個過程,但事實上聶魯達的文學形象要遠比這更為復雜。
隨著極端政治年代的結束,文學接受與傳播也開始在早春的天氣里出現“解凍”,聶魯達的接受與研究在經過1960年代后期以來的長期沉寂后,隨著1980年代以來的政治文化語境以及文學研究語境的轉換,中國重新掀起了關于聶魯達的文學熱潮。但是即使到了1980年代,聶魯達重新進入中國讀者和詩人的視野,但是在不短的時間聶魯達仍被認為是政治詩人、革命詩人、人民詩人,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抒情詩人。當時很多的外國文學史寫作都大抵如此。而隨著1980年代文學觀念和文學研究范式的轉換,尤其是1986年以來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中對文學性和美學性的空前強調都使得聶魯達不再是作為單純甚至庸俗化了的政治詩人形象被接受和傳播。聶魯達作為愛情詩人以及現代主義特征的詩人一面被逐漸挖掘出來。自此聶魯達的“政治詩人”形象逐漸邊緣化,而其愛情歌者的形象則占據了主導地位。在對現代主義文學的大力強調和文學本體性張揚的詩學觀念之下,聶魯達的翻譯和接受不再是作為一個政治詩人和所謂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詩人,而是作為一個現代主義詩人和愛情詩人而出現的。在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對拉美文學的譯介主要是對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學的接受,而在對智利文學的接受過程中,聶魯達和米斯特拉爾這兩位曾經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成了被重點譯介的詩人。從1980年代開始隨著文學和政治文化語境的逐步寬松,聶魯達的愛情詩開始被小范圍的譯介,聶魯達的文學形象也隨之發生改變。但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雖然譯介了一些聶魯達的愛情詩,但是他一些頗負盛名的愛情詩篇卻被當作“不健康”作品而舍棄。翻譯者仍認為這些“情詩”無助于意識形態的建構,而其中包含的“小資情調”則被認為是會腐蝕人民的不健康的東西。換言之1980年代的文學和政治文化語境盡管較之此前嚴酷的政治年代有了相當大的轉變并逐步走向自由和寬松,但是這種自由和寬松仍然是被限定在一定范圍之內的,而聶魯達的愛情詩歌被有限度的介紹與翻譯就很具有代表性。1980年代初期,陳舊、僵化的文學觀念依然盛行,譯者也不得不在作品的選擇上小心翼翼。
在當代中國對聶魯達的接受過程中,聶魯達在很長的時期內是被認定為政治詩人的。這不僅在于聶魯達寫作過大量的政治題材的詩作,還在于聶魯達在大量的散文以及演講和訪談中不斷強調詩人的政治性和社會屬性。由于聶魯達特殊的性格、身份、經歷以及智利國內特殊的政治環境,在聶魯達的詩歌文本中,政治抒情詩和愛情題材的詩作占有著相當的比重,所以這也給讀者和研究者們留下了兩個重要的文學形象——“政治詩人”和“愛情歌者”。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聶魯達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詩人,也是一個偉大的愛情詩人,這都是不爭的事實。政治和愛情成了聶魯達詩歌的兩個翅膀。從讀者的角度,以聶魯達的愛情詩為例,尤其是他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和《一百首愛情十四行詩》的影響,無論是在智利、拉美還是在世界上都有著相當數量的追捧者。以西班牙語版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為例,在1961年其銷量就已突破了一百萬冊,而現在全世界的銷量則已經超過了1億冊,這個數字在中外出版史上都是相當罕見的。而聶魯達的很多愛情詩作往往是與其歌頌的生命、自然、民族、革命和政治相當復雜地連接在一起的,不是單純的革命,更非簡單的情欲。這在他的《船長的歌》、《一百首愛情十四行詩》、《葡萄與風》、《狂歌集》甚至長達15000行的長詩《漫歌》(有譯者譯為《詩歌總集》)中都有鮮明的體現。聶魯達對女性的愛是與大地、自然、人類解放、政治生活、民族革命、自由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這種融合有時候強調的重點不同,有時是政治情結濃烈一些,有時則是傾向于濃烈的異性之愛。同樣不可忽視的是,聶魯達寫作了大量的、優秀的政治抒情詩和長篇史詩。在中國半個多世紀的對聶魯達斷斷續續的接受過程中,聶魯達成了一個被貼上政治標簽和愛情標簽的詩人,換言之,在不同時期的對聶魯達的“政治詩人”或“愛情歌者”形象的塑造與強化過程中,他的豐富性被不斷遺漏了。而聶魯達關于愛情和欲望的詩作更能有力地呈現人類作為生命的宿命、悖論、荒謬的一面,其間也彰顯出對社會生活現象的不滿與抗議、贊頌與反諷、平實與夸張都極其富有張力的糾纏在一起,從而呈現了聶魯達繁復的詩歌美學特征和深邃的關于人性、命運、社會、彼岸的思考甚至批判意識。
聶魯達詩歌中有數量不少的對身體的贊頌。而對身體的崇拜,原本是古老人類文明的偉大而自由的傳統,在古奧林匹克運動場上,人們赤裸著雄健的身體走向競技場,展示力與美。身體成為人類早期確證自我、征服外在力量的實體性存在,身體也成為人類生存的最終秘密的合理性依據之一。然而在中世紀神權壓倒了人欲,禁欲遏制了身體。在偉大的文藝復興時期,身體形象和身體的尊重再次作為人的自覺和自由權利被文學藝術所盡情謳歌與贊詠。尼采在他的時代用“上帝死了”的懷疑精神引領了此后人們對權威和禁忌進行挑戰與反撥,而伴隨著機械復制時代的來臨,后工業時代發達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日益強大,身體與靈魂,欲望與禁忌的二元對立狀態的城堡土崩瓦解。弗洛伊德旨在強調性原始本能快樂原則的精神分析成了人們重新認識自我、身體和欲望的合理性、合法化的旗幟和宗教。福柯和馬爾庫塞對性話語和身體快樂的不無精彩而獨到的分析似乎都確認了身體的合法化,也正式開啟了身體在藝術和詩歌中的合理依據途徑和一個嶄新的時代的到來。而歌頌帶電的肉體的惠特曼和寫作情詩的聶魯達更是在中國1980年代以來的詩歌接受中成為被摹寫的大師和偶像。中國詩歌歷來是倚重“詩言志”(此處的“志”已經完全被扭曲和非人性化了)傳統的,從此身體的切實存在和身體對自身和外物的感知被強大而虛無的規范所遮蔽、消隱。“身體”范疇所涉及的并非是簡單的肉體的快感,而是人的情感、欲望、快感、力比多、荷爾蒙、無意識、潛意識的綜合所指,它最終指涉于理性的反叛和作為社會主體性的人的最后解放,但是也不可否認,身體最終無力、也無法掙脫解放過程中文化傳統的巨大力量的牽制與羈絆。比照西方,中國文化一直延續著蔑視身體,輕視生命的巨大傳統,當1980年代之后人們企圖打破這個傳統禁忌,并讓身體在詩歌和文學中合法化并且有所作為決非一件易事。這也許正是關于身體的敘事在詩歌和文學寫作出現的歷史價值和時代意義,因為任何有良知的作家都不應該忽視和漠視中國壓抑身體和蔑視身體的文化傳統對文學的反復戕害。身體在20世紀的社會革命與文學革命的雙重否定和忽略中成了人類個體最慘痛的事實。詩人在由知識分子向工農兵大眾的轉換中喪失了個體主體性和最基本的身體體驗和身體性存在,詩人喪失了自我,真實的身體感受和欲望成為時代和文學的雙重虛妄。我們不能不面對這樣一個令人瞠目驚心的事實——我們每個個體都擁有的自由的自己,寫作時賴以感受、憑借,以及最終要抵達的身體,卻在長期的非正常化的政治運動和文學藝術創造過程中被宣布為非法化。很難想象,如果一個活的、經驗的身體不存在,寫作將如何真實地進行?在中國,身體在日常生活和文學中的長期遭壓抑的狀態導致人們對身體妖魔化的偏見,當上個世紀80年代在女性和男性詩人們(當然更有小說家等)一起舉起身體寫作的旗幟展開遲到的解放身體和追尋自由權利的時候,真是一件令人振奮和高興的事情。但事情也并非如此簡單。就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而言,長期非正常化的政治文化和道德規范的禁忌以及與之相關的偏狹文學觀念,使得真正的、健全的“身體”在文學寫作中幾乎是空白,而相應的文學接受和譯介也無不如此。只有在1980年代之后,“身體”才漸漸在文學中獲得久違的合法性身份,像卡明斯這樣的美國詩人才有可能走進中國詩人和讀者的視野,如他的那首《我喜歡我的身體》:“我喜歡我的身體,當它和你的/在一起。它是如此全新。/ 肌肉更有力,神經更活躍。/ 我喜歡你的身體。喜歡它做的一切,/ 喜歡它的種種方式。我喜歡觸摸你身體的脊 / 及其骨骼,喜歡那種/戰栗結實柔滑,以及我將 / 一再而再親吻的/地方,我喜歡吻各種各樣的你,/ 我喜歡——緩慢撫摩——你帶電的毛坯上——令人振顫的茸毛——還有開裂的肉體上 / 出現的東西……眼睛是大片的愛情面包屑,// 或許我就喜歡我下面你的顫栗 // 如此全新的你。”毫無疑問,“身體”在文學寫作中成了一個政治文化和國家革命神話中的道德禁忌與倫理暗礁。經歷長期的社會和文學革命,身體重新進入文學和詩歌并非就是一個讓人彈冠相慶的事情。不容否認的是,身體重新進入文學和詩歌寫作中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標志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雖然譯介了一些聶魯達的愛情詩,但是他頗負盛名的情愛詩篇卻被當作“不健康”的作品而舍棄”②。1983年鄒絳、蔡其矯等翻譯的《聶魯達詩選》開始對詩人的愛情詩有所關注,這本書中譯介了詩人的第六首和第二十首情詩,而第六首也是流傳最廣的一首。為什么這一首能被當時的人們所接受呢?先來看一下這首詩:“我記得你去秋的神情。/ 你帶著灰色貝雷帽,心緒平靜。/ 黃昏的火苗在你眼中閃耀。/ 樹葉在你心靈的水面飄落。// 你向藤枝依偎在我的懷里,/ 葉子傾聽你緩慢安詳的聲音。/ 迷惘的篝火,我的渴望在燃燒。/ 甜蜜的藍風信子在我心靈盤繞。// 我感覺你的眼睛在漫游,秋天很遙遠:/灰色的貝雷帽、呢喃的鳥語、寧靜的心房,/ 那時我深切渴望飛向的地方,/ 我歡樂的親吻灼熱地印上// 在船上瞭望天空。從山崗遠眺田野。/ 你的回憶是亮光、是煙云、是一池凈水!/ 傍晚的紅霞在你眼睛深處燃燒。/ 秋天的枯葉在你心靈里旋舞。”這首詩相對于第一首就要含蓄得多,盡管也出現了“親吻”的字眼,但更多的是一種心靈的交流,而這正好符合中國人傳統的關于情愛的含蓄表述的審美要求。1987年5月出版的由袁水拍、王央樂合譯的《詩與頌歌》盡管也收入了聶魯達的政治抒情詩,如《伐木者,醒來吧!》、《懷念智利的頌歌》,但是20首愛情詩作顯然占了相當的比重。《詩與頌歌》開篇就是《愛情的詩》(第一首)這樣一首在當時具有挑戰性的關于身體和情愛的詩作,“女人的肉體,潔白的山峰,潔白的腿,/ 你以委身的姿態呈現給世界。/ 我這粗壯勞動者的身體挖掘著你 / 使得兒女從大地的深處跳出”。袁水拍、王央樂在《詩與頌歌》中選譯聶魯達的10首愛情詩是相當可貴的,可以想象在1949~1978年間極端的政治文化語境下,在罕見而變態的禁欲式的革命斗爭和文藝批判運動中聶魯達的愛情詩中關于身體的鋪陳與比喻,如“肌膚的肉體,苔蘚的肉體,貪婪而堅實的奶汁的肉體”,“胸脯的杯子”、“思念的雙腿”、“腹部的玫瑰”等這些“情色修辭”是不可能被接受和傳播的。聶魯達的《愛情的十四行詩百首》大量使用自然意象來隱喻女性的身體——“她”是大地,是果樹,是飽滿的蘋果和芬芳的泥土;“她”是麥子、樹、沙子、木頭、布、琥珀、瑪瑙,是河流、村落、桃子、酒窖、月亮所揉制的面包;“她”赤裸的身體是蘋果的小徑,是纖細如赤裸的麥粒,是遼闊澄黃如夏日流連于金色的教堂,是蔚藍如古巴的夜色,是湍急的水流自雪下滴落,是糾纏的藤蔓所統領的丘陵,是荒涼的銀灰色大草原。就詩歌文本而言,聶魯達的一些愛情詩對“性”和“身體”的抒寫程度現在看來仍是令人瞠目的。聶魯達為人稱道的愛情詩有人卻認為不如稱其為“性”詩更準確,因為當年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最初的名字就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詩》。當然,聶魯達這部在1961年銷售就達百萬冊之巨的詩集也曾長時間被出版社和評論者所不容,《女人的肉體》、《你一絲不掛》、《豐滿的女人》、《你的乳房》更是遭到長時期的批判。但是在1990年代后期以來的接受環境中,更多的讀者和研究者除了接受就是贊賞,“女人的肉體,雪白的山丘,雪白的大腿……肌膚的肉體,苔蘚的肉體,熱切而結實的奶汁的肉體。/ 啊——乳房的酒杯!啊——迷茫的雙眼!/ 啊——恥骨的玫瑰!啊——你遲緩而悲哀的聲音”(《女人的肉體》);“一個吻接一個吻我漫游于你小小的無限,/ 你的邊境,你的河流,你的微型村莊,/ 而一團快樂的、變形的生殖器之火 / 滑過了窄窄的血道”(《豐滿的女人》)。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03年前后推出了“20世紀世界詩歌譯叢”,這套詩歌譯叢由于翻譯的規模、數量,翻譯者的較高水準和出版社的大力推動已經在學界引起了相當廣泛的關注。其中由香港詩人黃燦然翻譯的《聶魯達詩選》則呈現給中國讀者的聶魯達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愛情詩人”。正如該書的封底上所宣揚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是聶魯達最早、最著名和最暢銷的詩集,它與他后期的《一百首愛情十四行詩》在南美家喻戶曉,影響深遠,并突顯聶魯達首先是一位愛情詩人這一基本事實”。顯然由黃燦然翻譯的這部《聶魯達詩選》是要“還原”聶魯達“肉感”的“愛情詩人”這一事實。黃燦然強調《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就是關于“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詩”,是關于性與愛的詩集,“這也許是它的真正魅力,因此它更接近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的關系的本質”,而譯者更為煽情地渲染了肉體和性在聶魯達這些詩歌中的重要性,“它更像一組鏡頭:中近景(女人的肉體)、遠景(雪白的山丘)、特寫(雪白的大腿)。它在‘肉體’與‘大腿’之間插入‘山丘’——這是我所遇見到的最具震撼力的隱喻之一”。而值得注意的是黃燦然翻譯的這部《聶魯達詩選》的內頁,每頁的右上角位置都有一幅同樣的插圖,樹下的一對摟抱在一起相互撫摸的青年男女。
通過以上譯介的聶魯達的詩選,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聶魯達的愛情詩在1980年代以來開始被接受與傳播。甚至隨著文學和社會語境的轉換,聶魯達的愛情詩受到了越來越普遍的重視,其“愛情歌者”的形象也逐漸顯現。而1980年代中期以來聶魯達作為“愛情詩人”的文學形象被不斷強化不僅在有關聶魯達的詩歌和散文作品的翻譯中能夠體現出來,而且在關于聶魯達的傳記作品中也能夠清晰地呈現聶魯達在當代中國不同時期的接受過程中,由“政治詩人”、“人民詩人”向“愛情詩人”轉變的過程。
1990年代后期以來關于聶魯達的傳記作品已不再像此前的傳記更為強調其政治身份和政治抒情詩,而是同時強調聶魯達傳奇性的愛情、婚姻生活。為紀念聶魯達誕辰100周年,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推出了趙振江、滕威合著的《山巖上的肖像:聶魯達的愛情·詩·革命》。顯然在這部傳記作品中,聶魯達本人的愛情生活和愛情詩歌的寫作被強調出來,這對于長期的政治文化語境下聶魯達被完全塑造為一個政治詩人而言,其意義和價值是顯而易見的,而在關于聶魯達的愛情生活的描述中,一個愛欲的、追求性、肉體的聶魯達被呈現和“塑造”出來。在著者看來,從聶魯達的孩提時代開始他就是一個專注于男女之情的人,很早的時候聶魯達就幫別人寫作情書,招女孩子喜歡,而關于聶魯達的第一次一夜情的描述和想象無疑會滿足讀者強烈的好奇與欲望,“而離家在外的聶魯達,在晴朗而寒冷的夜里,一時難以入睡。沒有月亮,星星卻異常晶亮,他看著看著,也漸漸睡著了。突然,他醒了,感覺什么東西在靠近他,一個陌生的身體在麥秸下悄悄地,一點一點地向他的身體移動過來。寂靜如水的夜里,只聽見麥秸輕微斷裂的聲音。他怕極了。他想也許該大聲呼救,但是他什么也沒有做,只是全身繃緊,一動不動,等待。隨著耳邊傳來細柔的呼吸聲,一只女人的手伸向他,溫柔地撫摸他,他的額頭、雙眼、臉龐。接著,她濕潤的雙唇緊緊地吸著他嘴唇,她的整個身體緊緊地貼住他身體,直到合為一體。青春期的聶魯達沒有感到丁點兒恐懼,取而代之的是潮水般洶涌的快樂。他以同樣的柔情撫摸她長長的辮子、額頭、雙眼、臉龐、乳房、臀部、大腿,探索那神秘的未知世界”。自此,聶魯達的情感生活和婚姻故事被研究者甚至通俗讀物所格外關注。如上大學時聶魯達和一位年輕小說家的遺孀開始同居的情節,再到后來與特蕾莎(《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中的“瑪麗索爾”,《黑島紀事》中的特魯莎),阿爾貝蒂娜·羅莎·阿索卡爾(《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中的“瑪麗松布拉”)以及瑪麗婭·帕羅迪、喬斯·布莉斯的情感故事,他后來的妻子瑪麗婭·安東涅塔·哈格納爾、黛莉婭·德爾·卡莉爾、瑪蒂爾德。這些大量的女性貫穿了聶魯達的一生,換言之在一些聶魯達的翻譯者和研究者看來,“從少年時起,情欲成為聶魯達最重要的生命體驗之一;沒有欲望的力量,他無法寫作,甚至也無法生活”,“他渴望女人,渴望她們愛他,渴望從她們身上獲得生命的激情和創作的活力,渴望征服她們、占有她們。女人,就像他迷戀的石頭、貝殼、書以及大自然中的萬物一樣,他的生命中一刻不能缺少她們,但他也無法從頭至尾只喜歡一個女人,就像他無法一輩子只喜歡一塊石頭,一個貝殼一樣。他是收藏家,喜歡豐富、變化、差異、新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和不同的女人歡愛出于同樣的邏輯。所有這些豐富了他的生命,他的詩歌,而那些女人,似乎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他的愛情的傷害”。可見在《山巖上的肖像:聶魯達的愛情·詩·革命》這部傳記作品中,聶魯達本人的愛情生活、婚姻故事以及愛情詩歌的寫作顯然被強調和放大了,一個愛欲的、追求性、肉體的聶魯達被呈現和“塑造”出來。
大眾文化與多元媒介視閾中的“傳奇詩人”
隨著19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加速,文化和文學語境的劇烈轉換以及大規模的大眾文化、消費文化、影視文化的迅猛發展和娛樂精神的全面張揚,聶魯達的形象再次發生了位移。各種網絡論壇、媒體報刊不斷弱化和邊緣化聶魯達的政治抒情詩人的一面,而不斷張揚、強化其愛情、婚姻、性愛以及傳奇詩人的形象,聶魯達的世俗生活被不斷的強化,政治生活不斷被弱化。換言之,學術界、普通讀者和媒體所關注的熱點已經不再是聶魯達的政治經歷和一般意義上的文學生涯,而是轉向了聶魯達具有傳奇性的一生,甚至更為關注聶魯達和幾個女性之間的戀情、婚姻以及隱秘的私人生活,聶魯達“傳奇詩人”的形象被逐步樹立起來。而在此過程中,大眾文化、消費文化和網絡等新媒體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閱讀的消費化、時尚化、感官化使得聶魯達成了被消費的商品。
在此文化和政治語境的轉換下,1990年代后期以來研究者和普通讀者逐漸淡忘了聶魯達的政治抒情詩,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聶魯達的愛情詩歌要比他的政治抒情詩更重要。在大眾文化、消費文化和“娛樂至死”的后工業時代語境之下,聶魯達作為“傳奇詩人”的一面被不斷強調,而這與政治年代單一強調其政治性的一面都具有顯而易見的偏頗性。隨著后工業時代的降臨和后現代主義與消費主義、娛樂精神的全面張揚,拉美文學的翻譯與接受遭到沖擊與冷落。
1990年代以來,很多研究文章和各種媒體報刊(包括大量的通俗讀物,如《讀者》、《知音》、《譯林》、《大眾電影》、《世界電影》、《視野》等)都不斷強調聶魯達的情感生活和傳奇故事。而隨著電影《郵差》、電視劇《似水年華》、中國中央電視臺制作的《極地跨越》等影視作品的強大影響以及網絡等多元媒介的迅速發展,研究者和讀者所關注的已經不再是聶魯達的政治抒情詩,也不只是愛情詩篇,而是更為關注聶魯達多變的婚姻、戀情生活以及其傳奇性的一生。當聶魯達的私人生活最終成為公眾視野中的噱頭和賣點的時候,這不能不是一個詩人生前所沒有預料到的悲哀。當年那個一再被強調的政治抒情詩人到了這一時期,則無論是在中國的文學史敘事還是一般意義上的研究中都不斷地被弱化和邊緣化。顯然1990年代以來多元的傳播媒介(尤其是網絡媒介)對聶魯達的接受、傳播與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上個世紀50~70年代的媒介傳播網絡主要是傳統的紙質媒介和電臺廣播,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政治宣傳。聶魯達的文學形象的塑造與傳播也只能限定在極其嚴格的政治層面。而網絡等電子化的傳播機制擺脫了以往的政治化和傳播限制,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傳播的廣度、速度,并且這種多元化的傳播方式帶有很明顯的個人性、商業性和娛樂性。而對聶魯達愛情、婚姻生活和傳奇人生的強調顯然與當年單純強調其政治性都呈現了一個問題的兩面,即都忽視了聶魯達文學形象的豐富性與變化特征。而對于聶魯達來說,美麗的愛情是他生活中重要的部分,而政治同樣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更何況,聶魯達的詩歌寫作過程經歷了幾次相當大的變化,他的詩歌是遠非政治和愛情所能涵括得了的。
在1990年代后期以來,影視文化、大眾文化和網絡等媒體一起塑造的接受者(含普通讀者、文藝批評者、書商、出版社)對聶魯達形象的重新塑造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實際上1990年代以在對聶魯達的接受過程中其日常生活、家庭婚姻故事的強調是具有普遍性的,與此類似,中國對魯迅、張愛玲、林語堂、周作人、梁實秋、沈從文、徐志摩、海子、王小波等人的高度評價和傳記作品也往往集中于這些作家的日常化敘事。顯然這種對日常化敘事的倚重與這一時期的大眾化、消費化的接受語境是密切相關的。在此語境下連以往的領袖、偶像在接受者那里也發生了位移,如1989年中外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權延赤撰寫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一書中,人們關注的已不是以往那個被極端神話的偶像,而是更為關注毛澤東的私人生活,他的個人生活習慣、飲食起居、衣食住行和個人愛好成了大眾的閱讀期待。此后類似的關于領袖的傳記性的書籍大量涌入市場。作者和讀者更為看重的不是這些作家的文學成就,而是這些作家紛繁錯亂的生活履歷和傳奇性的一生(包括一些作家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而這無疑滿足了商業時代的大眾接受期待。以著名的朦朧詩人顧城為例,在1993年之前,人們關注他的“童話詩人”形象,而當1993年10月18日顧城在法國激流島殺妻自縊之后,讀者更為關注詩人的性格畸變、愛情、婚姻和多角戀的傳奇性故事。這也是為什么顧城、雷米合寫的自傳性小說《英兒》在當時暢銷的原因了。獵奇、窺私欲望成為1990年代后期以來的一個典型的閱讀心理,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大量熱銷的關于個人隱私、婚外戀的書籍。
隨著政治年代傳播媒介方式的結束,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和文化語境的轉換以及大規模的商業文化、大眾文化和娛樂精神的全面出現,聶魯達在中國的接受又陷入了另外一個極端。當年那個一再被中國強調和倚重的政治抒情詩人已經被傳奇詩人所取代。而對聶魯達愛情、婚姻生活和傳奇人生的強調顯然與當年強調其政治性的一樣都忽略了聶魯達文學形象的豐富性和立體性。消費文化、大眾文化、娛樂精神和電視、網絡傳媒對于聶魯達的文學形象的塑造顯然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所強調的在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里,造成精神毀滅的敵人更可能是一個滿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讓人心生懷疑和仇恨的人。我們不能不注意到這樣一個顯在的事實:詩歌接受與傳播也與娛樂和消費相當含混地纏繞在一起。
在1980年代后期中國對聶魯達的接受過程中,日漸興起的大眾文化尤其是影視文化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說的“目前居統治地位的是視覺觀念。聲音和形象,尤其是后者,組織了美學,統率了觀眾。在一個大眾社會里,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確實隨著讀圖、讀屏時代的到來,影視文化在社會文化場閾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1990年代后期影視文化的快速發展,聶魯達的形象經過影視作品、紀錄片等得以迅速傳播。中國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在2002年制作的規模空前的大型節目《極地跨越》中的“智利篇”就涉及了聶魯達和中國詩人艾青之間的交往情誼。中央電視臺作為中國最重要的主流媒體對聶魯達所起到的傳播作用是毋庸諱言的。1995年上映的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意大利電影《郵差》(又譯作《事先公開的求愛事件》)以及智利和西班牙合拍的紀錄片《聶魯達在瓦爾帕拉伊索》都使拉丁美洲家喻戶曉的智利詩人聶魯達變得舉世皆知,也再次在中國掀起了聶魯達熱潮。《郵差》這部電影曾獲西班牙韋爾瓦“哥倫布金獎”并榮獲1996年美國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劇情片音樂獎,這更有力地推動了聶魯達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盡管在這部著名的意大利電影《郵差》中,遭放逐的詩人聶魯達并非故事的一號主人公,但是一些重要的關于聶魯達和妻子瑪蒂爾德的情節,以及大海邊山頂上的那棟小房子里小唱機的纏綿而蒼涼的音樂,窗外的海風、海浪都給觀眾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聶魯達在墨西哥流亡期間與智利歌手瑪蒂爾德重逢并瞞著妻子開始了長達六年之久的秘密戀情,這也是電影《郵差》的故事背景。據此,《郵差》中聶魯達的情感生活和不無浪漫的生活場景使得中國的觀眾、讀者甚至是專業研究者不只是在聶魯達的詩歌和文學世界中徜徉,而是深入到了聶魯達的愛情、婚姻、傳奇故事的世界中。在聶魯達的一生中,他與眾多女性都有著復雜的交往甚至情感糾葛,聶魯達的3次婚姻成了1990年代后期人們關注的焦點。1951~1952年,瑪蒂爾德陪著聶魯達在意大利的小島上度過了流亡歲月,電影《郵差》就以聶魯達的流亡生活以及這一段特殊的戀情故事為背景,“在意大利一個美麗的161c3081065e0585007c20ca3dc9c1bc小島上同居的日子里,聶魯達和瑪蒂爾德每天早上醒來后在床上度過一段美妙的時光,下午在海邊盡情地散步,晚上聊天,兩人似乎總有說不完的話。聶魯達常常給瑪蒂爾德一些意外的小禮物——一首接一首膾炙人口、流芳百世的情詩,最意外的禮物是1952年5月1日的晚上,聶魯達把她拉到海邊,為她戴上了一枚戒指。他倆在月光下自行舉行了一個別致的‘婚禮’,兩人對著月光發誓,無論今后發生什么,兩人從此永不分離。當然,這個婚姻既不被法律所承認,也不被世人所認可”③。而此后,唱片公司出版的電影原聲帶還特別加進了聶魯達的十四首詩作,并由著名的好萊塢影星和歌星如麥當娜(Madonna)、朱莉婭·羅伯茨(Julia Roberts)、安迪·加西亞(Andy Garcia)、拉爾夫·費因斯(Ralph Fiennes)等這些“聶魯達迷”來朗誦。這顯然已經不是純粹的文學宣傳而是好萊塢式的商業運作了。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995年的電影《郵差》上映后,《當代外國文學》在1998年的第3期就大力推出智利作家安東尼奧·斯卡爾梅達(1940—)的中篇小說《聶魯達的郵遞員》(占43個頁碼),而電影《郵差》就來自這部小說。《郵差》這部電影對于推動聶魯達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對于中國讀者和觀眾而言更是如此,電影中崇拜聶魯達和聶魯達詩歌的馬里奧·赫梅內斯成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追捧聶魯達者的代名詞。值得注意的是,當年英文版的《郵差》電影海報相當煽情并充滿欲望的暗示,畫面是一個手拿信件的男人和一個裸露胸部的性感女人,顯然是在宣揚這是一部偉大的浪漫愛情劇作。而觀眾對《郵差》顯然沒有過多留意于這部電影在政治上的含義,而更為關注的是郵差馬里奧·赫梅內斯為詩人聶魯達身邊有眾多美麗、年輕女子而心生艷羨,也希望自己能像詩人那樣招引女孩子的喜歡。無論是小說《聶魯達的郵遞員》,還是電影《郵差》,馬里奧·赫梅內斯都是一個愛情和欲望的幻想家和踐行者,而小說和電影也都是以愛情為核心展開敘事。馬里奧是一個帶有一定“病態”的形象,他整日“做著大膽的愛情美夢”,“在甜美的夢囈中覓愛尋歡”,最愛看愛情電影,對大嘴的性感女郎“心馳神往”,到舊雜志書店里撫摸他喜歡的女演員們的照片,酒吧里穿著小了兩個號碼的襯衫緊裹著胸部和軀干的打臺球的姑娘——比阿特麗斯,都讓馬里奧如此沉迷,“她那栗色卷曲的頭發被微風吹得有些凌亂,像櫻桃一樣圓溜溜的棕色眼睛流露出幾分憂郁而又充滿著自信,胸部‘別有用心’地被小兩號的運動衫緊緊地‘壓迫’著,兩只乳房雖遮蓋嚴實,但仍有幾分不安分,那腰肢能誘人摟著她大跳起探戈舞來,直跳得把黎明送走、酒全喝光。就在姑娘離開柜臺,走在廳上地板的一瞬間,支撐著的各個姣好的部位就顯露了出來:在姑娘嬌小的腰肢下,雙臀扭動裊娜多姿,身著一條別有韻味的迷你裙,使得那修長的大腿格外引人注目,從大腿到古銅色皮膚的膝蓋部,像一段慢板舞蹈一樣直至那赤裸的雙腳”。而一定程度上馬里奧·赫梅內斯喜歡和聶魯達交往也不排除他的私心,他買下聶魯達的詩集《元素的頌歌》、《元素的新頌歌》也是希望獲得聶魯達的簽名而在漂亮的女人面前炫耀。馬里奧·赫梅內斯獻給心上人的情詩同樣成為讀者們注意的部分,如“裸體的你,是這樣簡明,就像你的一只小手,/ 光滑、平坦、小巧、圓滾、透明,/ 你有月亮的線條、蘋果似的風姿,/ 裸體的你,是如此瘦弱,像赤裸的麥子”。顯然更多的觀眾關注的還是這部影片中兩性關系,而這部電影之所以能夠獲得世界電影最高獎的榮譽其原因顯然不只限于此,這部電影對人性、政治、民族、文學、死亡和歷史的思考都是相當深入的。而經過《郵差》這部電影的“洗禮”,中國觀眾和讀者開始聚焦于聶魯達的私人生活和傳奇故事,而聶魯達的愛情詩篇和他的傳奇故事也影響到了中國很多的影視作品。在由黃磊、劉若英、李心潔等演員出演并熱播的電視劇《似水年華》中,黃磊扮演的男主角在故事的結尾就朗誦了聶魯達的詩歌名篇——“當華美的葉片落盡 / 生命的脈絡才歷歷可見 / 是不是,我們的愛情也要到霜染 / 時光逝去時 / 才能像北方冬天的質感一般 / 清晰 勇敢堅強”。很多的中國讀者和觀眾就是在這部電視劇《似水年華》中進一步認識和了解聶魯達的,而包括《郵差》、《似水年華》在內的這些影視作品對于塑造聶魯達的傳奇詩人的形象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這也能夠反觀影視文化在聶魯達的接受與傳播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1990年代后期以來,聶魯達的接受范圍已經不再局限于學術界和文學界,而是頻頻出現于各種網絡論壇和報刊媒體,甚至像《讀者》、《知音》、《故事會》、《視野》、《大眾電影》、《世界電影》、《集郵博覽》這樣的通俗暢銷雜志,以及《人民日報》、《南方周末》、《北京晚報》、《新京報》、《中國青年報》、《中華讀書報》等發行量較大的報紙也頻頻刊載聶魯達的愛情生活和傳奇故事。在1990年代后期以來大量的出版社和出版商為了迎合讀者的需要和“欲望化閱讀”而推出了大量的“情色”書籍。在這種“情色”化、消費化的閱讀視野之下聶魯達逐漸被轉換為一個充滿“愛欲”的傳奇詩人的形象。對于聶魯達而言,美麗的愛情和婚姻生活是他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他曾說過:“我們不能只寫談政治的詩,不能只用一種顏色來畫畫”,“還有一個長遠的責任,是詩人所不能忘記的。詩人首先應該寫愛情詩,否則,這是一個很奇怪的詩人。”而聶魯達由一個政治詩人形象向愛情詩人、傳奇詩人形象的轉換不能不與1990年代后期以來飛速發展的多元媒體有關。而值得注意的是智利的很多作家如豪爾赫·卡拉斯科的文章《聶魯達的露水姻緣》(朱景冬譯,《譯林》(文摘版),2007年,第1期)對聶魯達個人情感生活的肆意渲染,智利作家泰特爾鮑姆在文章中記述了聶魯達幾十次的愛情故事,甚至認為愛情和性愛是聶魯達的日常活動。而尤其是聶魯達的第三任妻子瑪蒂爾德臨終前寫下的自傳《我和聶魯達在一起的日子》在2005年的出版對于推動聶魯達的傳奇詩人的形象和傳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只有一個聶魯達”
無論是政治年代、“新時期”,還是1990年代以來多元文化和新媒介的快速發展,當代中國對聶魯達的接受與塑造過程,就是不斷地根據不同時期自身文化建構的需要,將聶魯達納入到當時的文化場閾與體系的過程。而正是由于不同時期政治和文化建構的需要,聶魯達的形象才發生了如此富有戲劇性的變化。接受的過程就是批評的過程,聶魯達在當代中國不同時期的接受就是接受者與文化和社會聯合過濾、篩選與批評的過程。而唯有在歷史語境之下,采用田野作業的方式還原和呈現出一個復雜的多向度的聶魯達的詩歌形象才是正途,換言之聶魯達的文學形象是豐富的,甚至是復雜的,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詩人,也非耽溺于身體欲望的愛情詩人甚至是“情色”詩人。在政治年代已經遠去,物欲和商業化的時代來臨的時候,研究者逐漸淡忘了聶魯達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抒情詩。這并非意味著聶魯達的政治抒情詩就比他的愛情詩歌以及其他題材的詩作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聶魯達的文學形象是極其豐富和復雜的。換言之,聶魯達并非是一個當代中國在接受與塑造過程中在不同時期呈現的單一化、刻板化的政治詩人、愛情歌者甚至傳奇詩人形象。應該說只有一個聶魯達,這個聶魯達又是無比豐富的。也許正如詩人自己所說的“所以不知道到底誰是我 / 也不知道現在或將來有多少個我”(《許多我》)。他年輕消瘦而中年肥胖,既矜持自負又幽默隨和,既慷慨大方又執拗狹隘,既崇拜詩歌又喜歡看偵探通俗小說,喜歡看商業電影而又喜歡交響樂和歌劇。同樣聶魯達不會只關心女人而不關注政治,也不會只抗議黑暗現實而不謳歌大自然與繁復的內心世界。聶魯達既是一個貧窮者又是一個癡迷的收藏家,既是一個詩人、戰士、革命者又是多情風流的男人。當代中國在不同時期對聶魯達文學形象的接受與塑造都不同程度地將聶魯達窄化了,這也呈現了不同時期的社會政治、文化、歷史場閾對文學接受與傳播的強大影響。而當我們回溯半個多世紀中國對聶魯達的文學接受過程,看到的更多的是遺憾和偏頗。無論是政治年代的政治詩人的塑造,還是在多元文化語境下的愛情詩人和傳奇詩人的塑造,聶魯達都有不斷地被狹窄化和庸俗化的危險。而他的豐富性,他詩歌中的南方記憶與故鄉情結,他的滾燙的革命熱情、生命體驗、浪漫想象、愛情欲望、自由精神、哲理反思、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語言、詩歌技藝的道德都受到了相當的遮蔽。無論是將聶魯達塑造為一個政治詩人,還是將其塑造為愛情詩人甚至傳奇詩人,都只能得出一個結論:文學的接受與傳播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動態的結構。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聶魯達是一個相當豐富的、多側面的、立體型的作家,換言之“只有一個聶魯達”,只是這個聶魯達在不同時期的傳播與接受過程中不斷經受了復雜的選擇、過濾與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