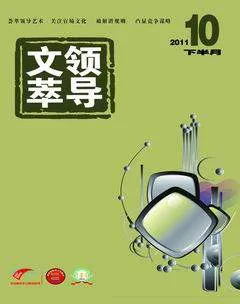前蘇東集團國家轉型之鑒
20年來,前蘇東集團國家的轉型有哪些值得借鑒的經驗和教訓?能否為中國未來的改革提供啟迪?
轉型國家的經驗
許成鋼(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教授):東歐國家最近20年來的轉型歷程,有豐富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以波蘭為例,自從體制轉型以來,其經濟增長速度非常快。在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之前,波蘭總體的經濟增長和中國相差并不很大。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以波蘭為代表的中東歐經濟在人均GDP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之后仍然能夠快速增長。這應當歸功于以下三點因素:一、經濟體制的基本轉變,即從中央計劃的國有經濟轉變為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二、政治體制的基本轉變,即從過去的體制轉變為民主、憲政體制;三、貨幣的可兌換性,這一因素的作用小于前兩個因素,但也非常重要。
田春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研究員):近20多年來,中東歐和蘇聯地區國家的轉型的經驗教訓很多,在這里,我想提出一些問題供大家思考:
一、轉型國家實現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是不是可以被認定為已經完成制度“轉型”?
在我看來,作為整體性、歷史性、變革性的人類社會的大規模的制度性轉型已經基本結束,這是對于“轉型是否終結”的基本的判斷。其標志是:首先,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制度性大變遷、大動蕩已經過去,市場經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框架已經在大多數國家建立。其次,各國已經走出“轉型衰退”的階段,市場的主體與運行、資源的配置與方式,市場制度的法律、規則,都在完善的過程。再有,多數轉型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已經與國際經濟規則接軌(盡管出現很多問題)。最后,在西方理論界看來,中東歐國家的轉型已經結束,其重要標志就是這些國家大多數已經“加入歐盟”。
二、轉型國家的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結合導致和產生的腐敗,是不是轉型國家特有的現象?
俄羅斯的經驗表明,政治權力一旦與經濟利益勾結,“政治內部人”首先成為改革轉型的“攫財大亨”。也許,這就是經濟社會轉型的“遺產”?過去,我們更多地關注“經濟內部人”而忽略關于轉型中“政治內部人”的權力制約問題。如何解決轉型過程中的“權錢結合”以及“權貴資本主義”的問題,尚需深入研究。
三、“由國家力量主導的經濟”(國家資本主義)以及“主權財富基金”,是不是轉型國家的一種經濟趨勢?
近年來,俄羅斯逐漸顯現出“國家資本主義”的特征與形態,即國家資本與國家政權的結合。自本世紀之初普京執政起,俄羅斯通過整治葉利欽時期形成的寡頭集團、委派政府官員在壟斷性企業任職、組建國家控股的大型旗艦企業等方式,實現了國家資本向命脈企業的擴張與壟斷。
四、歷史的路徑依賴對轉型有何影響?
俄羅斯經濟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轉型初期,以徹底否定原有制度的遺產、建立與原有制度和歷史慣性截然不同的制度模式為出發點。問題在于,在俄羅斯,非正式制度包括人們的理念、傳統、文化、習俗、道德等等,難以在短期內被移植,這使俄羅斯原有的歷史遺產和制度慣性會繼續發揮影響,而在較短時期內難以發生變化。那么,中國的轉型和社會發展是否同樣會受到歷史傳統的影響?
中國改革路在何方
許成鋼:中國過去一直推行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缺乏配套的產權和政治體制改革,試圖在不觸動現有體制的條件下,用通融的辦法來逐漸改變中國經濟。
然而,這種做法現在已經走到了盡頭。因為無處不在的政府權力使得中國面臨著許多基本問題,已經無法用通融的方法來解決。在缺乏基本體制轉型的情況下,政府的力量不會自行削弱。
中國現在必須面對、不能回避土地所有權的問題,它是任何經濟里面的最基本的產權問題,是決定社會進步的基本條件。
孔田平(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東歐研究室主任):關于中國改革的路徑,許教授提到的土地產權制度的變革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選項,另一個選項就是政府財政預算方面的改革,我認為,應當將政府預算置于立法機關的嚴格監督之下。政府預算進一步公開化,讓立法機關能夠真正有效地監督政府財政。
中國人需要討論改革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價值觀,討論民主、自由、法治、人權是不是我們應當認同的價值觀。中國改革要進一步推進,必須在價值觀上凝聚社會共識。
王小魯(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就經濟而言,私有制是不是惟一的評價標準呢?我認為,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關鍵是看私有化是怎么推行的,是通過市場競爭積累起來的,還是偷來的、搶來的,抑或通過腐敗、通過尋租拿到的?其間存在很大的區別。
另一個問題是,私有制在經濟中的作用是什么?是促進競爭,還是導致壟斷?葉利欽時期的休克療法,造就了一大批石油財閥、壟斷寡頭。他們都是私有的,但他們的財產基本上是偷來的。
除了靠競爭發展起來的私有經濟外,中國還存在一個靜悄悄的、圍繞權力發生的私有化。結果是少數人積累了幾十億、幾百億元的資產,這些資產是靠尋租、官商勾結得到的。這種情況和改革早期以競爭為主導的私有化的方向是相反的,是危險的,需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靠政府的透明和社會公眾對權力的制約、監督來杜絕這類現象。(摘自《中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