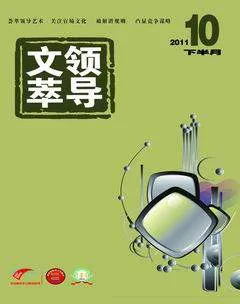“延安處處顯得平等”
我是1938年秋天到達延安的。一到延安,就感受到了一種自由民主的空氣,精神為之一振,心情也格外舒暢。那時是張聞天擔任總書記,也是毛澤東后來說的,處于我們黨的歷史上從遵義會議以來的第二個生動活潑時期。
延安當時的生活確實處處顯得平等,感覺不到明顯的等級制,有什么話都可以說,沒人干涉,沒有壓抑之氣,到處是歡快的歌聲。
我們抗大上課以中隊為單位。在課堂上,學員可以有不同意見,還可以隨便插話,隨便提問題。我那時候還小,只有十五六歲,就敢于當面和教員爭論。有一次學哲學,我就和助教沙英爭起來了,爭論的是共產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我提出是供給和需求的矛盾,他說我不對,我也說他不對,誰也說不服誰。
那時的言論自由,也表現在報刊上的公開辯論,各種各樣的問題都有,特別是文藝界。
當時延安的文人好像分為兩派,一派是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像蕭軍等;一派是從前線和根據地來的,像丁玲等。不管哪派,都可以辦自己的刊物,互相批評,沒有檢查。連《解放日報》也發表不同意見。我記得,有一次就登了一篇為京劇《坐樓殺惜》中的閻婆惜打抱不平的文章,說閻婆惜是被壓迫、受欺負者,宋江則屬于剝削階級,是糟踏女人的。接著,不少人就起來寫文章反駁,說這個觀點有悖當時的大背景,因為宋江是農民起義的領袖,閻婆惜告宋江的狀,其行為是反動的。
那個時候不論一個連隊、一個單位,都可以出墻報,大事小事都可以講,批評上級組織也可以,點名批評領導也可以。不過大家提的意見還都比較實事求是。這些墻報有編委會,作者只要把稿子交編委會,糊到墻上就完了,用不著給上面看,上面也沒有訂出檢查制度,反正出不了太大亂子。
當時延安轟動的就是中央青委的童大林、李銳等人在大砭溝(后稱文化溝)搞了一個墻報叫《輕騎隊》,內容多是議論時政和針砭時弊的,文風犀利潑辣,引起好多人去看。
整風前的延安,不但等級制不明顯,上下級關系也不很嚴格。下級給上級提意見,幾乎是常事。
我就直接給賀龍提過一次意見。當時我們在抗大上學,公家每年夏天給大家發一套單衣,但從賀龍的120師來學習的人,120師還能再發一套衣服。這就顯得太不公平了。因此我就給賀龍寫了一封信,說這不是在搞山頭主義嗎?大家都在一起學習,你120師來的學員怎么又另發一套衣服,而其他學生卻只有一套衣服。我提完意見,賀龍就派人來給我解釋,雖然說服不了我,但至少說明人家把我的意見還是當一回事的。
延安的出版也是自由的,沒有審查。特別是文藝界,各派都自己出自己的刊物。當時延安的印刷廠好像也容易辦,只要從國民黨地區買一套鉛字就可以辦了。那時延安的出版物還不少,刊物各系統都有,文藝界就有好幾個。
各機關一般都有圖書館。大點的圖書館,可以從大后方把各種各樣的書都買進來。像毛澤東喜歡看古書,就多是從大后方運進來的。那個時候沒有“反革命書”這個概念。
我那時看的舊書,包括中國的外國的,都是在延安看的,像鄭振鐸的新文學大系,希臘神話,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魯迅全集,各種各樣的書都有。我熟讀的《紅樓夢》也是在延安看的。后來1954年我們在日內瓦開會的時候,有人跟周恩來說,我可以背《紅樓夢》。總理問,什么時候看的《紅樓夢》?我說是在延安看的。周恩來說在延安哪有時間?我說是擠時間,例如連抬糞時也拿著書看,上山的時候不能看,就默記背誦。
延安整風前,不但什么書都可以看,什么歌也都可以唱。像《何日君再來》、《毛毛雨》這些舊社會的歌,我都是在延安學的。但這只是同學的歌詠隊自己唱的,領導上組織學唱的,還都是抗戰歌曲。
我們在抗大,要早集合晚點名,集合起來就唱歌,一般一個連隊有一個歌詠干事,自己先把歌學會,再教給大家,這些歌基本上都是救亡歌曲。像《到敵人后方去》,《大刀進行曲》,《在太行山上》等。和現在的紅歌不一樣,那時沒有歌頌黨的歌曲。歌頌黨的歌曲基本上都是抗戰勝利后才有的。在延安唱《東方紅》,也是整風以后才普及起來。
我在延安參加過兩次選舉,一次是1939年直接選舉七大代表,當時是無記名投票,我們抗大三分校選了幾個代表,這些代表的姓名和簡介在墻上一貼,我們就投票。我入黨七十多年,參加直選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就這么一次。
參加黨外選舉也有一次,是1941年選舉第二屆邊區參議員。我們三分校和魯藝、自然科學院三個單位為一個選區,產生一個參議員。我們的候選人是校長郭化若,魯藝提的是周揚,自然科學院的徐特立退出了。競選時周揚講了話,說他當選以后要承擔什么樣的責任,要把大家的意見反映上去,還批評郭化若不參加會,說你看,他對這個選舉不重視吧。但由于我們三分校人數占壓倒優勢,所以最后當選的還是郭化若。開完參議會后郭化若還向大家解釋,上次有人批評我沒參加會,是因為軍委會有重要事情,我也是請了假的。實際上我是非常重視這次選舉的。
在延安,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沒有什么高低貴賤之分。一到禮拜日,大家都喜歡到延安北門外的一處大山溝溜達。中央領導也騎著馬來,不過很遠就下來了,一個警衛員把馬拴好看著,一個警衛員陪著他散步。延安的秩序很好,所以領導出來用不著緊張。我就有一次看見何思敬在那里溜達,毛澤東也在那里溜達,毛澤東就和他打招呼(因為何思敬是給毛澤東等講德國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所以很熟),他也點個頭,連寒暄也沒有。(摘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