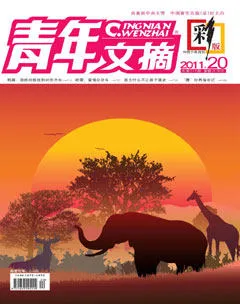最躊躇的門
一個人對你意義非凡,想到他,你便感到軟弱。
臨見一剎那,如橫著一道門,心酸、甜澀、怯懦,及至推開,又不知說什么,呵,那真是世上最躊躇的門。
我在三毛的《驀然回首》中見過它。三毛寫,和恩師顧福生約好見面,早到了兩分鐘,卻不敢進(jìn)門,只靜靜地站在夕陽下等。
等到時間到,等到有人領(lǐng)她進(jìn)院子,通往客廳“短短的路”,仍讓她感到“一切寂靜,好似永遠(yuǎn)沒有盡頭”。
就在見面前的幾秒,她還希望有人通知她,“顧福生出去了,忘了這一次的會晤”,但門終于開了,顧福生就在她的面前,于是“二十年的光陰飛逝,心中如電如幻如夢”,她變回少女時的樣子——“情怯依舊”。
三毛說,顧福生當(dāng)年改變了她的生命。
時間推至20年前,她因跟著顧福生學(xué)畫,走出自閉,恢復(fù)生機(jī)。
時間再推至10年前,她有個機(jī)會去見顧,但她在芝加哥的密西根大道上,“來來回回地走,眼看約定的時間一分一秒在自己凍僵的步子下踩掉”,最終還是沒有去,只因顧太重要,重要得她不知見面說什么,重要得怕自己不夠好——“沒有成績可以交代,兩手空空”。
蔣韻在《心愛的樹》中,寫過類似的感受。
大先生的前妻梅巧和他的學(xué)生私奔后,過得并不好。最艱難時,大先生通過女兒接濟(jì)梅巧——他始終愛她。
得知自己時日無多,大先生收拾書房,發(fā)現(xiàn)過去寫的沒發(fā)出的信,“梅:你這可恨的女人,你還好吧……”他握著它,手抖、淚濕,猶豫再三,他通過女兒約梅巧見面。此前,梅巧也曾問過女兒關(guān)于大先生,“她哽了一下,眼圈紅了”,用傷感、溫存的語調(diào)說:“你爸爸,他還好吧?”——同樣的五味雜陳和躊躇。
再相逢,一個對著恩人,一個對著愛人,卻“愣愣地,你望我,我望你”。大先生打了幾次火終于給彼此都點(diǎn)上了煙,“跨過34年的歲月,來在一個車站,好像就是為了在一起抽一支煙”。
嗚,始于躊躇,終于無言的相見,恐怕都源于深刻、深沉的情感體驗(yàn)。
我想起,我的一個女友認(rèn)識一位畫家,并愛慕他。畫家給她信息、郵件,她從來不回,“其實(shí)也回過,只是刪刪寫寫,寫寫刪刪,永遠(yuǎn)沒發(fā)出去”。
一次,畫家邀她看畫展,她沒說去卻去了,遠(yuǎn)遠(yuǎn)的,她看到畫家,逃似的飛快走到一邊。“見了他,我說什么?”畫展歸來,女友惆悵地兩手一攤。
靠近卻溜走,沒推開門,也沒給自己失望的機(jī)會,算幸運(yùn)。
要知道,不幸的推門者,在書中比比皆是啊。
老舍在《微神》中寫初戀,他對初戀的回憶凝固在舊時門邊一雙綠拖鞋上。后來他聽說初戀已變成暗娼,他鼓足勇氣,再去找初戀,初戀已睡在一口薄薄的棺材里。徹底,幻滅。
我總想著,最幸運(yùn)的推門者會是誰。
是那些挨著透明的門,無限接近,試圖推開,卻始終也推不開的人吧。
如羅曼·羅蘭。
“我來到波昂,貝多芬的故里。”
“我重新找到了貝多芬的影子和貝多芬的老朋友們……”
“在多霧的萊茵河畔,在那潮濕而灰色的四月天……我跪著,由貝多芬用強(qiáng)有力的手?jǐn)v扶起來。”
他在《貝多芬傳》的序言中如是說。
他沒有見過貝多芬,卻終生在貝多芬身上汲取力量,那力量支持他勇往直前。他不用躊躇,不會失望,不必?fù)?dān)心自己或?qū)Ψ讲粔蚝谩K挥酶屑ぃ屑ちα浚蛟S,也感激做一個純粹的追隨者、沉迷者、臣服者的幸福。
丁萌//摘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