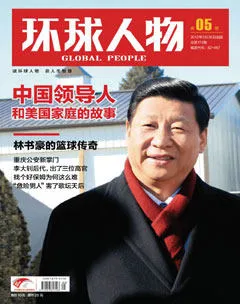中國說“不
為了敘利亞,在短短一個月時間內,中國在聯合國兩次說“不”。這讓世界感到吃驚,也感到疑惑,甚至引來五花八門的解讀和判斷。有人說,中國為了自己利益在力“挺”敘總統巴沙爾;有人說,中俄已經結成了“同盟”與西方對抗;甚至有人說,中俄連續投下否決票,讓人嗅到了“冷戰”的味道。
兩次說“不”有差別
中國兩次投下反對票,有所差別,但又一脈相承。
第一次,2月4日在聯合國安理會上,中國和俄羅斯一起否決了阿拉伯國家聯盟針對當前敘利亞問題提出的一份決議草案。這份草案一共16條,包括譴責敘利亞當局持續的侵犯人權和基本自由的行為等。安理會由中、美、英、法、俄5個常任理事國和10個非常任理事國組成,是唯一有權采取強制行動的聯合國機構。每個理事國有1票,實質性問題必須5個常任理事國都不反對才可通過。敘利亞問題就屬于此類。中俄的反對,讓聯合國無法對敘利亞采取強制行動。
第二次,是2月16日在聯合國大會上對聯大決議草案投反對票。這項決議向敘利亞政府提出5點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動;釋放所有近期被拘禁人士;從敘利亞城鎮撤出所有政府軍;保障和平示威的自由;確保阿盟和國際媒體人士自由進入敘利亞。與安理會決議不同的是,聯大決議由聯合國成員一起投票,但它沒有法律約束力,只有政治影響和象征意義。聯大決議只要簡單多數支持就可通過,任何國家均無否決權。結果,137個國家投票贊成這項決議,中俄等12個國家反對,17個國家棄權。
敘利亞國內沖突已經進行了11個月,統計稱,目前已經造成超過7400人死亡,其中包括2000多名政府安全部隊人員。政府軍與武裝分子在中部省份霍姆斯等地的沖突至今仍十分激烈。敘反對派稱,巴沙爾政權向普通示威民眾開槍;在西方國家看來,“敘政權屠殺人民”,“已經失去了合法性”。法國總統薩科齊2月17日和英國首相卡梅倫見面,希望敘利亞反對派團結一致,以便外界能夠幫助他們推翻巴沙爾。就連阿拉伯國家聯盟也敦促巴沙爾交權,在兩個月內組建包括反對派在內的國民團結政府。
兩次表決中,2月4日安理會的表決更為關鍵。為了爭取中俄“放行”,草案在措辭方面一再軟化,沒有直接提“制裁”等字眼。決議遭否決后,美駐聯合國代表蘇珊·賴斯非常惱怒,說“那些袒護殘暴政權的國家必須面對敘利亞人民的質問”。至于2月16日的聯大決議,用《華爾街日報》的話說,與2月4日的草案十分相似,“不過少了試圖讓中俄兩國同意的讓步條款”。中俄既然已對前者說“不”,對后者自然更會說“不”。
中國想說的真心話
中國說“不”的原因,溫家寶總理2月14日在北京會見中外記者時說得很清楚:中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絕不會庇護任何一方,包括敘利亞政府,但敘利亞的前途命運要由敘利亞人民自己決定。溫家寶說,在敘利亞問題上,當前最為緊迫的是防止戰亂,使敘利亞人民免遭更大的痛苦。這符合敘利亞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整個中東地區的和平穩定。
俄羅斯的立場也很明確。在2月16日的聯大決議表決后,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丘爾金說,這一決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令人擔憂的趨勢:有人試圖孤立敘利亞領導層,拒絕與其進行任何接觸,并將外部的模式強加給敘利亞,以實現政治解決。”
中方顯然不贊同關閉對話的渠道。2月17日,中國派特使、外交部副部長翟雋抵達大馬士革,為妥善解決敘利亞問題“做些貢獻”。翟雋會晤了巴沙爾,表明了中方立場。他也會見了敘主要反對派領導人,并表示愿與敘政府各政治派別、阿拉伯國家及阿盟保持溝通。
換句話說,在敘利亞問題上,一味強硬干涉,會把沖突的“結”越打越緊。中國說“不”,是希望緊繃的局勢緩和一下,并尋找解開這個“結”的機會。在目睹了“阿拉伯之春”給中東、北非國家帶來的動蕩,特別是目睹了利比亞血腥內戰之后,很多人相信,戰亂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也不能帶來真正的民主和改革,只會引發更多矛盾。翟雋說,實現國內穩定才能確保敘利亞的發展,才能為敘利亞改革創造良好的環境。這是經歷過動蕩年月、正進行改革開放的中國想說的真心話。
中國說“不”的幾種情況
回顧歷史,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曾經8次行使否決權。北京大學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教授張清敏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中國行使否決權可以大致分以下三種類型。第一類是考慮盟友的利益。比如,中國第一次行使否決權是1972年8月25日,否決了孟加拉國加入聯合國的決議草案。當時孟加拉國剛從巴基斯坦分離出去,中國投否決票,主要考慮的是好朋友巴基斯坦的利益。
第二類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主要是領土主權、臺灣等關系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比如1997年1月10日,中國否決了向危地馬拉派遣聯合國軍事觀察員的決議草案,原因是危地馬拉與臺灣維持“外交”關系,每年都參與要求臺灣加入聯合國的提案。1999年2月25日,中國否決了安理會關于延長聯合國維和部隊駐守馬其頓期限的決議草案。馬其頓1993年與我國建交,卻在1999年2月8日又與臺灣“建交”,迫使我動用否決權。
第三類是出于維護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基本原則,以及有利于爭議問題的和平解決。比如2007年1月,美國起草了緬甸問題決議草案,指責緬甸人權等問題對地區安全造成威脅。中國予以否決,認為緬甸問題是一國內政。2008年7月11日,中國否決了美國提出的制裁津巴布韋的提案,認為制裁津巴布韋將導致局勢進一步惡化。
張清敏認為:“這三種類型反映了中國對外政策的考慮和出發點。”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袁征在接受環球人物雜志采訪時表示,中國一般在兩種問題上說“不”。“一是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問題,二是違反基本國際法則的問題。中國希望在國際社會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積極維護世界和平。”
中國否決次數最少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1972年行使了兩次否決權,此后20多年就沒行使過,1997年至今行使了6次。這說明什么呢?張清敏認為,剛加入聯合國時,中國對相關程序的了解剛開始,有的否決現在來看其實沒有必要。“1972年到1997年,中國沒有行使否決權,很重要的原因是那段時間中國對一些問題相對超脫。而1997年以后,中國在解決國際問題時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許多問題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一些西方國家又總希望把聯合國作為推行自己對外政策的工具,忽視或違背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事情不斷發生,這也逼著中國的否決票在增加。”
袁征則分析說:“中國其實在安理會投的棄權票最多。投棄權票也是一種立場,說明中國持保留的態度,不是都贊同。上世紀70年代,中國在國際問題上發揮作用較小,更多在忙于國內的事。上世紀90年代以后,我們對許多國際問題表達了我們的關切。尤其是對武裝干涉,中方持有強烈保留的立場,因此投的否決票增加。”
實際上,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使用否決權次數最少的國家。有數據顯示,至2007年,五常中行使否決權以蘇聯及俄羅斯最多,共128次;美國83次,英國32次,法國18次,中國當時僅5次。最近中國5年行使了3次否決權,但也還是最少說“不”的國家。
中國說“不”要付出什么代價,又能收獲什么?
張清敏認為,說“不”肯定會有人不高興。“比如,中國否決孟加拉國加入聯合國,在當時肯定得罪孟加拉國,印度也不高興。但在關系中國核心問題,即中國的領土和主權時,不能管其他人高不高興。在熱點國際問題上,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對敘利亞問題的投票,敘國內反對派肯定也會不理解,不高興,但中國確實不是從自己的利益考慮,而是從國際法基本原則,從當事國人民的利益考慮。”
袁征則認為,中國對在聯合國投否決票,歷來都非常慎重,總是考慮怎樣不違反國際法原則,堅持和平共處,最大程度維護自身利益。“這或多或少受到些非議,根本上講,還是一個利益問題。”不過,那些支持某一決議或者反對某一決議的國家,又有哪個不是從自身利益出發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