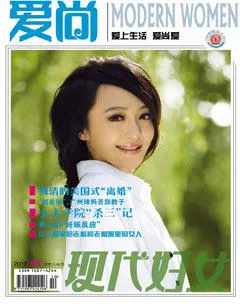殺豬匠和904個讀書娃
每天賣肉、砍柴、種田,辛勤勞作,在廣東英德市下鎮,鄧衛星就是這樣一位平凡的“豬肉佬”。30年來,他甘守清貧,卻先后收留了方圓二三十里內904個困難兒童,在家里吃住,照料他們上學,幫助這些娃娃們圓了讀書夢。
對失學有著切膚之痛的他,產生了助人之心
從廣州一路向北,車行140多公里,便是連綿的南嶺山脈,在一片山林中有一間破敗的土坯房。推開“吱吱呀呀”的木門,門外的陽光只照亮了屋內的一半。
這兒是鄧衛星的老家,30年前,就是在這里,他收留了第一批輟學兒童。
1959年出生的鄧衛星,從小喜歡讀書,是遠近聞名的“小秀才”。1977年,他初中畢業,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當地著名的英德中學。
不幸的是,就在那一年,父親去世了。身為長子的鄧衛星只能被迫退學,這時,他在英德中學的課堂上才坐了僅僅一個星期。
鄧衛星擱下書包,背上背簍,跟著堂叔成了一名“殺豬匠”。他每天起早貪黑,翻山越嶺到農戶家收豬、殺豬,販賣到集市,維持一家的生計。
1981年,鄧衛星下鄉收豬時,遇到了16歲的輟學在家的陸秋賢。“怎么不去學校讀書?”鄧衛星問。陸秋賢無奈地說:“我想讀啊,可我們這里這么窮,學校又那么遠。幾十里山路走一趟就是兩三小時,這書怎么讀?”
對失學有著切膚之痛的鄧衛星立刻產生了助人之心。想到自己家雖窮,但離學校比較近,鄧衛星問陸秋賢:“你愿不愿意住到我家里?”
就是這樣簡單的一句話,改變了陸秋賢的人生。她和另外5個跟她一樣情況的女孩,扛著鋪蓋走進了這間簡陋的屋子。
而這時,鄧衛星剛開始和熊廷賀處對象。鄧衛星對熊廷賀據實以告:“家里就是這樣的情況。你要是可以幫忙帶這些小孩,那我們就結婚。”1982年,善良的熊廷賀嫁入鄧家,一起默默地擔起了照顧孩子的重擔。
咬咬牙,把家搬到學校的斜對面
陸秋賢等6個女孩在鄧家住到了初中畢業后回了老家。而此時,鄧家收留孩子寄宿、不收錢只需背點米去的消息,早已傳遍四鄰八鄉。不少家長紛紛把上學不便的孩子送來,憨厚的鄧衛星來者不拒:“看人家有困難,就幫一下啦。”
來鄧家寄宿的孩子從10多個增加到30多個,最多時有50多個。其中,最小的才上小學一年級,大的也不過在上初中。鄧家成了村里人玩笑話中的“兒童避難所”,事實上卻是學生、家長心中感激不盡的“學生之家”。
20世紀90年代初,“學生之家”鎮上的學校搬遷了,鄧家的“地理優勢”一下消失了,孩子們的上學難又成了一個大問題。面對家長們痛苦糾結的目光,鄧衛星左右為難。
此時,距離新學校很近的一塊地皮正在尋找買家,開價兩千多元,這對以賣肉為生的鄧衛星來說不是個小數目。但他咬咬牙,湊錢買了下來,蓋上了房。就這樣,鄧衛星把自己的家搬到了學校的斜對面,把“學生之家”繼續到了現在。
如今,走進鄧家仿佛走進了學生宿舍。堂屋里,幾排舊課桌椅疊放在一側,墻上貼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往里走,一間間房間便是孩子們的宿舍。床是上下鋪,上方架一根竹竿用來掛衣服。3張床并在一起,已經將房間占得滿當當,靠門一邊還加了一張鋪。后院廚房的一側,整整齊齊地掛了一溜50多條毛巾。樓梯轉角則擺滿了孩子們的鞋,從一樓一直堆到二樓。
30年來,鄧家的每一天幾乎都是這樣開始的:每天凌晨3點,天還黑著,鄧衛星就起床到肉鋪打理生意;5點,妻子熊廷賀起床,喂雞喂鴨,給幾十個孩子做早飯——夫妻倆的這一作息深深地影響了大兒子鄧文芳。已大學畢業、正在深圳工作的鄧文芳,到現在仍會每天3點醒一次、5點醒一次。
早上10點多,鄧衛星從肉鋪收攤回家,一頭扎進廚房,洗菜、淘米,燒起灶頭。中午,孩子們嘰嘰喳喳地從學校回來了,房前屋后地竄進竄出,幾乎掀翻了天,直到鄧衛星一聲“吃飯了”的吆喝后,才“呼啦啦”捧著飯碗圍到灶邊。給孩子們分完飯菜,看著他們吃完后,鄧衛星夫婦才得空吃上幾口。
下午,夫婦倆到自家的20多畝菜地和橘園忙活,或上山砍些柴回來燒。下午三四點,孩子們放學回來,鄧衛星家迎來了一天中最熱鬧的時光。夫婦倆一邊在廚房炒菜,一邊挨個喊孩子們洗澡,還要隨時抽出手幫年紀小的孩子搓幾下衣服。
吃完晚飯,鄧衛星在堂屋里擺好課桌椅——晚自習開始了。孩子們寫作業的時候,鄧衛星也搬一張凳子坐在旁邊,隨時聽候“衛星伯,這個要怎么做”、“阿爹,這個要怎么讀”的求救。
直到晚上10點多,幾十個孩子鉆進被窩,閉上眼睛,忙碌了一天的鄧家才慢慢歸于安靜。
30年來,“學生之家”走出了904個孩子
30年來,“學生之家”走出了904個孩子,沒有一個有不良記錄。每每說起這些,鄧衛星的臉上總是會揚起幸福的笑容。
家長們把孩子送到鄧家,從不提什么要求。但是,幾十個孩子一口一個“阿爹”、“衛星伯”叫到了鄧衛星心里,鄧衛星自然而然地當起了這些孩子的家長。為了孩子們的安全,鄧衛星給房子裝上了防盜窗
最開始,鄧衛星只要來這里的孩子帶些大米就行。后來,孩子漸漸增多,加上物價上漲,鄧衛星只得收取少量的錢來維持“學生之家”。先是每學期175元,前兩年提到了每學期325元。和當地小學每星期50元的伙食費比起來,這個數字是非常便宜的。
但盡管如此,這里的貧困家庭太多,交不上錢的仍不在少數。鄧衛星有個賬本,上面記著學生家長們的欠賬,還了一筆就銷一筆,可賬本上銷不掉的還是大多數。今年住宿的54個學生中,只有5個學生把錢交了。
為了把“學生之家”辦下去,鄧衛星的日子只能精打細算:豬肉是每天賣剩帶回家的,雞和鴨是自家喂的,一些菜也是自家地里種的,油也是自己用肥肉煸的。雖然后來家里有了社會捐贈的電飯鍋,但電費太貴用不起,鄧衛星仍然用土灶燒飯燒菜。
可即使如此,“學生之家”仍然開銷不菲,每天光20公斤大米的費用就是一筆大數目。粗粗算下來,每學期鄧衛星要墊進五六千元。
鄧衛星記得,最難的是那一年,妻子熊廷賀上山砍柴被車碾了,在醫院昏迷了三四天,治病一下子花掉了2萬元積蓄。眼看兒子也快要念大學了,需要一大筆學費,鄧衛星一籌莫展。
大兒子鄧文芳回憶:“那時連吃的都快買不起了。我爸帶了一口鍋在醫院,每天就帶些菜在醫院煮。后來,80多歲的奶奶來‘學生之家’幫忙,才硬是撐了下來。”
然而,幾十年間,鄧衛星從來沒有向別人發過牢騷、倒過苦水,從來沒有向當地政府、向旁人、向從他這里走出去的孩子們伸過一次手,哪怕他們當中有人已經成了大老板。
30年來,鄧衛星從“衛星哥”變成了“衛星伯”,鬢角漸漸發白,體重越來越輕,從“學生之家”走出去的學生卻越來越多。904個孩子中,有6個上了大學,60多個當了老師,100多個進了部隊,有的自己創業,有的到外地打工,為人父母后又把自己的孩子送回這里。對他們來說,鄧衛星的“學生之家”就是一座永遠可以讓人感受溫暖的小屋。
(摘自《解放日報》) (責編 達溪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