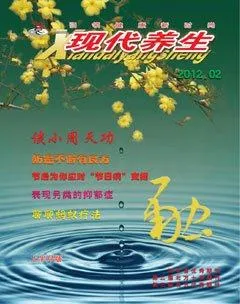話說余熱
不少老干部退休和離休之后,繼續為革命事業作出努力,大家稱之為貢獻余熱。余者剩也,而熱是物理學的名詞,即指大量實物粒子(分子、原子等等)的混亂運動組成的物體。貢獻余熱,這個詞兒用得非常巧妙,因此議論一下余熱。
我們的祖宗是一直講究“余”的。“農有余秉,女有余布”,以及“暖衣余食”,都是古代人民追求的理想和政治清明的反映。人老了,也叫“余年”。石崇說:“高歌凌云兮樂余年。”范成大詩“投老余年豈再來”,盡管意境不同,但以老年為“余年”則是一致的。三國時代魏人董遇,他教授生徒的讀書方法叫“三余”,即“冬者歲之余,夜者日之余,陰雨者時之余也”。利用三余,趕快讀書,其實同我們現在提倡的擠出時間來學習,很有相似之處。不過用他的論點,也正好證明了老者少之余也。投老余年,正如歲之有冬,日之有夜,晴之有雨,是一種極正常的現象,不足怪也。
至于熱,熱心熱腸、熱情熱忱,更是一種入世的象征。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就是不惜犧牲自己把天上的火種送到人間,給人類以光和熱。中國也是一樣,北齊顏之推寫的《顏氏家訓》中就說:“墨翟之徒,世謂熱腸;楊朱之侶,世謂冷腸。”墨子是主張兼愛的,他自己也身體力行“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而那位楊朱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的人,一切都為了自己,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把墨楊之學一對比,正說明熱是一種入世的態度,是人間最寶貴的動力。
以投老余年而不忘卻他的入世,盡余光、余燼而為社會造福,心存家國,澤被后世,這大概就是貢獻余熱的形象。這樣的形象,在我們歷史上是不少的。“太公八十遇文王”,那位姜尚先生,就是用他的余熱,輔助姬氏子孫,開創了周代八百年的天下,而“廉頗老矣,尚能飯否”那位白發蒼蒼的老將軍,當他“負荊請罪”,跪在藺相如面前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多么使人肅然起敬;東漢的馬援,六十二歲了還“據鞍顧眄,以示可用”,“矍鑠哉,是翁也”,這評語今天聽起來,還能激動人心。我小時候喜歡看《征東》,對于那位白袍小將薛仁貴三箭定天山的故事,佩服得五體投地。后來讀唐書,才知道這位將軍的暮年更加可以欽敬。據《新唐書》說,他年近七十之時領兵去抵抗突厥,對陣之際,“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這段故事現在讀來仍覺虎虎有生氣。唐詩所謂“獨立三邊靖,平生一劍知”,也未足以比之。至于在普通人民之中,這種老而彌堅、奮斗不息的故事,更加車載斗量,不勝枚舉。讀讀這樣的歷史,想想這樣的祖宗,確實是可以使每一個老頭子為之眉飛色舞,為之閑不住,坐不牢的。
當然,我們今天的時代不同了,而在我們這塊縱橫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六十歲以上的老頭子竟有八千萬之多,這個數字,使英國、法國、德國的人口瞠乎其后。這也就使我們在發揮余熱這個問題上,比別的國家更要重視一些。我想,余熱余熱,重點還在一個熱字,有了這點子熱,就能有普羅米修斯那種犧牲自己、熱愛人類的精神,就有諸葛亮那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忠于事業的精神。不管在什么崗位上,在什么環境中,有生之年,永遠保持著對黨、對民族和國家的忠誠、熱愛。
余熱余熱,自然也要考慮到那個余字,“渡頭余落日”,“夕陽無限好”,那風景是壯麗的,可是畢竟不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了。因此重要的不在事事親臨前線,舍命爭先,而在于幫著年青的同志健康前進,超過我們,使我們南征北戰、出生入死的事業更加發揚光大,繼往開來,生生不息。老當益壯,固然是好事,青出于藍,卻更富有生機。所以在這一點上,既要保持那點“熱”,也要注意這個“余”;做年青一代的帶路人,不要成為他們的絆腳石;多培養一些接班人,少安排幾個代理人。
人類的發展史告訴我們:人,是從野蠻時代來到文明社會的。幾千年來,盡管歷史上出現過一些黑暗時代,我們也親身經歷了“十年動亂”,但人類要向前發展,年青一代的道路一定比上一代更寬廣,前途一定更燦爛,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懂得這個道理,我們的余熱就能發揮得更好,起到更美妙的作用。
【編輯: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