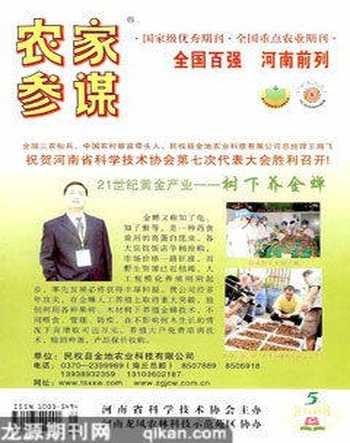雞痘怎樣防治
雞痘是由痘病毒引起的急性傳染病,在夏秋等有蚊季節易發流行,主要通過蚊、蠓等吸血昆蟲的叮咬傳播感染。雞不分品種、日齡大小均易感發病。從病變發生的部位上分皮膚型和白喉型(即黏膜型)兩種,皮膚型主要表現以面部皮膚特別是雞冠、肉髯部位長有痘皰為特征;而白喉型主要表現以咽喉部有假膜干酪樣物堵塞為特征,兩者在臨床上都不難診斷和區分。
一、消除傳播媒介,加強防疫消毒。清除雞舍周圍雜草及積水污溝等蚊子孳生地;噴灑驅蟲劑、驅除蚊、蠓、蜱等吸血昆蟲,給雞舍門窗安紗網等。同時加強防疫消毒,對禽舍、用具用2%燒堿或20%石灰乳噴灑消毒,病死雞焚燒、深埋處理。
二、刺種雞痘疫苗。這是預防雞痘最可靠的方法。使用雞痘鵪鶉化弱毒苗,在雞翅內側無血管處皮下刺種,1月齡以內的雞刺種1針,1月齡以上刺種2針,每刺種一下蘸取一次苗液。痘苗接種時機是在蚊蟲繁殖活躍的前期,山東地區一般在6月底、7月初接種,也可在雞1月齡左右接種新城疫I系苗同時接種痘苗。接種1周后檢查刺種部位皮膚有無痘痂,若無則需要重新接種。
三、對癥治療。雞群中有發現痘疹或結痂的,應隔離病雞做適當處理。對眼部痘瘡用手擠去膿液或干酪物,用2%硼酸水或生理鹽水沖洗干凈,再涂上金霉素、氯霉素眼膏。對面部其他部位的痘瘡,用大蒜泥按1:1的比例加入食醋調稀,涂抹患部,早晚各1次;或用針刺破痘瘡,痘瘡用鑷子剝離,涂碘酊或紫藥水,同時投喂病毒靈藥片,每只雞1片,1天2次,連喂2天,對皮膚型雞痘有特效。
四、白喉型雞痘臨床表現出嚴重的呼吸困難,打開口腔可見咽喉部有黃白色假膜或干酪樣物堵塞。其處理方法是,小心剝離假膜,清除干酪樣物,再涂以碘甘油,或蘸取少許高錳酸鉀水涂擦患部消毒,同時服用喉癥丸3粒,連服2天即愈。
五、大群治療用0.1%土霉素、0.02%病毒靈、0.01%維生素C、0.2%魚肝油一同混料喂給,連用5~7天。
六、中藥治療,每天用綠豆50克、甘草30克煎湯飲水,連服5天。
七、紫草100克、明礬100克、龍膽草50克,水煎可供100只成年雞1日服,連用3天。
八、雄黃、硫璜、冰片等量研粉末兒混合,加碘甘油適量,剝去痘痂涂敷。每只雞約500毫克一次用。
九、魚腥草粉碎拌料,每只成年雞1日用1克,連用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