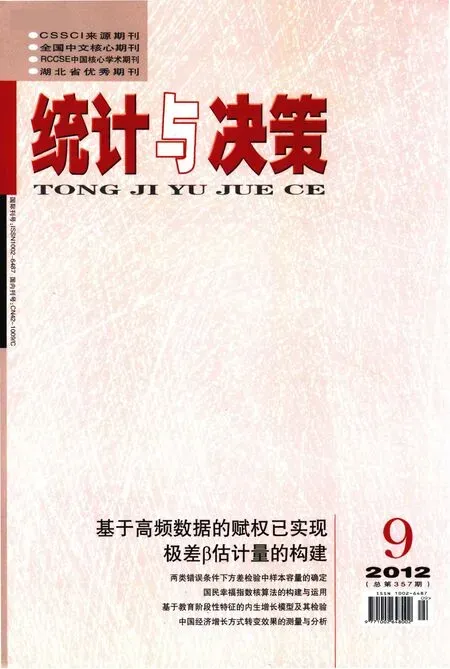中國股市流動性系統風險的測度
黎克俊,姚潔強,黃 峰,沈豪杰
(1.西安交通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院,西安710061;2.浙商銀行總行 風險管理部,杭州310006)
0 引言
作為市場之靈魂,流動性構成了市場的最重要的基石,沒有流動性便沒有了市場。因此對于流動性風險的測度問題就顯得非常重要。近年來,針對流動性風險的研究成為了熱點問題。然而,我們發現對于流動性風險中個體風險和系統風險組成的問題卻鮮有學者關注,而這顯然與系統流動性風險的在實踐中的意義不對稱,特別地,對于投資者來講,系統風險的大小尤其重要,因為系統風險不可能通過投資組合被分散掉,對于流動性系統風險而言亦是如此。
在國外,Chordia,Roll和 Subrahmanyam、Hasbrouck和Seppi[1]以及Huberman和Halka等學者首次對美國股市個股流動性中系統性風險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然而上述學者的研究對象是坐市商制度下的報價驅動交易市場,和我國股市指令驅動交易市場有著很大的不同,他們的研究方法不能夠直接移植到中國股市流動性風險的研究中來,而國內學者宋逢明和譚慧[2]曾利用2001年2月~2002年6月滬深交易所所有A股的高頻交易數據,參考選擇了絕對買賣價差、相對買賣價差、有效買賣價差的絕對值和相對值、以及報價深度作為個股流動性指標,構建了一個市場測度模型對系統流動性進行了檢驗。但是,他們的研究局限于流動性系統性之有無,未能計算流動性共性之大小,也未能深入解釋影響流動性共性之因素。這就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機會,本文旨在構建一種不僅能否測量流動性系統風險有無而且能夠精確計算流動性系統風險大小的模型,以便能夠從根本意義上回應投資者對流動性系統風險的關注。
1 模型的構建
和以往學者不同,本文采用非流動性指標來測度流動性風險的大小。而宋逢明和譚慧[2]則沿用了Chordia,Roll和Subrahmanyam[3]以及Brockman和Chung[4]的流動性共性檢驗模型,采用了買賣價差和報價深度指標來測度流動性風險,其中流動性變量是前后交易日的流動性水平的變化率。一般地,當變量的時間序列存在單位根時才有必要進行差分處理,而對一個平穩的變量進行差分處理會造成過度差分,反而有可能使變量產生自相關。包括價差和深度指標的流動性指標一般都是平穩的,因此理論上,簡單地前后交易日差分處理是不恰當的。因此,上述計量方法存在很大的缺陷,因此,本文提出了直接利用流動性水平變量進行系統性檢驗的改進方法。
1.1 非流動性指標的構建
采用日非流動性指標表示每個股票和市場組合每個交易日的流動性水平,該指標由黃峰和楊朝軍[5]提出,并在其實證研究中取得了較好效果。非流動性指標的計算方法是單位時間內單位成交金額所引起的價格振動幅度:

其中,illjt表示j證券在第t日的流動性,Vjt表示第t日內所完成的成交金額,是股票j在第t日的價格振幅(即(當日最高價-當日最低價)/當日開盤價),價格振幅是以百分比表示的。從上式可以看出,若t日內、單位成交金額所引起的價格振幅越大,則表示流動性越差,即非流動性越大,所以我們又稱該指標為非流動性指標。
市場組合的日非流動性指標是樣本股的日非流動性指標的等權重平均:

其中Ntd是第t月內的第d日的樣本股個數。
1.2 個股流動性風險的共性占比的測度模型
因為在指定流動性水平的代理指標即非流動性指標之后,用該指標衡量的流動性水平的波動方差是對流動性風險的度量,所以把個股流動性方差分解為與市場組合流動性的方差相關的部分和無關的部分,即系統風險部分和非系統風險部分,就能夠估計出其中系統風險部分占比。我國股市絕大部分個股流動性都是與大盤同步運動,所以我們用如下模型對個股流動性與市場流動性之間的關系進行擬合估計:

illj,t表示股票j的非流動性大小,aillt表示市場組合的非流動性大小。cj為截距項,βj為個股非流動性的敏感系數,反映了個股非流動性中隨市場整體非流動性變化而變化的系統性部分。假定ej,t的條件均值為零,方差有限,表示與aillt不相關的殘差項,因此它將隨著投資組合中股票數量的增多和權重的分散而趨于相互抵消掉。對方程兩邊求方差,則:

2 數據選擇和實證分析
2.1 數據選擇
我們從Wind資訊金融數據庫選用中國滬深股市的日交易數據進行流動性分析,我們選擇的樣本期間是1995年1月3日到2010年12月30日,共3886個觀測日。首先我們選取了2004年6月以前上市的股票。由于我國股市曾長期存在的操縱、關聯交易和莊家對敲等違規交易行為對實證分析市場流動性行為產生阻礙,因此為盡量減小統計誤差,我們又對股票按下列標準進行了精心地選擇:
(1)研究期間內的股票剔除了特別處理(ST)股、特別轉讓(PT)股和長期停牌股票,這是為了盡量去除我國股市長期存在操縱、關聯交易和莊家對敲等違規行為對實證分析的影響。而且,ST股和PT股的日漲跌幅限制是5%,而其它股票則是10%,剔除這些股票也是為了不讓交易規則差異影響我們的分析結果。
(2)我們把被媒體曝光以及曾發生連續三個以上跌停板但當時公司經營狀況沒有明顯變化而且與整個大市走勢不相符的股票以莊股對待而剔除掉。
(3)為正確反映本文所涉及的收益率變量,個股收盤價都是對派息、送配股和增發新股等進行復權調整后的價格。
(4)剔除股票剛上市交易第一個月的數據,并且如果在某個月內的交易不足15天則剔除該股票在此月的數據。另外,用非流動性指標表示流動性水平,則須剔除交易全天都封在漲跌停板價格的數據,因為該交易日的非流動性值計算會是零,不能反映實際的流動性水平。
這樣處理后,研究期間內歷年共有136個代表性股票達到以上條件。這些樣本股票代表了研究期間內各時期的整個市場組合,而個股研究對象是上述已選定的1996年以前上市的136個股票,這樣能保證每個股票都有足夠長的流動性交易數據進行回歸分析。
136個股票中50個是深市股票,其余86個為滬市股票,屬于滬深300指數成分股的股票有46個。按照MSCI和S&P聯合發布的全球行業分類標準(GICS),136個股票分屬八個不同的經濟部門大類,見表1。

表1 GICS標準下136個樣本股票所屬的經濟部門
這136個股票代表了不同行業和地域的上市公司,盡管樣本數量較少,但已經對滬深股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36只個股樣本的日非流動性指標數據(共421801個觀測值)的基本統計特征見表2。

表2136 只個股樣本非流動性指標的日數據基本統計量(1996~2010年)
2.2 實證結果
2.2.1.個股流動性風險系統性占比的經驗估計
使用上述的136個股票樣本數據來衡量我國股市的個股流動性風險共性占比。按照方程(1)對1996~2010年之間的每個股票分別進行估計的結果見表3。

表3 個股流動性風險中系統性占比的估計結果
表3顯示,流動性系統風險的比例平均為0.421,與孫培源和施東暉[6]計算的股票價格波動風險中系統性部分的平均比例(0.392)差不多相等,孫培源和施東暉估計股價的系統性風險時用的方法與本文類似,這也是多數文獻采用的基本方法,考慮到方法上的可比性,所以引用孫培源和施東暉的估計結果。由此看,我國股市的個股流動性風險中有接近一半的部分能被市場組合的流動性風險解釋。
為了檢驗上述估計結果的穩定性和考察不同發展階段的差異,我們把整個樣本按時間先后分為前后兩個子樣本:一個是1996.1.2日到2000.12.30日,另一個是2001.1.2日到2010.12.30日。估計結果見表4和表5。

表4 個股流動性風險中系統性占比的估計結果(子樣本:1996.1.2~2000.12.30)

表5 個股流動性風險中系統性占比的估計結果(子樣本:2001.1.2~2010.12.30)
對比表4和表5,均值水平由1996~2000年期間的0.495降到了2001~2010年期間的0.297,盡管系統風險比例仍然不小,但下降幅度還是比較明顯的。為判斷這個下降幅度在統計上是否顯著,我們需要求出前后均值水平差值(即14個百分點)的t統計量,計算公式為:


其中,Rj,t0和Rj,t1分別指股票j在前一子樣本期間和后一子樣本期間的系統風險比例的估計值。
由公式(3)和(4),前后均值差的t統計量為6.739,在雙尾1%水平上顯著。因此,2001~2010年期間我國股市的流動性系統風險的比例顯著地下降了。為了結論的穩健性,筆者還把母樣本劃分為更多的子樣本(子樣本要求至少有一年的交易數據)進行同樣的回歸,結果顯示在2001年之前的那些子樣本回歸取得了一致的估計結果,而2001~2010年期間的子樣本回歸結果則基本一致,即系統風險比例在2001年之前各子樣本基本在40%以上,而在2001~2010年期間各子樣本都降到了30%左右。
和美國市場流動性系統風險占比21.7%及香港市場流動性系統風險占比23.8%相比,我國的流動性系統風險占比仍然較高,這可能是因為滬深股市特有的“政策市”特點決定了中國股市的波動率較高,特別是我國處于市場建設初期的特殊階段,很多小市值公司容易被冠以各種題材概念(例如殼資源、資產重組等)而受到過度炒作。但不管怎么講,系統風險比例的下降也為投資者通過組合投資把流動性風險盡量分散掉的愿望提供了越來越大的可行性。
2.2.2 流動性風險結構改善的原因
滬深股市流動性系統風險的下降可能來自于“飛向流動性”行為的影響,Amihud,mendelson和Wood[7]認為,整個市場流動性變差的時候,投資者將偏好持有流動性相對好的股票,會把投資從流動性差的股票轉移到流動性好的股票中去。這將導致流動性相對好的股票在受到系統經濟因素影響而流動性下降的同時,還受到相反作用方向的“飛向流動性”行為的影響而緩解了流動性下降趨勢。
用136個股票在某段期間內的日非流動性平均值作為各個股票在該段期間內的非流動性衡量值,則在子樣本1996~2000年期間里,股票的非流動性大小與股票的流動性系統風險比例之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為-0.008,對應的雙尾p值為0.93,Spearman等級相關系數也只有-0.03,對應的雙尾p值為0.65。因此,在2001年之前,股票的流動性系統風險占比與自身的流動性好壞、規模大小沒有關系,股票的流動性價值體現不出來。
而在子樣本2001~2010年期間,股票非流動性大小與股票的流動性系統風險比例之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為0.31,對應的雙尾p值為0.000(小數點三位后舍去),Spearman等級相關系數則有0.36,對應的雙尾p值為0.000。因此,在2001年以后,股票的流動性系統風險占比已經開始與自身的非流動性水平正相關,流動性越差的股票則流動性系統風險占比傾向于越大,而流動性好的股票則得到投資者青睞而受大市影響程度小,顯示出投資者的“飛向流動性”行為。因此,股票的流動性價值已經開始拉開差距。
當把2001年前后兩個子樣本里每個股票的流動性系統風險比例進行相減,然后計算這些變化量和股票的非流動性大小之間的相關系數,可得Pearson相關系數為-0.33,對應的雙尾p值為0.000(小數點三位后舍去),Spearman等級相關系數則有-0.35,對應的雙尾p值為0.000。這說明,股票的非流動性越小(流動性越好)則系統風險比例在2001~2010年期間減小的傾向越大,這進一步驗證了投資者存在“飛向流動性”的行為。由此得出一個結論:整個市場流動性風險結構的改善更多是來自那些流動性好的股票。
3 結論
對投資者來說,流動性系統風險有多大是一個影響證券投資收益的重要問題。本文針對我國股市的特殊性,修正了Chordia,Roll和Subrahmanyam、Brockman和Chung以及宋逢明和譚慧用于系統性檢驗的流動性變量處理方法,采用非流動性指標,對比印證了滬深股市存在顯著的系統性流動風險,所不同的是,我們的檢驗簡便易行和更為準確,實證結果發現:在滬深股市的個股流動性風險結構中,在1996~2001年期間系統風險占比平均為0.495,而到了2001~2010年期間系統風險占比降到了0.297,流動性系統風險的下降的原因來自于“飛向流動性”行為,流動性越好的股票,其系統風險占比在2001~2010年期間的下降幅度越大,越傾向于具有較小的系統風險比例,顯示出投資者“飛向流動性”的行為特征。
[1]Hasbrouck,J.,Seppi,D.Common Factors in Prices,Order Flows and Liquidity[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1,(59).
[2]宋逢明,譚慧.訂單驅動型市場的系統流動性:一個基于中國股市的實證研究[J].財經論叢,2005,(3).
[3]Chordia,T.,Roll,R.,Subrahmanyam.A.Commonality in Liquidity[J].Journal of Financal Economics,2000,(59).
[4]Brockman,P.,Chung,D.Commonality in Liquidity:Evidence from an Order-driven Market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2002,(25).
[5]黃峰,楊朝軍.流動性風險與股票定價:來自我國股市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07,(5).
[6]孫培源,施東暉.基于CAPM的中國股市羊群行為研究——兼與宋軍、吳沖鋒先生商榷[J].經濟研究,2002,(2).
[7]Amihud,Y.,Mendelson H.,Wood R.A.Liquidity and the 1987 Stock Market Crash[J].Portfolio Management,199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