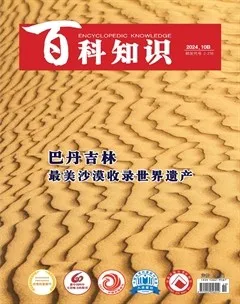光變:夜不眠的生態效應
地球的自轉帶來了日夜交替,在演化的過程中,各類生物均適應了這種周期性變化。從宏觀角度來看,地球上白晝與黑夜的時間大致相等。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通過各種方式延長了光照時間。如今,城市和鄉村的照明設施日益完善,許多國家的都市地區已經實現了全天候的照明,幾乎消除了黑夜。然而,持續的夜間光照對人類和其他生物演化的影響尚未被充分理解。
最近,中國科學院大學的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研究,發現北京城市路燈旁的樹木葉片遭受的蟲害損失比農村地區的樹木要少。為了更準確地評估這一現象,研究人員對北京30個不同地點的180棵受路燈照明影響的樹木進行了觀察和研究。他們測量了每棵樹接收到的光照量,其中一些樹靠近發出特有橙色光芒的鈉路燈,還有一些樹在夜晚幾乎完全處于黑暗中。接著,研究人員分析了近5500片葉子的多種特性,如葉片的韌性、氮含量、鞣質含量和水分含量等。
通過研究這些植物的特性,研究人員可以更好地理解植物如何適應環境并維持生存。鞣質,又名單寧,是植物細胞中的一種防御性化學物質,能夠封鎖蚜蟲的口腔,阻止它們侵害植物,同時也能保護植物免受紫外線的傷害。在自然光照條件下,植物會將能量投入到自我防御中,變得更堅韌,并增加鞣質等化學物質以進行化學防御。研究發現,夜間人工光照越強,城市樹木的葉片就越堅韌。在人工光照最強烈的地區,樹木的葉片最為堅韌,并且沒有被昆蟲食用的跡象。
這種現象得到了其他科學研究證據的支持。例如,日本科學家發現,槐樹的葉子在有路燈照射的區域受損率僅為2.1%,而在黑暗區域則高達5.3%。同樣,美國科學家發現,賓夕法尼亞州的綠梣樹在路燈附近的葉子的受損率為2%,而在黑暗區域則為4.1%。不過,研究人員指出,光照減少了昆蟲對葉子的取食,會導致昆蟲和鳥類能量輸入減少,這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進而影響該地區的生物多樣性。此外,長時間光照使樹葉變得更堅韌,可能會減緩葉子的分解過程,從而改變樹木下方和周圍土壤的化學成分。
2021年,英國生態與水文中心、紐卡斯爾大學等機構合作的一項研究顯示,新型LED路燈對昆蟲的影響更為嚴重。與未照明區域相比,鈉路燈使樹籬中的飛蛾幼蟲數量減少了41%,而LED路燈使飛蛾幼蟲數量減少了52%。研究人員推測,路燈可能干擾夜間飛蛾的產卵行為,并增加它們被蝙蝠等捕獵者發現和捕食的風險。英國鳥類信托組織也發現,生活在人造光源附近的知更鳥和烏鴉等鳥類會在夜間鳴叫和覓食,而生活在路燈附近的藍山雀則會提前幾天產卵。
在古代,由于缺少人工照明,人們的生活遵循著自然的節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隨著人造光源的普及,人類的活動不再受限于日光,在夜間工作成為可能,極大地提升了生產力和產出。同時,這也意味著人們越來越多地暴露在人造光源之下,即使不在夜間工作,現代網絡和信息技術的普及也讓人們在人造光源中度過更多的時間。這種光照時間的增加,無疑會對人類的生理和健康產生影響。
以往的研究已經表明,長時間暴露在人造光源下與肥胖風險的增加有關,增幅為13%~22%。基于這些發現,研究人員開始懷疑這種暴露是否同樣會增加人們患糖尿病的風險。最近,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和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的研究團隊發表了一項研究,為這一疑問提供了肯定的答案。研究人員利用1300萬小時的光傳感器數據,深入分析了個體光照暴露的具體模式與2型糖尿病發病風險之間的潛在聯系。
研究結果發現,夜晚(00:00—06:00)暴露在人造光源下且光照亮度更高的參與者,患2型糖尿病的風險更高,二者呈正相關關系。與夜間光照暴露為0~50%的參與者相比,夜間光照暴露為90%~100%、70%~90%和50%~70%的參與者患2型糖尿病的風險更高。與夜間光照暴露水平最低的參與者相比,夜間光照暴露水平更高的參與者患2型糖尿病的風險增加了67%。
這項研究還發現,白天(07:30—20:30)暴露在自然光的強光之下,患2型糖尿病的風險更低,二者呈反向相關關系。相比于白天光照暴露為0~50%的參與者,白天光照暴露為90%~100%、70%~90%和50%~70%的參與者患2型糖尿病的風險更低,這表明,自然光可能對人更有益。
糖尿病的成因復雜多樣,要準確評估光照對該病的影響,必須先排除其他潛在的風險因素,如心血管代謝風險因素、睡眠質量和時長、晝夜節律模式、光照周期、心理健康狀態以及夜班工作的影響。在這些因素得到控制之后,研究顯示,較長的夜間光照時間與2型糖尿病的發病風險增加呈現正相關。此外,該研究還證實,夜間光照時間的延長導致糖尿病風險上升,與晝夜節律的紊亂密切相關。
關于糖尿病和肥胖,科學家提出過“節儉基因”假說。根據這一假說,在人類早期的演化過程中,由于生產力有限,人們往往會在食物充足時儲存更多的脂肪,以便抗過饑荒時期。然而,在現代社會,這種基因傾向可能導致人們更容易積累脂肪,從而增加了罹患糖尿病的風險。與之類似,古代人類每天僅受到大約12小時的自然光照,而現代的人造光源卻使得人體受到光照的時間可延長至全天24小時,這擾亂了人體的正常生理節律。因此,光照變化可能成為誘發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重要因素。
此外,科學家還發現,與人造光源相比,暴露于自然光照下不僅有助于降低肥胖和糖尿病的風險,還能預防近視。科學研究表明,青少年每天在戶外自然光照下活動至少1小時,可以顯著降低近視發生的風險。可見,平衡自然光和人造光源的暴露時間,維護健康的晝夜節律,對促進現代人類健康具有重要意義。
【責任編輯】張小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