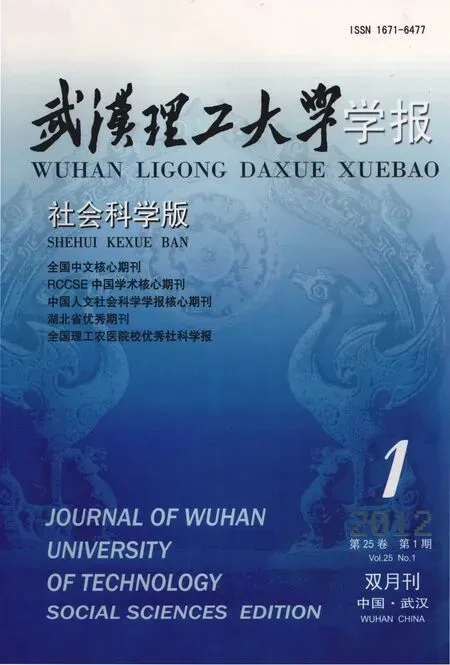農村信用社、國家與農貸悖論*
易棉陽,曾 鵑
(湖南工業大學商學院,湖南株洲412008)
一、引 言
作為合作金融組織,中國農村信用社自其產生以來,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視以及民間和學界的關注。可以說,農信社在中國存在了多久就改革了多久,然而中國農信社不僅始終達不到改革的預期效果,而且還內生出農貸悖論的現象。農貸悖論命題可作如下概括:本該服務于“弱勢群體”的農信社,卻沒有為弱勢者服好務。在發達國家,農信社是一個能為“弱勢群體”提供有效金融供給的制度安排,為何在中國卻出現“好而無用”的結局呢?
對于中國歷史上的農貸悖論現象,近年來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張杰對存在數千年之久的農貸制度進行了長時段的考察,認為國家農貸有這么一個悖論:要么強制均攤,要么就是最不需要錢的人最能貸到錢。現今的農信社作為國家持牌金融機構,也跳不出農貸悖論的怪圈,農信社陷入這種困境的根源在于國家一直試圖讓其提供商業性農貸[1]。謝平以西方經典合作理論為標準考量中國農村信用社,發現建國以來中國就不存在合作制生存的條件,農信社不是真正的合作組織,離農就商乃題中應有之義[2]。易棉陽認為近代中國農業金融在轉型過程中內生出兩種悖論性現象:一是近代農業金融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但農民得利甚少;二是近代農業金融遏制了舊式高利貸但制造了新式高利貸[3]。易棉陽在較為全面地考察抗戰時期四聯總處農貸政策后,認為四聯總處之農貸政策也滋生了農貸悖論現象:即農貸促進了大后方農業生產發展,但廣大真正需要農貸資金的貧困農民卻得利甚微[4]。這些文獻有的不乏理論創見,給我們思考農信社為何產生農貸悖論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啟示,有的研究了歷史上的農貸悖論,為解釋現時農貸悖論現象提供了參考。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特別是經濟制度問題,必須以該制度在中國的變遷為分析起點,才能弄清楚該制度在中國何以失效?本文以中國農村信用社長期的運作績效為實證材料,試圖從剖析農信社與國家關系的視角,來揭開農信社為何在中國會內生出農貸悖論的謎團。
二、農村信用社與國家關系解構
描述建國以來農信社的演變史跡,是解構農信社與國家關系的邏輯起點。農信社的演變歷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①。
第一階段(1949年—1957年)。在這一階段,在國家力量的推動下,農信社在全國普遍建立。土改完成以后,分得土地的農民無錢購置生產工具和改良土壤,生產資金的短缺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難以付諸實踐。在此背景下,政府決定通過發展農村信用合作來破解資金短缺難題。1951年—1953年,農村信用社穩步發展。從1953年起,農信社作為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國家力量的推動下,短期內得到飛躍發展。截至1956年,全國農村信用合作社達到16萬個,97.5%的鄉建立了信用合作社,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了信用合作化[5]。
第二階段(1958年—1978年)。這一階段農信社成為官辦金融機構。1958年—1961年大躍進期間,農村信用社被改組為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的信用部,成為基層政府的一個內部機構。1962年開始調整國民經濟,信用社恢復成立并脫離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的基層機構,此種狀況維持到1968年。1969年—1976年,在極“左”思潮的干擾下,農信社被下放給貧下中農管理委員會管理,農信社業務經營陷入混亂狀態。十年動亂結束后,金融行業撥亂反正,農信社再次收歸中國人民銀行管理并成為其基層結構。
第三階段(1980年—今)。這一階段是政府主導下的農信社改革時期。1980年—1995年的改革,目的在于恢復農信社的“三性”,即組織上的群眾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經營上的靈活性。因農信社歸中國農業銀行管理,所以這個階段的改革由中國農業銀行領導實施。1996年行社脫鉤,1996年—2002年的農信社改為中國人民銀行領導,主要目標是要恢復農信社合作制,但效果不盡人意。2003年啟動的新一輪農信社改革,不再堅持合作制改革取向,此輪改革從產權入手,因地制宜,可以實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也可繼續完善合作制。
從建國以來農信社的演變史跡中,我們清楚地看到,農信社每走一步,幾乎都是由政府在推動或主導。那么,國家為何對農信社具有如此強烈的控制欲呢?處在農業化階段或工業化初期階段的中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經濟剩余是國家生存乃至發展之本。問題是,如何確保農業產生更多的剩余呢?政治精英們認識到,資金稀缺是中國農村殘破的基本經濟因素。只有保證發展農業所需的最低資金供給,農業才能產生剩余。資本逐利的本性和交易費用的高昂,驅使商業性金融機構對農貸望而卻步,城市金融機構不愿下鄉,植根于農村的信用社,國家若不加以控制,農村勢必出現國家農貸真空,這對維持農業發展是非常危險的。反過來,國家若控制了農村信用社,農業便能比較方便地獲得國家的資金支持,農業剩余具備了一個產生的前提。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即便是最困難的時期,農村中也并非完全赤貧,農民節衣縮食后余下的少量資金,如何才能為國家所掌控呢?理性的農民自然愿意把自己的保命錢交給有國家信用作擔保的金融機構,農村信用社自然是最理想的選擇,國家也最愿意看到這種結局。長期以來,大量的農村資金就是農村信用社集中起來去支援工業與城市建設,這種狀況即使到現在也沒有徹底改變。
農村信用社是否有向國家靠攏的追求呢?應該說,謀求獨立發展是當年合作經濟創始者的設想,為此,羅虛戴爾先鋒社曾制訂了對政治嚴守中立,嚴拒政府援助的辦社原則。但后來信用社的實踐卻證明這條原則是一個不存在性命題。由民間發明和推動的誘致性制度,政府的態度決定著其生死存亡,這在政府有著強烈控制欲望的中國則顯得尤為重要。20世紀20年代后期,中國信用社的蓬勃發展曾使政府感到莫大的恐慌,若不是一部分政治精英看到了信用社的可用之處,信用社可能在20世紀20年代就被扼殺在襁褓之中。當下我國農村廣泛存在標會、搖會、合會等民間合作金融組織,因得不到政府的允許而只能以地下金融組織狀態“灰色推進”。在社會主義國家,私營經濟、合作經濟、集體經濟、國有經濟四種不同經濟成分具有不同的政治經濟地位,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體經濟,合作經濟在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面前低人一等,但比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則高過一頭。于是,合作向集體過渡,集體又向全民靠攏,便成為一種必然的現象和規律[6]。比如,在1980年以前,信用社是國家銀行的基層機構,信用社職工享受與銀行員工相同的待遇,1980年開始的農信社改革,旨在改變過去的官辦性質,把農信社辦成群眾的合作金融組織,為使改革順利推進,中國農業銀行宣布“兩個不變”作為改革的前提條件,其中的一個“不變”就是“信用社職工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與銀行職工一致”不變。但這種“一致”僅局限于老員工,新增員工則不轉城鎮戶口,不吃商品糧,不拿固定工資,根據業務發展情況確定合理報酬。此種待遇差別引起新增員工的不滿,他們寧愿報酬少一點也要謀求編內員工身份。若從經濟上考察,可以發現,農信社的產權制度安排也決定其在發展階段離不開政府的扶植。農信社的初始產權結構由社員入社股金和經營中所積累的公積金組成,作為弱勢者的農信社社員,所納股金少則幾元多亦不過數十元。作為合作金融組織的農信社,互助是其經營宗旨,盈利能力差,所積公積金額少量寡。顯然,依靠自身的積累,農信社沒有很強的自生能力。而政府的資金扶助往往能推動信用社超常規發展,國民政府時期信用社的運營資金幾乎全部來自國家銀行,當前我國信用社的產權積累中也有相當部分源自國家財政資金。其實,發達國家合作金融組織亦是如此,如美國聯邦土地銀行1916年初建時資本總額900萬美元,其中政府出資889.2萬美元,直到1920年聯邦土地銀行才還清政府的出資。再如日本農林中央金庫在1923年建立時,政府就出資20億日元,直到1961年農林中央金庫才還清政府的全部資金[7]。
三、農貸悖論:表現形式與形成機理
農村信用社因解決小農信貸難題而產生和發展,中國農信社之所以長期以來績效不盡人意,根本性的因素恐怕就在其農貸運作偏離了合作金融組織的宗旨。進一步探討,便可以從長期的農信社演變史跡中抽象出一個農貸悖論命題,這個命題可概括為:本該服務于“弱勢群體”的農信社,卻沒有為弱勢者服好務。
“離農”是當代中國農信社農貸悖論的具體表現形式。農信社的“離農”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農信社收縮農村據點,大舉“進城攀親”;二是農貸業務萎縮。1980年—2004年的20多年間,農信社的農業貸款每年平均僅占其貸款總額的30%左右,70%的貸款流向非農產業;三是不為真正需要貸款的廣大社員服務。農信社的非社員貸款長期占其農戶貸款總額的50%以上,農戶向農信社貸款難。隨機抽取1996年—1998年三年農戶借款來源數據,1996年農戶從農信社的借款額占農戶借款總額的比重為17.96%,1997年、1998年分別為18.12%、13.12%,而75%左右的借款來自民間私人借貸[8]。
“農貸悖論”的形成機理可以從中國農村信用社管理制度的循環組織結構中探尋。

圖1 農信社管理制度的循環組織結構
圖1所示,社員、社員大會、經理層三者之間實行循環管理是農信社在管理制度上的一個顯著特征。但在中國農信社的管理組織結構中,社員和社員大會卻長期缺位,社員和社員大會不對農信社實施監督管理。造成這個結局的原因還得從建社之初說起,由于農村信用社是20世紀50年代靠政府意志按行政村普遍建立起來的,所以,人人是社員,但產權經濟理論早已表明,人人是社員實際上就是人人都不是社員,農信社中社員產權主體成為虛置。社員主體虛置,社員大會自然名存實亡。盡管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府一直致力于真正讓社員和社員大會對農信社行使管理權的改革,但始終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效,原因很簡單,社員犯不著為幾元或幾十元股金而花費成本對農信社實施管理,放棄管理比行使管理更加劃算[2]。長期以來,作為農信社直接管理者的經理層(即農村信用社的理事長、主任),實際上是屈從于地方政府的選擇和任命,甚至是農村信用社省級聯社“調兵遣將”“挪棋子”排兵布陣的結果,并將農村信用社理事長、主任納入行政科層結構安排與管理,因而強化了縣級農村信用社理事長、主任的“行政化”、“官員化”。因此,農村信用社理事長、主任的較多決策,一方面難以真正基于市場與合同決策;另一方面又難以真正從有利于服務“三農”角度來決策[9]。
按國內學者的總結,由合作制原則演化而來的合作金融制度,其區別于商業性金融制度和政策性金融制度的質點在于產權制度、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三個方面。具體講,自愿入股,民主管理,為社員服務是合作金融制度的本質特征。據此看來,中國農村信用社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合作金融組織[10]。建國后組建農村信用社的指導思想實際上不是蕾發巽或舒爾茨主義,而是列寧在《論合作制》所倡導的合作原則②,合作組織的樣板就是蘇聯的集體農莊,盡管后來中國農村的政治組織、經濟組織與蘇聯集體農莊有著明顯的區別,但在主政者心目中預設了一個比較理想的模式,就是受國家控制的蘇聯式集體農莊[11]。20世紀50年代一夜之間在全國普遍設立的農信社,仍是政府強制推行合作運動的產物。靠政治運動建立起來的合作社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以國家意志替代了民眾的自愿,換言之,它是沒有自愿的合作,是強制的捏合。胚胎時就沒有培育成自愿合作基因的信用社,在成長過程中再嵌入合作含義,只會產生表內不兼容的結局。20世紀80年代以來,歷次由國家主導的企圖恢復農信社合作性質的改革,最后都無功而返,就是有力的印證。
深究發現,農村信用社一旦被國家控制,這種局面就會內生出兩個破壞合作金融制的因子——踐踏民主管理制度和為社員服務的分配制度。原因很簡單,權吏要掌控信用社,必先剝奪社員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決策權。至于信用社為不為社員服務,很大程度取決于權吏的態度,一個不幸的結局是,大多數情況下信用社非但不為社員服務而且還假手信用社侵犯社員的利益。倘若農信社為政府所控制,農信社實際上就被賦予了雙重目標:一是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在第一個目標實現的前提下兼顧社員利益的滿足。但在絕大多數時候,農村信用社是為了實現第一個目標而運作的,而國家要達到這個效果,必須閹割社員對信用社的管理權,不但如此,社員在信用社的產權收益都難以獲得,遑論從信用社得到優惠服務了。
四、農貸悖論的破解
國家在經濟活動中應該或者實際上起著什么樣的作用?學界對此給出了三種不同的答案。古典經濟學循著斯密“看不見的手”原理,把國家看成一只“無為之手”,認為國家除了提供國防、治安、維持和執行合同等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外,國家不應該再去干預經濟活動。福利經濟學則按照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理論,把國家看作是一只“扶持之手”,在福利經濟學家看來,市場并非如古典主義者所描繪的那樣是萬能的,市場也會失靈,如壟斷和信息不對稱,并且,市場失靈會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國家的干預則正好可以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從而增加社會福利。顯然,在福利經濟學的國家理論中,國家總是善意的,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是其目標。近年來奧爾森③等通過對歷史上國家行為的解讀,發現國家的行為并非總是出于善意,即為了增加社會福利,國家也有其自身的利益,并會使用所固有的強制力來謀求自身利益,國家的此種行為使其成為了“掠奪之手”。奧爾森形象地把國家比喻為具有掠奪偏好的“坐寇”。施萊弗(Shleifer)[12]循著奧爾森理論進行進一步的深究,發現國家并不總是謀求長遠利益,往往為了實現其當前和短期利益,而不惜進行過度掠奪。三種不同的答案,對國家進行了立體的多維解讀,使人們對國家的認識更加符合現實。歷史和客觀地看,國家大多數時候是同時扮演著三只手的角色,在市場自己能良好運行而不需國家過多干預的領域,國家甘當無為之手;在面對危及統治的利益集團時,國家會重拳出擊,起到扶持之手的作用;為了實現某一特定的目標或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時,國家就可能是一只掠奪之手[13]。
在中國農村信用社里,國家長期以來就是扮演“掠奪之手”的角色。國家首先通過掠奪社員在農信社的股權繼而掠奪社員對農信社的管理權。遭受掠奪之后的農信社不為弱勢者服務成為順理成章之事。既然如此,破解農貸悖論的關鍵在于正確界定國家在農村信用社的行為邊界,具體講,就是國家對農村信用社是選擇抓還是選擇放。基于此,本文提出兩策:第一策,國家退出信用社。從美國、日本、臺灣的農貸實踐中,我們得到啟發,在農村信用社的創立與發展階段,國家給予資金的支持是必要的,但當農村信用社具備了自生能力之后,國家應該退出其全部股權,不再干預農村信用社的微觀經營活動,讓來源于民間也只有在民間生存才能壯大的農村信用社真正“回到民間”,把農信社真正改制成具有民有、民辦、民享、自主、自治、自助特征的合作金融組織。第二策,國家控制信用社。中國的農村信用社是國家通過外力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國家不僅搭建好了農村信用社的構架,而且控制了絕大部分產權,留給民間的實際上只有些許產權空隙。長期以來,農村信用社被迫打著合作金融的幌子執行商業信貸的實質,國家一直在讓農村信用社為其提供商業性農貸,名不符實使得農村信用社蒙受諸如“離農”、“商業化”等種種責難,若把農村信用社干脆轉制為國家控股的商業性農村金融機構,也不失為明智的選擇。
注釋:
① 建國以來農信社的演變歷程,詳情參閱易棉陽、陳儉:《建國以來農村信用社的發展路徑與制度反思》,《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② 1951年9月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農業互助合作決議草案》和同年11月毛澤東發表的《組織起來》是指導中國合作運動的綱領性文獻,而這兩篇文獻的思想來源即為列寧的《論合作制》。在實踐中,農信社不是按雷發巽主義或舒爾茨主義把農信社辦成一個獨立的合作金融組織,而是把它與銀行捆綁在一起。毛澤東把農信社與銀行之間的關系比喻為“信用社有了頭,銀行有了腳”的頭腳關系,鄧子恢把農信社看成是銀行的“前線部隊”,銀行是農信社的“后臺老板”。詳情請參見盧漢川等著《中國農村金融四十年》,1991年由學苑出版社出版,具體見第491頁和第47頁。
③ 奧爾森的國家理論集中在他的三本著作中:Olson,Mancur,1965,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Olson,Mancur,1982,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Olson,Mancur,2000,Power and Properity: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New York:Basic Books.
[1] 張 杰.解讀中國農貸制度[J].金融研究,2004(2):1-8.
[2] 謝 平.關于農村信用社改革的幾個問題[J].金融研究,2005(1):24-31.
[3] 易棉陽.近代中國農業金融的轉型及其特點[J].福建論壇,2008(1):52-57.
[4] 易棉陽.抗戰時期四聯總處農貸研究[J].中國農史,2010(4):76-87.
[5] 唐 海.新時期農村信用社改革工作指南[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14.
[6] 孔祥毅.百年金融制度變遷與金融協調[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334.
[7] 成思危.改革與發展:推進中國的農村金融[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255,269.
[8] 馬忠富.中國農村合作金融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138.
[9] 何廣文.農村信用社制度變遷:困境與路徑選擇[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9(1):50-54.
[10] 于 海.中外農業金融制度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205-207.
[11] 白欽先,秦援晉.“退而更化”:中國合作金融改革之路[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7(6):3-9.
[12] 施萊弗,維什尼.掠奪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理[M].趙紅軍,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13] 王一江.國家與經濟[M]∥吳敬璉.比較:第18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