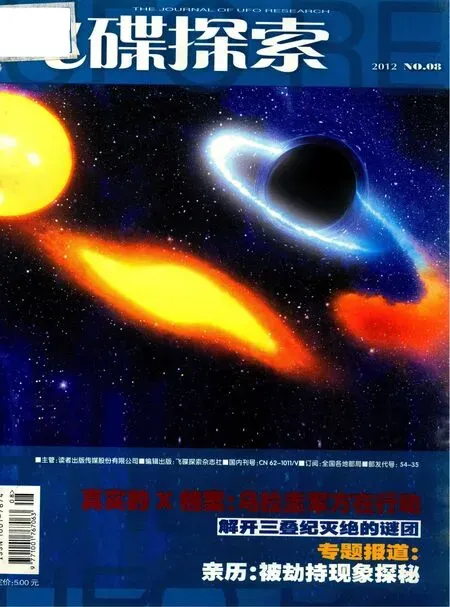誰控制著生態平衡?
■方舟子
誰控制著生態平衡?
■方舟子

一般人只知道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奠定了進化論的基礎,不知道這部著作還蘊含著許多重要的現代生物學思想。例如,雖然還要過許多年“生態學”一詞才由德國生物學家海格爾發明,但是在《物種起源》的第三章,為了說明“自然等級相去甚遠的植物和動物是如何被一張復雜的關系網聯結在一起的”時,達爾文已舉了一個有趣的生態平衡的例子,被認為是科學史上對生態系統的首次描述:三色堇和紅三葉草必須依靠土蜂來受精,如果土蜂滅絕了或變得極稀少,三色堇和紅三葉草也會變得極稀少或全部滅亡。任何地區的土蜂數量很大程度上是由田鼠的多少來決定的,因為田鼠會毀滅蜂窩。而眾所周知,老鼠的數量又大部分決定于貓的數量。因此,一個地區的貓的數量,竟可做考慮。)如果各個成員的數量基本維持不變,我們就可以說達到了生態平衡。這三類成員的數量多少又是互相牽制的:植物的數量取決于陽光、土壤、空氣狀況,但是也受到草食動物數量的影響;草食動物的數量同時受到它吃的植物數量和吃它的肉食動物數量的牽制;肉食動物的數量又受到它吃的草食動物數量的牽制。那么,在這些相互關系中,究竟哪一個是最主要的、起控制作用的?
這似乎是個簡單的問題,然而至今卻還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在學術界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從下到上”模型,認為植物會使用“化學武器”對抗消費者,通過改變化學成分使植物變得難以消化或不可食用,而過度的消費也會降低植被的質量,從而限制消費者的數目,進而限制捕食者的數目;另一種是“從上到下”模型,認為捕食者控制著消費者的數目,從而限制了消費者對植物的過度消費。
哪一種觀點正確呢?要設計一個實驗來驗證并非難事。如果我們把一個生態系統中有關的捕食者全部消滅,“從下到上”模型預言消費者的數量不會改變,因為它們的數量是由生產者控制的;“從上到下”模型則預言消費者的數量會膨脹,進而又會改變生產者的種類和數量。然而這個實驗設計雖然簡單,卻無法執行,我們不可能在實驗室建立一個包括肉食動物的大型生態系統,法律和道德也不允許我們在野外有意消滅肉食動物來研究其后果。因此,這兩個模型孰是孰非,難以驗證。
幸運的是,大自然已為我們做了實驗。1986年,委內瑞拉在加羅尼河谷建了一個大壩,造出了一個面積達4300平方千米的世界第七大人造湖——古里湖。數百座山峰變成了湖中的島嶼,面積有大有小,最小的不到0.1公頃,最大的大于150公頃。1993年和1994年,一個由美國、秘魯、英國、印度、委內瑞拉、西班牙和加拿大生物學家組成的聯合小組開始對其中12個彼此隔絕、面積不一的島嶼的植物群和動物群進行調查,結果表明,面積不同的島嶼的動、植物群發生了不同的變化。與附近的大陸相比,在大島(大于150公頃)上,原有的物種基本上都保留著;在小島(小于1公頃)和中島(4公頃~12公頃)上,75%以上的脊椎動物滅絕了。小島上的動物剩下了三類:食蟲動物(蜘蛛、蜥蜴、蛙、鳥)、吃種子動物(鼠類)和草食動物(吼猴、鬣蜥、切葉蟻)。以決定某一類花的數量!
生態系統正是由這樣一張張“復雜的關系網”組成的。但是,不管生態系統多么復雜,我們都可以根據食物鏈將其成員分成三類:生產者(例如植物)、消費者(例如草食動物)和捕食者(例如肉食動物)。(此外,還有一類分解者,如細菌、腐食動物,在此不中島上剩下的動物還多了犰狳、刺鼠,有的還有戴帽猴。在中島和小島上,脊椎動物的捕食者(美洲豹、美洲獅、鷹、蛇)基本或完全消失了,形成了一個捕食者被滅絕的生態系統。結果就像“從上到下”模型所預測的,消費者數量激增,中、小島上的鼠類密度比大陸和大島增加了35倍,鬣蜥增加了10倍,吼猴增加了30倍,而切葉蟻巢的密度大約是大陸的兩個數量級。在小島上,密集的草食動物徹底地破壞了植被,植物的密度不到大島的一半,而且大部分植物物種都屬于難以食用的藤本、灌木。按這種趨勢,要不了多久,動植物的多樣性就會從島上消失,最終演變成物種單調的貧瘠的生態系統。這已有了先例:1913年在建巴拿馬運河時也形成了一個人造湖——蓋頓湖,到現在,湖中已有80余年歷史的那些小島就只剩下了貧瘠的生態系統。
由于肉食動物也能對人構成生命威脅,人們對它們有天生的厭惡和恐懼。在人們入侵一個生態系統時,肉食動物往往首當其沖,成為最早的犧牲品,多種肉食動物已被滅絕或成了瀕危物種。在我們知道了肉食動物對生態平衡的重要調節作用之后,或許能使我們對它們更加寬容,從而更好地保護生態環境。
類似的大自然實驗在中國也曾經有過,將來肯定也會發生。例如千島湖就是因修建新安江水庫而形成,而三峽大壩的建成,也將會形成許多新島。我不知道中國的生物學家是否曾經做過類似的生態研究,像這種無須先進設備、又能解決重大科學問題的研究,不應錯過。
(盛文娟插圖)